中國首席奧運記者走了 他用40年講述一個中國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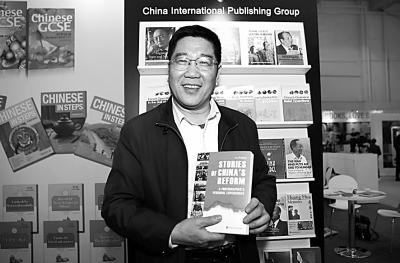
2012年,高殿民在倫敦書展上向讀者介紹中國圖書。資料圖片

高殿民參加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資料圖片

逝世前一天,高殿民(左三)在韓國平昌參加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會會議時與國內同事合影。資料圖片

2004年,高殿民在雅典奧運會新華社前方發稿中心。資料圖片
【追憶】
送別
2016年11月18日上午,天色陰沉,凱文·高斯帕在八寶山送別了一位多年好友,匆匆趕往首都機場T3航站樓。作為北京奧運會協調委員會副主席,他見証了這個航站樓從無到有,也曾經無數次從這裡進出中國的“心臟”。但是他可能從未想過,會有這樣一趟旅程。
高斯帕83歲了,2015年從國際奧委會退休,回到澳大利亞布裡斯班郊外的小鎮,規定自己一年出國不超過六次。然而,雖萬裡迢迢,他也要來與高殿民做最后的告別。
高斯帕管高殿民叫“高”,這是他們1996年在洛桑第一次見面時定下的稱呼。那時,高斯帕是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會主席,作為新華社體育部副主任的高殿民是這個機構的新成員。此后的20年間,“高”成為他“最信任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高”比高斯帕年輕21歲,2016年2月剛剛從新華社退休。高斯帕記得他看上去康健硬朗,寬厚的臉龐上毫無枯槁的痕跡。“高”的離世,就像他驟停的心臟一樣,毫無征兆,未及告別便斬斷了他與這個時空的勾連。
高斯帕帶來了他寫的悼念信:“我欣賞他的人格力量,他的低調而自信,他的真誠,尤其是他溫暖的笑容。”
對高斯帕來說,封存“高”的笑容,也像是給他們親身參與其中的一個時代打上封印。1977年,田徑運動員出身的高斯帕進入國際奧委會,高殿民從大連外國語學院畢業進入中國的國家通訊社。他們從不同的起點出發,因緣際會走上同一條軌道,經歷了中國借助體育和奧運登上世界舞台中央的歷史進程。
首席記者
許海峰59歲了。距離在洛杉磯奧運會上那被載入史冊的一槍已經過去32年。近些年,作為主管現代五項的自行車擊劍中心副主任,他很少出現在公眾視線裡。來告別高殿民,他毫不意外地被記者抓住,鏡頭裡他的臉愈發寬了,眼袋深重。
記憶回到洛杉磯普拉多射擊場。許海峰在那裡射落中國第一塊奧運金牌,而高殿民第一個用文字向祖國、向世界宣告了這個消息。
中國人奪下首金的消息由中國媒體率先發布,現在看來似乎天經地義、不足為表,但在當時難度和意義並不亞於許海峰奪金。
1979年11月,結束十年動蕩、重新面向世界的新中國重返國際奧林匹克舞台。面對中國體育即將鋪開的新章節,新華社在1983年籌劃設立體育新聞編輯部。即將步入而立之年的高殿民,作為當時對外部的英文記者走上了新的軌道。
1984年元旦,新華社體育部成立。那年夏天,以體育部為班底,新華社派出30人的報道團奔赴洛杉磯。他們知道,中國人登上奧運最高領獎台的歷史性一刻就在眼前了。然而,中國脫離奧林匹克大家庭長達25年,誰都沒有親身經歷過這個世界上最盛大的體育賽事,加上遠離祖國、技術落后,報道奧運會和整個國家正在經歷的改革開放一樣,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7月29日,洛杉磯奧運會開賽第一天,高殿民和攝影記者官天一趕到距離市中心140公裡的普拉多射擊場。當時的射擊比賽使用紙靶,打完之后要收齊靶紙驗靶,確定一些壓著環線的彈著點算做幾環。
但當許海峰扣出最后一發時,現場已經躁動起來。中國射擊隊領隊張福告訴高殿民,不用等驗靶,冠軍拿定了。
中國隊和華人們開始歡慶。這不僅是中國歷史第一金,也是洛杉磯奧運會首金,那是全世界通訊社的必爭之地。高殿民沒有時間咀嚼自己的感受,他必須盡快把這則新聞發布出去。
新華社知名體育記者楊明曾這樣解釋通訊社搶發快訊的重要性:“我們發一個消息,如果比美聯社快一秒,全世界的媒體就會用我們的消息,如果晚了一秒,人家就用美聯社消息﹔或者是冠軍,或者是最后一名,這事隻能爭第一。”
高殿民沖到射擊場的新聞中心,抓起電話打通了市內主新聞中心的編輯部。很快,新華社用英文發出了全世界第一條中國贏得第一塊奧運金牌的消息——
China won the first Olympic gold medal。
和許海峰的金牌被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一樣,在當時的情境下,完成奧運首金、中國首金的世界首發,不僅是新華社的成就,更是國家榮耀——世界聽到了中國的聲音,她說這個民族不再孱弱。
相隔半個地球的祖國也收到了年輕記者高殿民用中文記錄的歷史場景,與傳唱大街小巷的“萬裡長城永不倒”匯聚成噴涌的民族情懷。他飽含淚水趴在別人背上奮筆而就《零的突破》,這篇特寫入選小學課本,被中國少年代代傳誦。
“7月29日中午12時26分,雄渾豪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首次在奧林匹克運動場上昂揚高奏。在這庄嚴激越的國歌聲中,鮮艷的五星紅旗徐徐上升,挂在中國體育健兒胸前的金牌,閃爍著耀眼的光輝。在這激動人心的時刻,中華兒女熱血沸騰。多少中國人奔走相告,互道喜訊﹔多少華僑熱淚盈眶,豪情暢涌。許海峰的槍聲不但為新中國奪得了奧運會的第一塊金牌,也向世界宣告奧林匹克的舞台上,從此出現了一個新的體育大國!”
這段文字定格的不僅是中國體育乃至奧林匹克運動史上的重大時刻,更是一個歷經百年磨難的民族站在復興起點、准備重返世界舞台的姿態。
自那時開始,高殿民的職業生涯,甚至是生命,便以4年為刻度延伸。從洛杉磯到倫敦,八屆夏季奧運會,他的角色從記者到領銜者,再到指揮者,從未缺席﹔退休之后,作為國際奧委會的新聞委員,又以觀察者的視角親歷了2016年裡約奧運會。中國走向世界體育大國的歷程全部在他的記憶和記錄裡,沒有人比他更配得上中國奧運“首席記者”的名號。
從雅典到裡約,四次獲邀傳遞奧運火炬,固然是一種榮耀,但對高殿民來說,更意味著傳播奧林匹克精神和理想的使命。在北京奧運會前的數年時間裡,無論哪家媒體、哪個單位、哪所學校請他去講解奧林匹克運動,他無一例外欣然前往。高斯帕稱他為一個“虔誠的奧林匹克人”,為此惺惺相惜。
中西橋梁
2016年11月11日,安東尼·埃德加在韓國平昌的醫院送走了高殿民。幾天之后,他又臨時改了行程,趕來北京參加他的告別儀式。算上在新聞委員會會議上的追思會,他已經三送好友了。
安東尼來自澳大利亞,擔任國際奧委會媒體運行部總監已經10余年。他和高殿民結識於國際排聯新聞委員會,有20多年的交情。“高”是他親密的“哥們兒”,也是敬重的同行。
在一封詩意的悼念信裡,他回憶起一件往事——
“那是2006年的春天,我和高在故宮裡散步,我們閑聊了很多話題。當時美國在小布什政府的領導下深陷伊拉克戰爭。與此同時,美國的一些媒體和政客在公開批評中國以及中國的一些政策。我問高對此有何看法。他若有所思地走了幾步,然后平靜地回答道:等到美國擁有4000年歷史和12億人口的時候,我們再來聽聽他們說什麼吧。”
一個東方大國的快速崛起,必然伴隨西方世界的警惕與偏見。從中國重返奧林匹克舞台開始,中西方之間的摩擦便和交流如影隨形,其中自有語言文化的差異,更有世界觀、意識形態的鴻溝。北京兩次申辦奧運,西方政界和媒體不厭其煩地翻炒一些敏感話題。
高斯帕對這種自以為是的傲慢和政治綁架嗤之以鼻,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更是一針見血:他們就是不想讓中國通過奧運會飛速發展。
曾任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的何振梁對此感觸極深。這位“申奧功勛”在日記裡寫下這樣一段談話:“在總體對我們不利的輿論環境下,盡可能爭取創造某種有利於我們申辦的體育輿論。要達此目的,必須在對外宣傳范圍內,大力做好有影響的體育媒體、有影響的體育記者的工作,也就是說,外宣工作中也有外聯工作。”
這便是高殿民的使命。從1992年進入國際排聯新聞委員會開始,他就不再僅僅是一名中國記者。在國際排聯、國際乒聯、國際田聯、國際奧委會、國際體育記者協會,他與許多國際主流體育媒體人成為摯友。他手下的“兵”,但凡遇到國際奧委會官員或各國資深體育記者,隻要提到“高”,對方往往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地講起與高殿民的友誼。
國際奧委會媒體專家理查德對“高”的外交才華贊嘆不已。他一面是“管道”,西方媒體和國際奧委會的很多人都是通過他了解中國的體育和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另一面是“海綿”,他向外界展示了一張具有世界通行力的中國面孔——身材魁梧,笑容滿面,睿智幽默,常常在笑談間消弭分歧。
媒體間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憑借多年積累的資歷、聲望、人脈,高殿民常常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和他的部下們一樣,國家體育總局宣傳司副司長溫文管高殿民叫“高sir”——沒有人叫他“高主任”。溫文對這位老大哥有太多的感謝,她稱他為“救火隊員”。
早些年的奧運會,運動員和教練員的証件不能通行媒體區域,如果要開新聞發布會或者接受各種訪談,需要提前24小時辦証件,但往往比賽結束就已經過了時限。但是,他們有高sir。“第二天,我們快到的時候,他都會在門口接我們,總能把我們順利領進去。”這是其一。
其二,高殿民就像中國代表團“不在編的新聞官”,常常幫忙“圓場”。“用他獨特的話語方式,用西方媒體能理解和接受的話語方式,表達我們的主張,澄清外國媒體的誤解。”
安東尼喜歡和高斯帕一道,經常拿那個標志性的掩嘴動作來“嘲笑”這位中國“哥們兒”。但在告別的那天他認真地說,“高”是一個非凡的人。“他幫助世界媒體了解中國,幫助中國媒體了解世界,是促進中西方體育媒體交流和理解的一座橋梁。”
中國立場
年近七十的理查德這次去韓國平昌有一項特別的任務——為老朋友高殿民致頒獎辭。“高”將在2016年年底結束他在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會的任職,這次新聞委員會會議特別邀請他前來,准備表彰他長達20年的服務。
他們准備好了金質奧運五環紀念雕塑,基座上寫著:“高殿民,為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會出色服務20年。”
理查德也寫好了四頁紙的講稿,沒想到幾個小時之差,沒能念給“高”聽。榮休會變成了追思會,理查德一字不改宣讀了原文,“就像風趣的‘高’還坐在我的對面”。頒獎辭回顧了高殿民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的工作,生動幽默的文字卻使他幾度哽咽。
理查德說,“高”在國際體育媒體圈獲得那麼多的友誼和尊重,不僅在於他與生俱來的交往能力和對奧林匹克的虔誠,更在於他對國家利益的忠誠。
如果不是溫文的講述,很多高殿民身邊的人至今都不知道在外聯之余,他為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做了怎樣直接卻又默默無聞的工作。
2013年接受北體大教師薛文婷採訪時,高殿民曾提到2001年北京接待國際奧委會評估團考察,自己作為媒體運行第二陳述人的事,寥寥幾句,輕描淡寫。作為親歷者,溫文在他身后講起來龍去脈,幾乎落淚。
當時奧申委考慮到高sir較高的國際聲譽、出眾的英語水平和對體育報道透徹的了解,想邀請他作為媒體運行的陳述人。“對他來說,這是新聞工作生涯中值得大書特書的榮耀”,但是他頗具洞察力地指出,國際奧委會很大的一部分收入來自電視轉播,所以舉辦國家電視轉播機構的態度和實力很關鍵,他因此力薦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負責人馬國力作為陳述人,認為這樣更能有效打消委員們的疑慮,更有利於申辦成功。
“我們把高殿民的建議匯報給奧申委,當時包括何振梁在內的專家都認為他的考慮是周全和有道理的。”溫文說,“高殿民就這樣放棄了當第一陳述人的機會,甘願當候補陳述人。他一直參加相關文件的起草,提出很多有見地的意見,還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准備候補陳述人的匯報材料。他還不斷鼓勵我說,‘你把心放到肚子裡去,不要著急,我給你當備選!’”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夢圓,天安門廣場徹夜未眠。4個月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此后的七年,新中國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融入世界。北京奧運會,是重新崛起的東方大國第一次走到世界舞台中央,她向世界發出怎樣的聲音,與她向世界呈現怎樣的新面貌一起,成為重塑中國形象的軌道。這必然是一場立足體育又超越體育的國際輿論競爭。
回溯到10年之前,高殿民初掌新華社體育部。他敏銳地認識到,中國體育報道終將參與國際體育新聞競爭。作為國家通訊社,爭奪國際話語權是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為體育部設定了英文專業的門檻,要求每名記者必須能用中英雙語採訪和寫作。奧運會之前數年的各種大賽,年輕記者都經歷了中英雙軌採寫的“魔鬼訓練”。
高殿民常說——
“我們對英文報道一點都不能忽視,國際奧委會官員、國際知名媒體每天都在看我們的稿子。在他們眼裡,我們代表著新華社的立場,代表著中國的立場。”
經年的積累,在北京奧運會前得到了集中回報。
2006年10月26日,在高斯帕看來,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天。作為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會主席,他將國際奧委會確定新華社為北京奧運會東道主通訊社並組建官方攝影隊的授權書,交到時任新華社副社長馬勝榮的手中。
中國國家通訊社第一次獲得了與美聯、路透、法新世界三大通訊社同等的待遇。國際奧委會在寫給新華社社長、總編輯的信中說,新華社的報道將把重要的中國視角帶入到國際奧林匹克運動中。
回憶起“無與倫比”的北京奧運會,理查德說,毫無疑問,這屆奧運會的新聞報道同樣取得了巨大成功。“高”的影響隨處可見,這讓他對這種成功“毫不意外”。
聽聞高殿民猝然離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第一次為一名中國記者寫來唁電。信中說——
“作為奧林匹克大家庭頗受重視的一員,無論是早期擔任體育記者,還是后來成為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會的委員,他都將自己的生涯,致力於推動體育的發展。他為此作出的杰出貢獻,將會被中國和世界銘記。”
不滅燈光
米蘭·昆德拉在《為了告別的聚會》裡說,最好的告別,就是你倆話說到一半,突然有件事把你叫走了,話頭還撂在那兒,原打算待會兒繼續的,卻就此天人永隔。
然而對徐濟成來說,這樣的告別雖詩意,雖天意,卻叫人肝腸寸斷。
2016年11月11日晚上,國際奧委會的新聞委員們要為“高”辦榮休會。下午3點28分,已經成為北京冬奧組委新聞宣傳部副部長的徐濟成接到老領導高sir從房間打來的電話:“我都換好衣服了,門我沒關,直接進來就行。好,好,就這麼著。一會兒見!”
“一會兒”之后,徐濟成推門進去,見高sir仰面躺在梳妝鏡前,皮鞋緊系,衣著整齊,領帶端正,神態安詳……他扑過去打了急救電話,又扑回來做心肺復蘇。后來醫生說,就在相隔4分鐘的兩個電話間的某個時刻,就像關電燈一樣,他的心臟驟然停止搏動。“你1米8的身軀,就像一件庄嚴的袈裟,從衣架上滑落在地,鋪展攤開。所以你的后腦著地,卻沒有任何碰傷,衣褲甚至連皺褶都沒有,四肢完全鬆弛,就像神仙一樣。”
永別來得猝不及防,卷起一片震驚與哀慟。
許基仁曾與高殿民搭檔執掌新華社體育部13年,彼此有著深厚的情誼。在高殿民遠赴歐洲出任倫敦分社社長之后,許基仁成為他的繼任者。11月14日,他強忍悲痛逼迫自己寫下一篇祭文,其中有這樣一句:“我還從來沒有發現身邊的人辭世時,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思念,如此之深的痛惜。”
那是因為他淡泊名利——從2010年卸任體育部主任開始,他一再陳情,希望辭去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的職務,由體育部同仁接替,以更好地延續新華社在國際體育媒體圈的話語權。
那是因為他寬厚溫暖——后輩們說他是宣武門西大街57號大院裡最不讓人緊張的人,他常常“寓教育於八卦”,笑瞇瞇地跟他們拉家常,教他們如何寫稿子、帶孩子……
那是因為他自律簡朴——一輛自行車、一袋白饅頭的日常幾十年未變,一件西服能穿上20年。
那是因為他古道熱腸——他為身邊所有人的健康、職稱、福利、發展,乃至大齡單身青年的終身大事操心,不計付出,不求回報。
那是因為他遼闊的胸懷,和他像孩子一樣發自肺腑、又裝作蔫壞的笑容……
現任體育部副主任周杰接替高殿民成為國際奧委會的新聞委員。11月11日下午,他是第二個趕到高sir身邊的人,又陪伴他夫人和他的骨灰從平昌回到北京。一個星期過去,他才敢於去觸碰一些往事。
那是1988年的一個夜班,高殿民因為第二天一早有事,便借住在周杰的集體宿舍,兩人聊了許多。“我記得高說,作為下鄉知青,他勞動很賣力,公社和生產大隊對他很不錯。有一天下午,他正在打麥場打麥子,生產隊長給他送去了大連外語學院的入學通知書,這紙通知書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說,他一直被人善待,無以為報,因此他唯有努力工作,善待他人作為報答。”
他的老部下王子江身在遙遠的倫敦,在一個深夜淚流滿面,寫下這樣一段話——
高sir,又是一個倫敦的深秋,分社前橡樹的黃葉又一次隨風飄零著。
往年,當葉子逐漸稀疏,你會指著剩余的幾片葉子問:“知道為什麼別的葉子掉光了?隻有那幾片還留著?”
往往不等我們回答,你會解釋道,因為那幾片葉子靠近路燈,靠著燈的一點熱量,殘葉會在秋風中做最后的舞蹈。
…………
高sir,隻盼你在另外一個世界裡安息,我們每個人都如同眼前的黃葉,都會有凋零的一天,你只是沒有長在靠近燈光的一側。
因為你自己,就是那燈光。(沈楠)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