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高滿堂:我也擔心收視率,更擔心沒有好作品


高滿堂
高滿堂是當下最著名的編劇之一。從1983年開始,至今編劇900余(部)集,曾多次獲得全國“飛天獎”“金鷹獎”“五個一”工程獎等中國電視劇最高獎項。他的作品多以貼近生活、富有時代感著稱。其《闖關東》系列、《家有九鳳》《鋼鐵年代》《溫州一家人》等等,不僅收視率高,而且贏得了觀眾的良好口碑。
高滿堂不僅是金牌編劇,更熱心於促進電視劇的產業發展。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多次在兩會上建言獻策。高滿堂站在創作第一線,說話耿直爽快,一針見血,讓人拍案叫絕。最近,高滿堂醞釀三年的電視劇《老中醫》開拍在即,他帶領所有主創人員第三次來到中醫之鄉——常州進行採風,體驗當地生活。高滿堂特意抽出時間,來到九局,和我們聊聊他的新作品和對電視劇行業的看法。
【九局有請】高滿堂——
九局:聽說這是您第三次來常州採風了。前兩次是您自己來,這一次為什麼要帶領整個團隊來採風呢?
高滿堂:這次我創作的是中醫題材的電視劇。平日裡去採風,一般來說兩次就差不多了。但今天我第三次來到常州,又聽到了一些中醫的醫案,是醫生們祖上或者朋友之間流傳下來的,非常精彩。要是有時間,我還得再來。
帶演員來到中醫的故鄉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陳寶國,之前他通過影像資料、書籍已經了解了很多中醫方面的知識,給人號脈的時候,姿勢也都正確,但感覺還是有些“隔”。他仔細在現場觀察中醫治病之后,就連眼神,都和以前不一樣了。

陳寶國向常州中醫院院長,孟河醫派傳人張琪學習如何把脈
九局:現在總聽到劇組開機儀式、關機儀式、探班活動,這種採風活動真是不多見。
高滿堂:剛才可凡老師說,他來之前告訴一位著名的電影導演要為電視劇採風,體驗生活,那位導演意味深長地說,採風這個詞在影視圈可是好久都沒聽說過了。
80年代、90年代的影視劇創作,採風不僅僅是作家、編劇的事情,演員、主創人員到下面去深入生活是家常便飯。馮遠征出演《青春祭》的時候,導演就把他放到了最貧困的傣族的寨子中最窮困的人家。他在那裡呆了3天3夜,最后都不成樣子。助理看著他身上幾百個蚊子咬的包,當場就落淚了。確實也隻有這樣,演員才能迅速地融入到故事當中。

《青春祭》中,馮遠征先去寨子體驗生活
九局:之前您批評當下影視劇的一些亂象引起了社會很大的反響。
高滿堂:我確實說過,我的劇組如果出現倒模的現象,我就把它砸了。我認識一個年輕演員。他說,高老師,我快累死了。一個劇拍4、5個月,他往常能給一個劇組50、60天就不錯了。包括我最近要上映的一部戲《愛情的邊疆》,也找過當紅年輕男演員。當時他團隊的人問我,高老師,上哪拍戲呀?我說,去東北啊!他說,東北可冷呢!我說,不僅冷,而且要拍三個季節,冰天雪地呢。這個團隊直接就拒絕我了,因為團隊本身不想遭罪。而那個演員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很多演員就是這樣被綁架了。

電視劇《愛情的邊疆》在冰天雪地裡拍攝,條件非常艱苦
九局:您的作品涉獵工商農等各個行業,這一次為什麼要以中醫為題材?
高滿堂:現在大家尋找的都是熱點,各種大IP,中IP,小IP,絡繹不絕。那些所謂的“歷史劇”的年代背景,僅僅作為時間、地點的交代。這種傳奇加神奇的方式,省時省力,雖然許多年輕觀眾喜歡看,但文化含量少,審美層次淺。我還是想好好地給觀眾講故事。
去年屠呦呦憑借青蒿素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世界為之驚嘆。而我們作為中國人,對中醫藥知之甚少,甚至比較麻木,這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不過這也是有原因的。中醫歷史悠久,但是從誕生起就泥沙俱下。我自己的家人甚至都受過假中醫的傷害。但也是因為中醫的實用性,患者沒辦法分辨真假,許多假中醫寫的書卻很暢銷,我覺得老百姓需要一種淺顯易懂的方式“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
九局:您對這部作品有什麼期待?
高滿堂:我去年來的時候,開始轉了幾天沒有太多感覺,還反復問自己為何而來。后來我讀了30多本中醫相關的書籍,發現自己之前真的很無知。中醫蘊含了歷史、天文、地理、書法等等,老祖宗不動聲色地為我們后代留下如此寶貴的財富,而我們卻渾然不知。另外,中醫還在潛移默化中淨化我們的心靈。他讓你心靜,讓你覺得對名、利沒必要患得患失。
我希望老百姓看完這部電視劇,自己能簡單號號脈,開點小方子,更能夠體會老中醫的那種“放下”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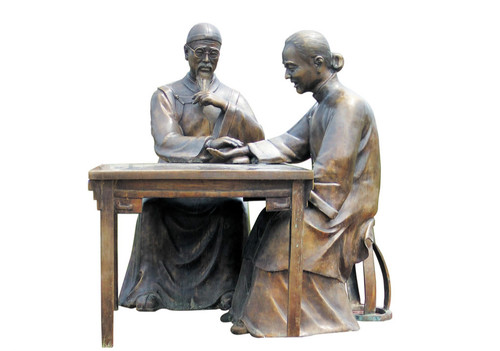
中醫
九局:現在很多影視劇講究“快”,怕過了時效失去關注度,您怎麼看現在這種現象?
高滿堂:要說快,我可以作為一個反例了。《闖關東》我創作了10年,《老農民》5年,這部《老中醫》到目前也已經打磨3年了。許多人在市場面前,成為了為市場服務的作家。為了金錢、名利,他們沉不下去。大量的迎合市場的電視劇,今天看了,明天就忘,這是一種文化快餐,是市場的“催生婆”,浪費大量資源而生產出的“殘疾兒”真讓人心疼。有人給我提出質疑,你高滿堂出門採訪方便啊,你是名作家,有人招待。我剛開始採訪時,沒人理我,我裝了40袋方便面,60包榨菜,一個人深入東三省。其實我住在農民家,發高燒,差點燒死,那兩個農民不識字,也不給我送到醫院,我最后尿都尿不出來﹔我胃潰瘍犯了,上完廁所一看全是鮮血,覺得自己死定了,可能走不出北大荒了﹔最后在一個大雪天,我在加格達奇,一個人坐著火車,到了沈陽。我躺在沈陽南站,一坐不醒。那個時候,我沒有任何條件,我是不知名的作家,我去做了,我走了第一步,現在我熬過來了。誰沒有第一次,為什麼不敢趟第一次?這是弱者的借口。包括闖關東,一路沒有人理我們,我們走了7千多公裡。那天我們到了孫吳縣,一天沒吃東西,吃豆腐蘸大醬,我吃了六塊。吃完了之后肚子脹,我坐在地上都起不來。我說深入生活,不應該是浮光掠影,應該老鷹抓地。抓起一把土。
九局:當下這種浮躁之風,是創作的原因還是市場的原因?
高滿堂:市場一直都在影響著創作者。這一點無論如何都得承認。就算我有再高的靈性,沒人投資,沒用。我之所以堅持做現實題材,堅持現實主義,也是因為現實主義創作得好,有收視率,就能創造出經濟效益,這是雙贏的。包括我之后做《老酒館》,也是一個年代劇,投資方對我非常有信心,他們說高老師,馬上做,我信任你。你會發現隻要你認真創作,就會贏得尊重,獲得支持。不過,現在很少有投資方,這麼神閑氣定,這麼有投資眼光,這麼不急不躁了。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投資方不要瞪著猩紅的,充滿血絲的眼睛,恨不得把編劇吃了:趕緊給我生作品,一年要懷八次孕。這是一種非藝術的做法,都是短命的也是短視的。真正做得長遠,還是有見地、長遠思想的人,才能出好作品。
九局:您覺得當下這種風氣會發生好轉嗎?
高滿堂:目前創造導向出現問題,這不是偶然現象,是歷史長期積累的一個結果。不少創作者不去直面人生,直面現實,隻去拐彎抹角地寫鬼怪神仙。口水話,輕飄飄,無病呻吟,假模假式,飛來飛去……這其中需要反思的東西太多。中國影視真正走出去,不是鬼怪神仙俠,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主義。美國的《血戰鋼鋸嶺》《為奴十二年》《拆彈部隊》,都是現實主義,他們獲得國際大獎是有道理的。英雄主義、愛國主義,永遠是我們追逐的主題。
當下產業浮躁,是一個社會、文化發展必須經歷的階段,無論小鮮肉高片酬還是唯收視率、點擊率,都是要經歷的階段。我們電視人每天經歷一種痛苦:電視劇的收視率是多少?我也不能免俗,也得看,這是一個困惑期,也是一個調整期。但是沒有什麼走不過去的,我們必須要有我們的力量,戰勝偽文化、浮文化。(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文藝九局工作室 任飛帆)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