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神磊磊:推倒知識橫在人們面前、那道高深的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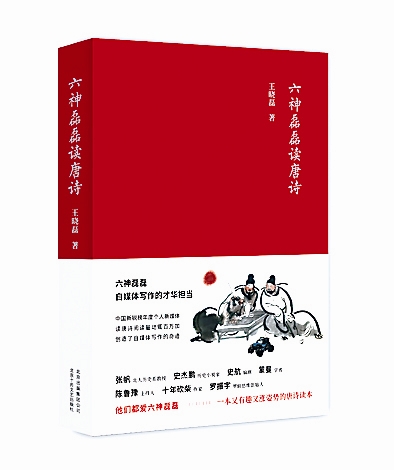

曾經,當網絡閱讀蔚然成風時,不少人在歡呼,門檻降低的全民閱讀2.0時代到來了。如今,人們卻越來越多抱怨微信公眾號打開率低、閱讀數直線下降,而有關文章怎樣才有趣、才能吸引人打開的討論不絕於耳。在這樣的起伏中,六神磊磊算是成功的弄潮兒,他覺得自己做的,就是推倒了知識橫在人們面前、那道令人畏難的高深的牆。
閱讀這個概念,在今天被分成了很多層次,不論是圖個樂子、找點談資,還是為了求知,我們會發現,大家的要求其實越來越高﹔而與之對應的,卻是對閱讀付費的反彈越來越大。今天的專題,我們想探討:把閱讀變得有趣當然可行,但如果閱讀付費,你會接受嗎?
和古人共情
第一次和六神磊磊隔著聲波打交道,是今年初春,當時李白和杜甫成為社交網絡上的一對網紅,網友拿出杜甫為李白題寫的若干首詩歌,對比李白隻寫了一首《贈汪倫》,調侃李白是個負心漢。李白、杜甫成為熱搜榜上的紅人,和演藝明星並肩,這件事本身就很匪夷所思。那時候,《詩詞大會》的熱點還沒有消散,所有涉及詩歌的話題都可以標榜自己是文化界的清流。
編輯說不如做個題目吧。當時我很清楚,用什麼方式講述這個故事,是擺在我面前的一道選擇題:用中學語文課上老師的講法、《百家講壇》的講法,還是用互聯網上那種不端著的講法。三種方法都沒有絕對的對錯,但不同的表達最后指向不同的結果。后來六神磊磊的名字突然空降到我面前:曾經他寫杜甫,他說杜甫遲來的功名與成就,像是“一個小號的逆襲”——這種說法很打動人,入了半截土的事,被他一說,總覺得是抖掉了歷史的陳舊的塵,煥發出屬於這個時代的氣息。再說得直白點,就是把看似標本一樣蔫萎的菜,做成一款時髦的料理。我覺得,就是他了。
找到六神磊磊採訪時,他說,自己先要例行健身,等他有時間再認真回答。傍晚,他一氣兒發了二十多條語音,完全是信手拈來的速度,“李白對杜甫說‘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和杜甫對李白說‘何當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不是一樣的感情嗎。” 他說覺得杜甫寫李白感動人的四句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和“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之后又找補一句“李白大概聽了想親他一口吧”。
最后,採訪稿以《六神磊磊談李杜:杜甫對李白的評價沒那麼高》為題發在了本報上。
最近出版社的朋友和我透露說,他的新書就要出版了,這次他不是要讀金庸,而是專門寫一本帶有考據色彩的唐詩閱讀指南——也就是今天擺在書店裡的《六神磊磊讀唐詩》。於是這一次,我們有了面對面採訪的機會。
寫一本唐詩解讀,用現代人的眼光走近古代人,這是六神磊磊的一次偶然,他當時還在上班,同事都回家了,他獨自在辦公樓裡寫了幾個唐詩故事,起標題說《膜拜吧!唐詩裡的那些猛人猛事》,第二天發現這篇文章被轉得到處都是,“我意識到,咱們的同齡人不是都喜歡‘那一天,我轉動所有經筒’。慢慢的我開始想醞釀寫一本唐詩的書。”
史航說他喜歡六神磊磊談唐詩時文字裡的滄桑感,“他像是陪著他們一塊度過了很久歲月的人,所以提到誰的時候都不是隔山夸牛,都像是年老的牧童看著一代一代的耕農變成了什麼。”
他想寫那些真正感動到他的故事。他說他目之所及的地方,少有人這樣做。有次在家鄉江西的新華書店他聽到一個8歲的小孩對他7歲的弟弟說,“你都多大了,你還看唐詩?”“在他們的概念裡,唐詩是就是兒歌。”六神磊磊說,“沒有感動,沒法和古代人共情,唐詩就讀不懂了。”
“我們都知道‘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但誰能真正理解韓愈當時的心情?他得罪了皇上,早上把奏書送到皇帝那兒去,晚上就被要求貶到潮州,上千裡路程,而且必須馬上動身。”他說要讓讀者和唐詩的距離真正拉近,讓每個人走入那種情景,讓詩句中的情感打動到人,“應該和孩子們講,小朋友,今天晚上必須背上背包去越南。爸爸媽媽沒法陪你們,問問孩子到路上時你是什麼感情?這樣孩子們就會懂了。”
寫公號的藝術與技術
採訪六神磊磊這天,北京很熱,他被媒體輪番採訪完並且簽了很多簽名書以后,坐下來回答我的問題。開始之前,工作人員拿來一瓶水,桌子上,不鏽鋼的盆裡放了幾隻桃子和一堆葡萄。“我能先吃個桃嗎?”六神磊磊問,然后開始吃。多汁的桃子很快吃完,他手上有點黏。“啊,還是先去洗個手吧。”之后我們才開始訪問。
對這個開場白印象很深,我不是要說什麼不尊重的問題,反而覺得這種自然的狀態很少見。之前很多採訪受訪人都會想表現出某種正式,大家嘴上說著,雖然也有放鬆或者自然的狀態,但說到底還是有牆隔著。
從事表達創作的人,面臨無數這樣的牆,要讓溝通順暢就要想辦法越過這些屏障。六神磊磊的工作更像是推倒一堵關於知識表述的牆。
無論是讀金庸,還是讀唐詩,在他的公號裡,因為他語氣的親民,《金庸、古龍、魯迅會怎麼寫爸爸去哪兒》、《金庸江湖裡的三個宣傳部長》、《杜甫的太太:我嫁的是個假詩人》,光看題目就知道,很多事情就好像不再處於殿堂之高,仿佛就是簡單到“我能吃個桃嗎”一樣。接下來他再用考據和網絡上年輕人的語言說這個桃子為什麼甜,把這個桃子的前世今生講給每個人。
把高深的東西,講得有趣是一門藝術。曾以為是他的記者經歷讓他懂得大眾傳媒的秘密,但其實並不是,這份工作帶來一把尺子,衡量“好內容”的意義,在他看來,這才是刷屏的秘訣。
在六神磊磊這個名字被大家熟知以前,名為王曉磊的他在新華社重慶分社工作。那份工作的性質是用“最嚴謹、最無法挑剔的語言寫東西”。新華社很多年前發過一篇稿子《萬裡委員長離任的時刻》,六神磊磊說,這樣的稿子放到現在手機端也會刷屏。“因為好的內容永遠會受歡迎。不是用什麼妄言妄語,而是靠真實的東西把人打動。”
好的內容是那個核,但把好內容講得親切仍是一件技術活。說穿了,讓人覺得幽默有趣會心一笑的文章,讀者在閱讀中往往收獲了一種熟悉感,這是作者創作之初就渴望達到的默契。咪蒙從萬千男女的情感故事中找到讓人們咬牙切齒的但難於啟齒的恨,然后開始替群眾泄憤﹔而很多篇篇十萬加的娛樂八卦號則是從汪洋般的娛樂新聞裡,找到一部劇或者一個明星與普通人的共性,最后包裝出一個大多數人覺得閃閃發光的普遍真理。這些是他們推倒牆的辦法。
對於六神磊磊來說,他的渴望從“知識邊境”內外挖掘。“你要大概知道讀者的知識邊界在哪裡,你要介紹的一個人是在這個邊界之內還是之外。”他很會在一個論証之后舉出例子,特別自然的不會讓人覺得和他聊天是難如取下圖書館最高層書架上的書。“有一天我在公號裡寫盧植,你會知道這個人是落在大眾知識邊境之外的一個人。如果你非讓他出場,怎麼辦?你解釋解釋,這個事情不會降低你文章的品位的。”六神磊磊說,他的技巧是用關系網把這個人拽到大眾的視野裡,“我會說,盧植有個徒弟,在《三國演義》裡出場過,是白馬將軍公孫瓚。那你還要想到,這個公孫瓚也可能是大眾知識邊界之外的人,這時候再告訴大家,盧植還有另外一個徒弟,叫劉備。”用已知聯系未知,這件事讓六神磊磊也很上癮。
賣知識可恥嗎?
春天就李白、杜甫的話題採訪六神磊磊時,他曾經和我談到“二手知識”。“如果(讀者)感興趣,(應該)盡量去讀原著和經典,不要總看二手三手的知識,總看二手知識,人會傻掉的。”
說法很新鮮,道理很簡單。現在網絡上越來越多的知識類網紅在做知識販賣者。把六神磊磊和咪蒙或者娛樂八卦寫手放在一起,好像並不太科學,除了在互聯網上做自媒體的寫作者以外,他們文章的屬性並不相同。六神磊磊的文章帶著知識的屬性,但如果嚴格去講,解讀本身也是二手知識。
他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翻越圍牆:“唐詩是一個花園,被圍牆圍著,多數人都和這個花園擦肩而過,我想翻過唐詩的圍牆,去裡面摘幾朵花給大家看看——你們看這個花很好看,你們喜歡嗎?如果喜歡你們可以去走正門。”六神磊磊說,“我相信每一個做二手知識的人,他有點兒追求的話,他都會希望最后是把大家引到一手知識那兒去,我相信羅振宇肯定也是這樣的。”
“最重要的,是你如果感興趣自己繞到正門進去再看。”羅振宇覺得六神磊磊這話深得他心。
說到二手知識,不可能繞開羅振宇和他的“羅輯思維”,此前青閱讀訪問羅振宇的“羅輯思維”的互聯網產品“得到”——這個專注於把一本書的干貨打撈出來供大家購買、學習的產品,收獲大量粉絲,他們的員工干脆把“選書編輯”稱為“知識買手”。
知識賣錢,用互聯網語言叫“知識經濟”,這件事的爭議不小,知識能作為商品出售嗎?六神磊磊的觀點是,有這樣的疑問的時候,就是我們在用雙重標准來做判斷:“你看,比如面對一個明星,我們絕對不會問他一年掙多少錢﹔但是如果去採訪一個作家,我們會好奇這個人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第幾,這麼高的收入有沒有改變一個人的生活。這說明我們隱隱約約覺得這件事不正常。”
六神磊磊自己也准備把知識和經濟聯系起來了——他正在籌備自己的古詩課程產品——給孩子講古詩。雖然課程的形態和內容還在籌備階段,但付費課程已經是確定的事了。
他又指著不鏽鋼盆裡的桃子說,“我們搞了商品經濟那麼多年,大家都覺得這個桃子、這個手機可以賣錢,可是我把知識做了剪裁、包裝之后賣錢,大家就覺得有點新鮮。我們就忍不住去問,知識還能賣錢?標價合理嗎?你怎麼保証你的知識是好的知識……”所有這些問題隨著記者們的震驚接踵而至,但六神磊磊安慰道,大家放鬆,不必太過驚詫。“我付出了勞動,如果這個東西在市場上有價值,也是挺好的事情。畢竟在市場上有人還在賣地溝油的時候,有的人在賣知識,這不是一件壞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