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好故事從何處尋——寄語當代電影編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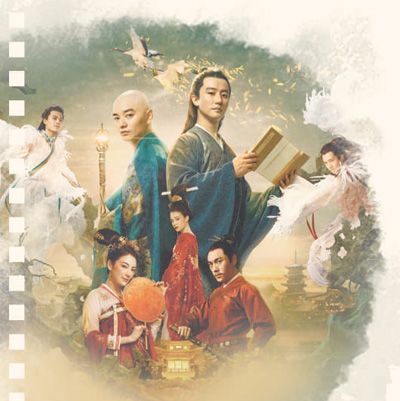

559.11億,中國電影再度交出漂亮成績單。這是一個有溫度有含義的數字。某種程度上,讀懂它,也就讀懂了中國電影的成績與短板,讀懂了中國故事與電影發展的深切勾連。
斬獲56.83億票房的《戰狼Ⅱ》讓眾多觀眾熱血沸騰﹔直面歷史傷疤的《二十二》成了票房破億的現象級紀錄片﹔《芳華》《妖貓傳》兩部“第五代”導演新作燒熱賀歲檔……回望2017,我們發現,不斷擴容的市場,不僅意味著數字增長、銀幕延伸,更渴求精彩的中國故事來支撐。
作為一劇之本的編劇,如何為大銀幕輸送好故事?在創作鏈條中最具首創精神的編劇,如何與資本邏輯共舞,做出新時代的文化表達?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的電影電視評論周論壇,成為編劇、評論家、理論家三方求解的話題。
文學精神是電影核心競爭力
“我們一些電影敘事重故事、輕人物,經典類型的敘事經驗仍然是中國電影的短板。”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鐘大豐在會議發言中說。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聽到如此評價。電影《老炮兒》上映時,導演管虎在接受採訪時曾說:“我的小野心是給中國電影史留下幾個人物。因為我們的電影大多數老談故事,故事之后是IP,然后是賺錢,這幾年幾乎想不到留下什麼人物。”這似乎也不只是電影的難題。2014年,我採訪編劇高滿堂,同樣聽到類似的感慨:“回想這一年的電視劇,你能記住哪些人物?大多數都是類型化的,個性面貌都差不多。但我們今天能忘記李雙雙、李有才、梁生寶嗎?我們現在都在開著情節的列車狂奔,但人物還留在始發站。中國每年有一萬多集電視劇,留不住人物形象,是個問題。”
一方面是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是情節的碎片化、段子化,這是一體兩面的問題。一些由熱門IP改編的影片,主人公的台詞直接引用原著,有的甚至直接引用網絡段子。段子消費了觀眾的情感和關注,故事的情感表達和敘事邏輯卻變得零碎不堪、氣若游絲。還有的以主觀式意願、情緒化表達、意向式拼貼,以場面、技術和明星,取代故事主體。一部影片看下來,除了場面、段子就是明星面孔,劇情和人物難以讓觀眾留下印象,就更別提情感共鳴甚至審美體驗。
造成碎片化和輕人物的原因有多方面。市場偏重題材、偏重故事,對傳記電影缺乏熱情﹔而回到劇本,編劇缺乏精耕細作,對生活的體認提煉不足,難以塑造真正俘獲觀眾的人物,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影視中心主任田水泉在論壇上講,他經常接待編劇和導演去法院體驗生活,一些創作者走馬觀花,了解一下整體情況,開個座談會,就回去創作了。“比如寫《紙牌屋》,如果對政權體系的了解不夠深,即便有再高的編劇技巧,也很難寫到深入人心。這是創作者自身的問題。”
碎片化和輕人物,還意味著對文學的背棄。“文學語言是想象的起點,電影語言是想象力的終點。沒有文學性的電影就如同無源之水。”《滾蛋吧!腫瘤君》的編劇袁源舉了《紅高粱》《芳華》《心理罪》《星際穿越》做例子,她認為優秀影片大多脫胎於嚴肅文學,網絡文學帶來影視界IP“高燒”,網絡文學的碎片化、快餐化等弊端同步被移植到電影創作中,值得警惕。
電影雖然具有經濟屬性,但畢竟是內容產品。人物塑造、情節設置、藝術表達、意蘊傳遞,是電影的內容屬性,也是文學的精神要素。優秀電影總是站在文學巨人的肩膀上,它們不斷提醒后來者:文學精神、文學氣質始終是電影的核心競爭力。
故事格局與創作情懷有關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這是好萊塢編劇麥基的名言。在那本影視業人盡皆知的《故事》裡,麥基寫到了故事的衰竭。美國好萊塢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暴露這一問題:電影工業化程度越來越高,電影作品越來越多,故事反而越來越單調、平庸、模式化﹔好故事越來越少,漏洞百出和虛假的故事手法越來越多,人們用奇觀來取代實質,用詭異來取代真實。
而在中國,最近40年的社會變革帶來了人們生活和思想的巨大變化。生活極盡精彩,故事也層出不窮。在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洋看來,我們當前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大故事貧弱、小故事興起。“《戰狼Ⅱ》是大故事,中國觀眾都能夠看懂理解並認同﹔《閃光少女》屬於小故事,聚焦一小部分人群的趣味和生活。”他認為,模式化編劇相對容易,真正深入生活寫出脫胎於時代、反映時代精神的大故事才最為考驗水平。
這些年,中國電影類型化、多樣化發展引人注目。動作片、青春片、喜劇片、懸疑片成了市場的主打類型,但講述中國大故事的主流電影同時獲得口碑票房雙贏的,卻屈指可數。2017年除了《戰狼Ⅱ》,還有《建軍大業》《空天獵》《十八洞村》等幾部,但放在國產電影全年798部故事片的基數上來看,仍顯單薄。
當前類型編劇發展不平衡的另一個表現是,都市題材的編劇陣容比較大,工業題材、農業題材、法制題材的創作數量不足。特別是重大歷史現場的缺位。城中村改造、脫困攻艱、“一帶一路”等正在進行中的重大歷史現場,目前還沒有產生公認的精品力作。我們的時代正處於大的歷史轉型時期,但編劇沒有介入和反映重大歷史現場,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之所以創作不出具有宏大敘事格局的影片,可能跟創作者自身的思想深度、格局情懷,甚至美學素養有關。什麼是正確的價值觀?什麼是錯誤的價值觀?什麼是美的?什麼是丑的?如果電影創作者本身不清楚,就表達不出來,也無法傳遞給觀眾。”田水泉說。
構建中國電影的文化體系
“在好萊塢大片的陰影下,中國的國產電影常常要面對巨大挑戰。我們理應考慮對中國電影傳統的傳承,也要考慮失去獨特價值觀和美學的潛在風險。”前不久,張藝謀在美國《紐約時報》撰文《從中國看好萊塢,是什麼樣子?》,不無焦慮地提出問題。
這也是編劇、理論家、評論家共同的擔憂。“與電影相比,話劇同樣是舶來品。直到老舍先生寫出《茶館》,這門源自於古希臘的藝術才初步完成了中國化移植。時至今日,《茶館》依然是北京人藝的保留劇目,它能夠擁有長久生命力,在於老舍寫進了中國人自己的怯懦與悲鳴。東方式的人情包裹住了西方式的表達,成就了一出經典。”電影《相愛相親》編劇游曉穎追問:今天的中國電影,應該承載怎樣的內核,建構怎樣的文化體系?
“好萊塢歷經百年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文化體系,這恰恰是我們的弱項。”鐘大豐認為,武俠電影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江湖門派、武林規則、俠者風范構成了武俠世界觀,大家都在講武俠故事,在這個體系裡不斷創造創新。他認為,玄幻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體系。“《長城》和最近的《奇門遁甲》《妖貓傳》,都在建立各自的體系,但沒有呼應起來,而且這套體系很大程度依賴西方的技術、敘事、審美經驗。於是,我們看到武打越來越像日本,怪獸越來越像好萊塢,我們何不回到自己的文化傳統?比如,依據《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演義》等建構中國人的想象空間。”
2017年,一些非好萊塢敘事讓中國觀眾耳目一新。印度的《摔跤吧!爸爸》、泰國的《天才槍手》、西班牙的《看不見客人的房間》,都是將類型電影的敘事法則與本國國情、文化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敘事空間。“今天我們需要考慮的是,什麼是中國電影的敘事空間?這是不是一個可拓展的空間?”《不成問題的問題》編劇梅峰提出。
敘事空間的展開和文化體系的建構,必然牽扯到方方面面。比如,個人表達與市場需求,影像文本與社會現實,常規敘事與觀眾審美的需要等。但有一點,我們不能忽視:學步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們最寶貴的東西。不要想著討好市場,也不要想著討好觀眾,做一個真誠的講述者才能與世界溝通。
2018年的大幕拉開,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征程中的中國電影人,滿懷信心的同時也要認清不足、踏實前行。市場越龐大,越渴求精彩的中國故事。這故事源自生活、折射時代、傳遞價值,也承載著新時代電影人的使命與擔當。中國電影的幸福由奮斗而來!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