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書“香餑餑”該怎麼吃
編者按 公版書一直是出版機構競相追逐的“香餑餑”,近幾年公版書的出版規模快速增長,讀者對公版書的品質要求也越來越高。對於出版機構來說,如何做好公版書?做公版書怎樣才能不侵權?圍繞這些話題,《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採訪了多位業界相關人士,並邀請版權方面的專家進行解答,希望能為行業提供借鑒。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所配的專家導讀成為吸引讀者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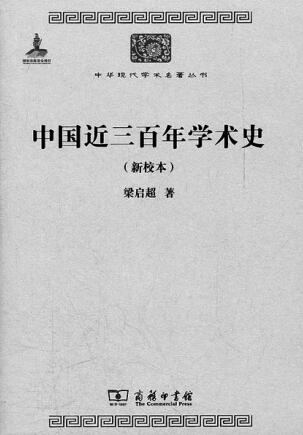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邀請梁啟超研究專家夏曉虹,根據諸多版本匯校、考訂成一部精良版本,增加新版附加值。

經過重新包裝設計的《金聖嘆選批唐詩六百首》,上線20分鐘,5000冊圖書便被搶空。
最近幾年,公版書整體出版規模以及單品銷量都呈現快速增長趨勢。據當當公布的數據顯示,其銷量前五十的圖書中,公版書所佔比重越來越多,從2016年的9%上升至2018年的15%,增長超過60%。
當下,越來越多的出版機構加入到公版書市場的競爭中,深挖公版書的出版潛力,在對舊有的暢銷經典進行重新加工的同時,也在積極開發新的公版書,一些好的作品煥發新生,甚至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公版書形成了一種風潮,甚至是一種時尚。
緊跟時代 受年輕讀者青睞
“我覺得公版書最核心的競爭內容已經不是定價低廉,而是讀者越來越注重的品牌和品質。”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副主任胡文駿根據市場觀察和工作經驗概括道。
2017年年底,由人文社推出的“四大名著”精裝珍藏版,定價遠高於市場上繁多的同類產品,但甫一上市,還是很快取得了銷量上的領先。“可見內容品質的優長(包括文字內容和裝幀設計等)和出版社的品牌號召力已經成為引導讀者購書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說是主要因素。”胡文駿總結道。
胡文駿的這番總結在讀者陳鵬身上得到了印証。從事文化工作的他,喜歡逛書店、買書、在豆瓣上分享閱讀心得,“一般來說,我會選擇有品牌影響力的出版社出版的公版書,比如古籍類首選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學類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事實上,我自己,包括身邊的朋友,會選擇裝幀設計有特色、比較具有象征意義的公版書,送人或者自己留作紀念。有的朋友還以書為媒,喜結姻緣。”陳鵬告訴《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就是買了一套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木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策劃的《金聖嘆選批唐詩六百首》送給暗戀自己的男生,“那個男孩子對她說過自己喜歡金聖嘆,這兩個人真的是因書結緣”。
由木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策劃的《金聖嘆選批唐詩六百首》上線20分鐘,5000冊圖書一搶而空﹔《東坡樂府·雅集》首印一萬冊,也是迅速“秒”光。“我們用極其有創意的設計和想法,將公版書重新包裝,用當今的審美做成文創產品,同時利用專業工號聯合發布,走出了一條制作與銷售的新路。”木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策劃總監朱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道。
“除了內容和品牌,在公版書的發行中找到特別的營銷點也很重要。”胡文駿以《紅樓夢》紀念版為例,“我們將該書整理出版65周年紀念版,與個人閱讀史相關聯。在紀念版新書發布微信推送后,不少讀者在評論中回憶起自己年輕時或父輩們閱讀這個版本的經驗,還有一些讀者亮出自家珍藏了幾十年的老版本,達到了我們希望產生的共鳴共情的效果。”
如今,越來越富創意的裝幀排版,越來越緊貼時代的闡釋解讀,以及別具一格的營銷宣傳,讓公版書越來越受到年輕讀者的追捧和喜愛,進而帶動了更多公版書的銷量。
深耕內容 升華留存價值
公版書除了在裝幀設計、營銷方面下功夫,深耕內容品質,增加其本身附加值,才會深化並升華公版書的留存價值。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收錄自晚清至1980年代末的學術名著。出於學術史完整性的考慮,有很多公版的名著繞不過去。“如何才能做到不炒冷飯?我們採取了新增導讀年表、請專家重新校訂等方式增加新版的附加值。”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文史編輯部主任陳潔說。
譬如,其中梁啟超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早已進入公版,商務印書館請到梁啟超研究專家夏曉虹做了“新校本”。據陳潔介紹,夏曉虹與合作者共取了清華學堂講義本、《東方雜志》本、《史地學報》本、上海民志書店本、《飲冰室合集》、朱維錚《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等合計6種本子進行比勘,“夏老師配寫的導讀正是從版本的角度闡釋了梁啟超歷次改定所體現出的學術思想的變化,也說明了校訂工作的意義”。
在與市場上多種版本的角逐中,這本書得以一印再印。正如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先生在“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第二批出版座談會上所說,“在講求‘學術史的思路’與‘經典化的做法’方面,這200本書站得住,而且做得很了不起”。
有時,有些公版書所配的專家導讀甚至成為吸引讀者的一個重要因素。以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例,其版本不下四五十種。作為讀者的王斌,就迷上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軍全做導讀的這一版《中國近代史》,“導讀很厚,差不多有書的1/5,但是就是這份導讀,讓其從幾十個版本中脫穎而出”。
在王斌看來,出版機構在做公版書時,要有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要堅持社會效益優先的准則,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把好的作品挖掘出來並傳承下去,要有一種定力。
他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國維集》為例,“這套書可以說匯聚了王國維先生一生非常深刻的學術作品。與他的《人家詞話》相比,這套書做下來,很費功夫,並且讀者市場也不如《人間詞話》。即使這樣也應選擇去做,是因為其所具有的學術傳承價值和意義。”王斌表示,出版機構在做公版書時,要肩負起文化傳承的責任。
陳潔也表示,出版機構在做學術公版書時,有時需要有超前的判斷力和堅定的自信心,方能耐得住寂寞,也才能做出精品來。
做成精品 挖掘現實意義
精品迭出,很多書重新煥發新生,並形成了新的時代意義,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出版規模和銷量呈快速增長的公版書,在帶動文化繁榮的同時,也始終面臨著盲目扎推、重復生產、劣幣驅逐良幣、隨意侵權等一系列問題。正所謂“瑕不掩瑜”,在圖書市場日漸成熟的當下,針對公版書再開發豐富圖書供給,也引發從業者們的思考和探討。
在王斌看來,公版書更要注重加強選題策劃,“‘公版書有什麼好策劃’的這種觀點,擱在十幾年前可能還算合理,現在肯定是行不通的。一家出版社對於如何去做公版書,要有自己的出版規劃,這相當於其自身發展戰略,或者趕市場熱點或者填補市場空白”。
“做公版書要有精品意識,因為其具有留存和傳承價值。”王斌表示,面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公版書,隻有做成精品,才對得起這部作品。
對此,陳潔也表示認同:“作為出版從業者,更應該盡最大努力提供最有品質的精神文化產品,面對讀者,我們責無旁貸。”她坦言,校書如掃落葉,常常“如芒在背”,唯恐愧對讀者的信任。
“公版書一定要挖掘出公版書的現實意義,或者當今時代再出版所代表的時代精神。”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常務副總編輯劉凱看來,公版書要做到“古為今讀”。同時,他認為公版書要根據市場同類書的不同和讀者情況做出差異化,找准不同版本的真正讀者對象。劉凱以市場上兩版《枕草子》為例,一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版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這兩個版本都賣得不錯,雖然都是同樣的內容,但在制作上,反映出編輯的不同理解,面向不同的讀者審美喜好。前者偏大眾化,后者走小清新路線”。此外,劉凱認為公版書還要做出特色來,“要麼版本是最新發現的,要麼是名家新譯的,要麼是名家導讀或注解的,總之要有再版的獨特價值”。
正所謂,“大浪淘沙始見金”,對於泥沙俱下、良莠不齊的公版圖書市場,時間和讀者才是最好的“試金石”。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