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老鐘
老鐘,鐘立群,離開我們已經13個年頭了。可他滿臉笑容的形象卻總是時不時在腦海裡出現,心裡因此也會升起欠他“一筆債”的感覺,時間愈久,欠債感愈深。
我可以名副其實地叫他一聲“師傅”。七十年代那一天,我到王府井報社辦公大樓報到,經濟部農村組李克林老太太二話不說就把我帶到隔壁小辦公室,說“你就跟著老鐘吧”。靠窗右側背對著門的老鐘轉過身來屁股不離座椅,滿面笑容地伸出手來。從此我就“跟上”了他。四十多年了,這一切好像發生在昨天。
辦公室就我們兩人,窗子兩邊一人一張辦公桌。互相略作介紹,立即開始了“學徒生涯”。他交給我幾份他身邊的稿子,有編輯過的小樣,有未經編輯的來稿,說你把它們拼成一塊版。說實話,編稿馬馬虎虎還可以,可版面怎麼拼?真的一無所知。他把工作流程一樣一樣告訴我,然后便是我自己開始實踐。從跑活板車間開始,編稿、發稿、出小樣﹔畫版、拼版、出大樣﹔標題制作、字數刪減,版面美化﹔小樣再編輯,大樣再修改,稿件送審。大標題幾號字,小標題幾號字。一樣一樣,不厭其煩,一一教來。新人版面不熟,碰到難題在所難免。老鐘往往不急著給你解難,逼你“走投無路”,再來點撥。這個辦法極靈,一次成功,記憶尤深,不會再犯。就這樣,在他的指點下,很快找到了感覺,進入了“自由王國”。不知道其他年輕人走上工作崗位后有沒有走過一些彎路?我,因為“鐘師傅”,起步階段順風順水。

人民日報經濟部老同志春節聚會。后排居中高個者為鐘立群。
人民日報編輯部業務部門歷來編採合一,在家當編輯,出門是記者。老鐘一輩子當編輯,好像沒有當過記者。編輯是他一輩子職業,也是他一輩子追求,更是他一輩子背負的責任,一輩子樂在其中。每當他認真瀏覽完一篇來稿,一支煙點燃在手,陷入久久沉思時,我便知道,一篇重要來稿將要推上報端,不會打攪他。老鐘編稿時“進入狀態”的樣子,會讓你感覺他在美美的享受一頓精神大餐。他的靈魂似乎也在稿件中隨著文字在遨游。我常常被他那專心致志的精神所感染。那時候,農村組人手少,季音、姚力文等幾位大家還沒有加入團隊。李克林老太太得力助手就是老鐘和老宋(宋錚)。但凡重要來稿,均經他們之手。老鐘編稿,不厭其煩。往往初稿就反復推敲,小樣一改再改,大樣仍不放過。無論哪個部門,稿子改動的多,年輕人就要連續跑活版車間,因而少不了受大師傅的“刺”。邱師傅拼版技藝精湛,做得一手快活,人也直爽,沒有壞心。但愛開玩笑和“刺”人,大樣改動愈多,他的話也愈多,“刺”的年輕人往往“狼狽而逃”。不過,老鐘編稿,無論小樣大樣,都是字跡工整,一絲不苟。連線條都是精心劃出的,文字和段落刪除部分,整整齊齊劃出方框,再用斜線一筆一筆齊齊的畫掉。添加的文字,整整齊齊列在文章兩旁,用粗粗的線條畫成一個個小方框,再用直線引到添加處。小樣很有美感,我常常不自覺把它當藝術品欣賞。大樣同樣如此。那些小樣和大樣,今天拿出來,說不定可作藝術品拍賣。從沒見過他隨意漫不經心改動一篇稿件,哪怕改動一個字,他都會精心地圈好,然后用一條直線在兩行字中間筆直的引出來,在邊上漂亮地畫個帶尾巴的圈。所以,拼版師傅們看起來很清楚,改起來很方便。由於這種執著和專心,也有人認為他有編輯過度之嫌。說實話,當時我也產生過這種感覺。李老太喃喃地說:“廟在山前,山在廟后,有什麼區別?非要改過來嗎?”老鐘不喜和人爭辯,總是笑呵呵的以笑作答。辦公桌前一坐,立馬又恢復到往日的狀態。稿子好像能使他進入忘我境界,不盡心編得自己滿意決不罷休。后來,我慢慢理解了,這不就是一位披星戴月幾十年的老編輯養成的習慣嗎?在稿件面前,眼裡揉不進半點沙子,精了,還要求精。無論哪裡有點小疙瘩,都要堅持去除掉。
編輯意味著什麼?為他人作嫁衣裳。許多稿件經老鐘精磨細琢,在人民日報重磅推出,成就了他人。和出版社不同,在新聞單位當一輩子編輯不容易,把編輯當做工作的全部更不容易。不求名,不為利,這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我在人民日報許多老前輩中看到,使我發自內心對他們尊敬和尊重。老鐘也常常受命起草社論、評論,至於按語、編后、短評等,更是家常便飯,但就是沒有署名發表過報道和文章。他新中國成立之際即到人民日報工作,不是白班就是夜班,一干就是一輩子。一個能把成就他人當做一輩子的工作和追求,並且樂在其中的人,看是多麼的平凡,但又多麼的不平凡?這就是老鐘,這就是人民日報諸多老編輯。
老鐘被經濟部同仁戲稱為“座鐘”。除了去食堂吃飯,真的沒有見他離開辦公室外出過。每天除了編輯還是編輯。時常有年輕同志過來找他,求教問題,這時候往往是他最活躍的時刻。他對年輕人一視同仁,有求必應,有問必答,非常樂意和年輕同志聊天。那時來報社學習的通訊員多,這些來自各地的同志也常常找他,他很重視這些來自基層的同志,一方面向他們了解各地情況,一方面進行業務指導。沒有架子,沒有隔閡,平易近人。
“座鐘”年輕時其實相當活躍,有過許多不為人知的愛運動歷史。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學做過“兩球”隊長,足球和排球。參加過游泳比賽。不是“健將”,也差不多是個“類健將”吧。他愛好廣泛,那個年代,在報社,不少同志找他修過收音機之類,許多手工活,他都能做。孩子插隊下鄉,他給三個孩子每人裝了一台收音機。女兒鐘嘉英語好過同齡人,就是因為有了這台伴隨她到內蒙古兵團插隊的收音機。她還清楚的記得那年春節回京,指導員還讓她把收音機帶回來請她爸修好了。改革開放微風咋起,一天,在王府井辦公室,老鐘悄悄塞給我一盒磁帶,說回宿舍聽。那是他錄的幾首鄧麗君的歌,如此美妙的歌聲,是我第一次聽到。報社從王府井搬到金台西路,不久,老鐘去了9號樓新聞系教編輯學,我們見得少了。他退休后,又開始專攻電腦。據說,一輩子戒不掉的煙,就是因為玩電腦太專心致志,居然不知不覺戒掉了。我到人民網后,有一次去他家看望,他便和我大談網絡,特別是電腦和手機,興趣不減當年。有些技術的東西我也搞不清楚,他說的頭頭是道。
老鐘到社科院新聞系教學多年,也深得大家喜愛和尊敬。他編輯的一本編輯學教材,至今網上有售。他離開人世時,學生們相約去和他遺體告別,我也去了。他在人民日報報端似乎沒有留下什麼“看得見的業績”(署名),但他和他的同輩同仁們卻留下了一座實實在在“看不見的豐碑”。以此短文,聊表紀念。(來源:“金台天空”公眾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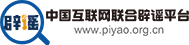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