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記憶場域”的內江:范長江、方大曾和馮雪鬆解讀
2017年6月10日,在范長江故居(紀念館)舉行“《解讀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長江新聞獎得主的閱讀筆記》首發儀式”,深切緬懷中國戰地記者先驅、杰出攝影家方大曾先生。參加首發儀式的有該書的主編、央視高級編輯、紀錄頻道的副總監馮雪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彭莎莉女士,范長江新聞學院顧問、范長江長子范蘇蘇,原中國攝影出版社副社長陳申先生,原四川日報高級記者、方大曾外甥張在旋,還有原解放軍報高級記者、少將、中國軍事文化研究會攝影藝術中心主任江志順先生等11位“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以及內江市和東興區新聞工作者代表,東興區部分單位干部職工代表。我參與在內江的系列活動,見証了范長江、方大曾的精神傳承和弘揚。如何表述我的見聞?我想用“記憶場域”來解讀。
“記憶場域”,是法國歷史學家Pierre Nora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概念﹔有三個構成要素:物質性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它是在記憶與歷史的互動中產生的﹔它最初的出現必須由一種意志的力量來推動,即想要回憶的願望。用“記憶場域”來解讀范長江、方大曾和馮雪鬆的對新聞事業的貢獻,在我看來是恰當的方式,也便於闡釋作為“記憶場域”的內江。

首發式馮雪鬆發言 肖亞光拍攝

馮雪鬆、彭莎莉和范蘇蘇向范長江紀念館贈書 肖亞光拍攝
物質性的活動場:范長江故裡
四川內江是范長江的物質性的活動場。他出生、讀書在此﹔他成名后又在故裡建立了“范長江紀念館”。他的故居和紀念館,成為做新聞、學新聞、研究新聞人的“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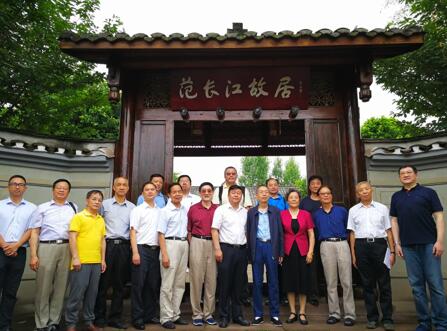
與會者在范長江故居前合影
首發儀式結束后,來賓參觀“范長江紀念館”,館內以實物和展板介紹范長江的生平業績。
范長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於四川省內江縣趙家壩村,今屬內江市東興區田家鎮。他青少年時期家道中落,靠母親的手工勞動來維持生活,供其上學讀書。他是范仲淹的第31代孫(范長江紀念館副館長段瑞明首發式座談會發言),祖父是清末秀才,幼時由祖父啟蒙,后到離家7裡多地的田家場去讀小學,1923年秋考入內江縣立中學。內江位於沱江中部,兩岸有稻田,翠綠的甘蔗,又有美麗的小山,好像一幅明媚的山水畫,留存給人們美好的記憶。
1927年,因廣州的革命政府遷到武漢到內江招生,范長江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憂而憂,后天下而樂而樂”為己任,到吳玉章所辦的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學習。期間,重慶發生了“三三一慘案”,血腥的屠殺教育了范長江。他離開了學校,參加了賀龍20軍的學生營,旋即又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起義失敗后,他流落廣州汕頭、福建一帶,衣食無著,險些喪命。1928年考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因不滿“九一八”后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差半年就畢業,憤而離開學校,北上抗日。1932年初到北平,發現並無抗戰活動,度過了一段艱苦的工讀生活,下半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33年日軍侵佔山海關,范長江深感民族面臨的危機,積極參加抗日救援活動,並為北平的《晨報》、《世界日報》和天津的《益世報》、《大公報》投稿,開始了他的新聞生涯。
1935年他以《大公報》特邀通訊員的身份,開始了西北採訪,歷時10個月,經川西,過隴南,走六盤,越祁連,沿河西走廊,繞賀蘭山,跨內蒙古,西達敦煌,東止西安,北止包頭,途徑48個縣市,總行程6000余公裡,進行西北考察。首次向全國人民公開報道了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對增進人們了解紅軍起了重要作用。他寫的通訊陸續在《大公報》發表,后集結成《中國的西北角》,到1937年底,曾連續9次重印。1936年夏天,范長江回到天津,被大公報社錄用為正式記者。
綏遠抗戰期間,范長江到前線採訪,聽到“西安事變”爆發,為弄清事變真相,他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換乘用各種交通工具到達西安。1937年2月3日,他化妝后隻身進入舉世矚目的事變中心西安。第二天,在楊虎城公館見到了周恩來,周便說:“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沿途都看到了。”“我們紅軍裡的人,對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關系,我們很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方蒙:《范長江傳》,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71頁。)后由西安到延安,2月9日夜晚,毛澤東與范長江作了徹夜長談,講解了十年內戰的經過,闡釋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等,使范長江頓開茅塞,豁然開朗,也促進了他的世界觀轉變。
范長江是國內記者進入延安第一人,想留下做長期採訪,但按毛澤東的吩咐,他日夜兼程2月14日趕到上海。胡政之為推動國共合作抗戰,冒風險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的15日,在《大公報》發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大公報》天津版發了全文,上海版被國民黨撿扣去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四項保証。(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62頁。)他的綏遠和陝北採訪的通訊在《大公報》發表后,又集結成《塞上行》出版。
名記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永存。范長江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勇於深入第一線。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在槍林彈雨裡馳騁,出生入死,為民族的解放,祖國的新生做出了不懈努力。他的西北採訪,跋涉於原始森林,爬雪山,過沙漠,乘羊皮筏子渡河,歷盡艱險,見人之未見,聞人之未聞。他做戰地記者,總是設法跑到前沿陣地,跑到戰壕裡,了解實況和戰士們的情緒,進行報道。“八一三”他在江灣前線﹔“台兒庄大戰”他就在離台兒庄1公裡半的南棠棣鋪的前線指揮所,目睹了我部隊乘勝追擊,敵軍狼狽潰退的情景。范長江滿腔家國情懷,滿腹經綸才學,艱苦卓絕採訪,有重大價值的報道,引入入勝的寫作,奠定了他在新聞界的地位。正如《大公報》老報人陳紀瀅所言:“民國二十四、五、六年間以及二十七年5月以前,《大公報》上‘長江’筆名所寫的通訊稿,可以說真是膾炙人口,紅半天,受到全國人士的注意。”(轉自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63頁。)范長江有抱負,有理想,他說:一個記者的名字,如同工廠、商店的招牌,工廠商店的名聲搞壞了,就沒人去買它的東西﹔一個記者的名聲壞了,就沒有人去讀他的作品,不相信他的報道。范長江珍惜記者的名聲,“量入為出”,生活在自己正當收入中。范長江的傳世佳作及優秀品德,使他成為久負盛名的記者。
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范長江發起創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培養了大量戰地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歷任新華社總編輯、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等職。
范長江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優秀品德和職業精神永存。1991年設立“范長江新聞獎”, 是中國優秀中青年新聞工作者的最高獎,以鼓勵他們學習和繼承范長江獻身於黨和人民新聞事業的崇高精神。獎勵從1991年起每三年舉辦一次,自2000年起該獎改為每兩年舉辦一次。2005年根據中央關於《全國性文藝新聞出版評獎管理辦法》的精神,與韜奮新聞獎合並為長江韜奮獎。
2009年是范長江的百年誕辰,政府決定以此為契機,籌建范長江紀念館,作為對這位新聞巨子的紀念。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於2006年8月19日,還正式作出了《關於同意修復范長江先生故居的復函》的批示。范長江紀念館總佔地1800畝,其中包括核心區60畝,故居建筑面積1400平方米以及水體面積4879平方米的范長江紀念館。工程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對范長江故居進行修復性建設,並對周邊環境進行設計。根據范長江的工作性質,把中心地帶的造型定為喇叭形,同時在中心景觀上將筆的形態進行變形,將竹捆扎起來,形成筆筒,中心栽種竹子,象征筆杆,再用竹廊連接。碑林和景牆,象征報紙。紀念館展出了范長江的生平業績和“范長江新聞獎”歷屆獲獎人的影像和簡介。
與會者參觀“范長江紀念館”后到“范長江大講堂”的接待室座談。
座談會由范長江紀念館副館長段瑞明主持,先后發言的有:陳申、喬雲霞,二人都是第一次到故居和紀念館,談了對范長江、方大曾的崇敬,學習他們淨化心靈,感恩時代發展使范長江、方大曾兩位摯友在此相聚。喬雲霞還向范長江紀念館贈主編並她寫的范長江的書《中國名記者傳略與名篇賞析》和她作編委寫有范長江的《中國名記者》第五卷。接著發言的依次有:內蒙古日報首席記者、第七屆范長江獎獲得者劉少華,重慶日報首席記者、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代表、第六屆范長江獎獲得者羅有成,江志順,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第二屆范長江獎獲得者於寧,今時代傳媒總經理、第八屆范長江獎獲得者趙拴,山西廣播電視台駐外記者管理中心主任、高級記者、中國視協媒體融合推進委員會副秘書長、第六屆范長江獎獲得者肖亞光,他們都在范長江100年紀念會來過,感到紀念館越建越好,每次來都很受感動,都很受教育,都是一次加油、鼓勁。他們都為《解讀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長江新聞獎得主的閱讀筆記》寫了文章,表達了他們對方大曾的震撼、折服,發言中都表示傳承范長江與方大曾精神,做時代的記錄者、守望者。最后段瑞明、陳澤清作了總結性發言。
物質性的活動場把現實的場景與過去的記憶鏈接起來,讓我們身臨其境,深受教育,由衷地表示要沿著范長江與方大曾的家國情懷指引,為實現“中國夢”,堅定、努力前行。
象征性的:范長江、方大曾在內江相會
為什麼在范長江故居(紀念館)舉行“《解讀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長江新聞獎得主的閱讀筆記》首發儀式”,緣於馮雪鬆2016年4月15日拜訪新聞學界泰斗、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學術總顧問、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博士生導師方漢奇先生。方先生對范長江和方大曾的評價:“方大曾和范長江雙峰並峙,二水分流,一個長於文字,一個長於攝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可以並存於世、並存於史、並存於書。”(馮雪鬆在2016年4月15日下午拜訪方先生時,方先生說的,馮有微信發我。)這次活動是象征性的范長江、方大曾在內江相會。

方大曾
范長江與方大曾相識,並介紹他擔任上海《大公報》戰地特派員,二人成為摯友。范長江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寫到他對方大曾的印象。(見馮雪鬆主編《解讀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長江新聞獎得主的閱讀筆記》中,范蘇蘇《方大曾與我的父親范長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北平人,1912年出生於外交官家庭。殷實的家境給了方大曾痴迷攝影的物質基礎。1929年,17歲的方大曾發起成立中國北方第一個少年攝影社團。“少年影社”曾舉辦過展覽。自那時起,方大曾對攝影的感情,就從愛好逐漸發展成職業情結。1930年方大曾考取中法大學經濟系。第二年他在大學裡參加“反帝大聯盟”,參與編寫機關報《反帝新聞》,第三年,他又聯合詩人方殷共同主編《少年先鋒》,直到方殷被捕。大學畢業后的方大曾來到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和吳寄寒、周勉之等人成立“中外新聞學社”,他立志成為一名出色的戰地記者。“九·一八”事變后國難當頭,他以相機和文字為武器,為抗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初期題材的攝影作品,如《日軍炮火下的宛平城》、《奮勇殺敵的二十九軍》等。1936年12月他來到綏遠抗戰前線,進行了長達43天的採訪,完成《綏東前線視察記》。在綏遠前線,他拍攝了數百張珍貴的照片。方大曾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攝影記者,他是“七七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在1937年9月18日在河北蠡縣寄出他的文章《平漢線北段的變化》,9月30日他的這篇文章刊登在《大公報》上,從此就沒有消息了。在當時,他與范長江等人齊名,在抗戰前線失蹤,時年25歲。
1936年,方大曾和范長江相遇。這雖是第一次見面,但兩人深感神交已久。范長江了解到方大曾做戰地記者的志向,引薦他到上海《大公報》工作,方大曾自此正式用“小方”的名字,在戰場發回報道。范長江對方大曾印象很好,在《憶小方》(見《范長江文集》)中寫道:方大曾碩壯身軀、面龐紅潤,頭發帶黃的斯拉夫型。“被人叫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們朋友心裡佔據了很重要地位。”“盧溝橋事變了,在盧溝橋長辛店保定一帶,我們又常常碰頭,他的工作情緒愈來愈高漲,身體也愈來愈結實。北方的夏季,他穿著短褲襯衣,自己帶著他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漢路前線不斷地突擊。他那誠摯、天真、勇敢、溫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在抗戰初期范長江主編的幾本戰地通訊集中都收錄了小方寫的文章。在1937年11月出版的《西線風雲》一書中收錄了小方的《從娘子關出雁門關》及《血戰居庸關》。在1938年9月由生活書店出版的《盧溝橋到漳河》中又收錄了小方的三篇文章:《保定以北》、《保定以南》和《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在1938年1月由生活書店出版的《淪亡的平津》一書收錄了小方寫的:《前線憶北平》,封面寫的是:“長江小方等著”,版權頁上:寫著者長江和小方。
范長江對方大曾的消失,初始不相信,之后多次懷念和尋找。在《憶小方》結尾寫道:“我相信他不會有問題,因為他的機智,足以應付非常事變,他的才能也應該為中國新聞事業,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多盡些力量。”雖然小方失去消息一年了,但是范長江還相信並期盼著小方“不會有問題。”之后,范長江多次在文章中懷念方大曾,到新中國成立后,還利用一切機會,不斷地打聽小方的下落。(范蘇蘇《方大曾與我的父親范長江》人民網-傳媒頻道2015年12月09日16:57)
范長江和方大曾是肝膽相照的親密戰友和同事。我們在內江完成了他們兩人的再相聚,是靈魂的、職業精神的聚首﹔是 “長江精神”、“方大曾精神” 的融合﹔是我們以范長江和方大曾為榜樣,堅持為國家復興,職業精神的守望。
功能性的:馮雪鬆在傳播職業精神
物質隻能留在從前,精神卻將穿越時代,世代相傳。馮雪鬆18年尋找方大曾是在傳播職業精神。他從塵封的歷史中重現方大曾的人格與光輝,充分彰顯了社會進步中的國家責任,是對所有為抗戰勝利獻出生命、做出貢獻的新聞界先驅們最好的紀念和懷念!
18年前,一次偶然的“相遇”,讓央視高級編輯、導演馮雪鬆與方大曾結下了一世的“情緣”。1999年,時任央視《美術星空》編導、29歲的馮雪鬆收到了一份希望合作推廣關於抗戰初期戰地攝影記者方大曾書籍的傳真。這份傳真竟然牽出了一個精致木盒中837張珍貴的歷史底片(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的晚輩捐獻給國家博物館),方大曾的攝影作品深深地震撼了馮雪鬆。他覺得:這些優秀的攝影作品不應該被埋沒,小方應該被我們的民族永記。職業的敏感使馮雪鬆向台裡報批拍攝《尋找方大曾》紀錄片選題。
《尋找方大曾》紀錄片拍攝不順利,馮雪鬆為尋找“失蹤”的方大曾化費了許多心血。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結果比較理想。
在接到編導選題的同時,馮雪鬆的父親卻被查出了重症。在這個選題還沒做完時,57歲的父親就離他而去,僅用三天處理完了父親的后事,他就返回了攝制組。
先期採訪開展的也不順利。他最先從北京圖書館的舊刊庫開始尋找,埋頭苦讀四個半月,在三十年代的書山報海中查找著與方大曾相關的信息。當《盧溝橋抗戰記》《奮勇殺敵的二十九軍》《集寧防空演習》《血戰居庸關》《抗戰圖存》《日軍炮火下之宛平》等一篇篇通訊、一幅幅的照片被陸續找到后,方大曾的戰地足跡隱約浮現了。隨后,馮雪鬆給當年方大曾,曾經出現過、採訪過的地方發去信函,希望找到線索、信息或者得到幫助,但石沉大海,均無回音。馮雪鬆沿著方大曾的戰地足跡,自費前往方大曾過去採訪過的地方。他一個人或火車或汽車或步行,從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縣,去史志辦、博物館、報社查找資料,詢問情況,也常被拒之門外,還被當作過假記者。好在一路尋找,一路宣講,小方的事跡感動了越來越多的好心人,如保定史志辦主任孫進柱等。孫進柱在報紙上發表《加入尋找方大曾的行列》《踏著方大曾的足跡》等文章,並帶馮雪鬆尋找戰爭遺跡、查閱地方志、描繪戰事圖、訪問知情人。艱苦的尋訪,雖然找到與小方直接關系的內容不多,卻播撒下了尋找方大曾的種子,堅定了尋找的決心。
馮雪鬆終於制作出了精良的紀錄片《尋找方大曾》,穿越歷史的塵埃,將方大曾的生平事跡在現在熒屏。紀錄片《尋找方大曾》,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特等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全國好新聞一等獎、中國電視文藝星光獎、中國電視金鷹特等獎、中國新聞史學會“新聞傳播學學會獎”組委會特別獎等。
馮雪鬆用16年的時間發掘出了許多極其珍貴的史料,完成了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把一個80年前為國捐軀的年僅25歲的戰地記者的高大形象復原后展現給讀者。馮雪鬆從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專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到2015年7月7日方大曾紀念室在保定市光園落成,再到“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后到目前專著《解讀方大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通過不斷地努力、發掘、推廣,讓中國的羅伯特·卡帕——方大曾,重新回歸當代人的視野﹔並被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成為在中國新聞史上與范長江並肩而舉足輕重的人物。
馮雪鬆近兩年來,通過業余時間,自掏腰包,不收講課費進行公益講座20場,使方大曾的精神和事跡在社會及高校學子中得到廣泛傳播和認知,這既是對先輩的緬懷,更是對於未來的責任——弘揚一種職業精神,家國情懷。
“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一覽表)
(2015年9月至2017年7月)
第 1 站 清華大學 第 2 站 中國傳媒大學
第 3 站 北京大學 第 4 站 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
第 5 站 復旦大學 第 6 站 暨南大學
第 7 站 汕頭大學 第 8 站 中央民族大學
第 9 站 廈門大學 第 10 站 河北大學
第 11 站 天津師范大學 第 12 站 重慶大學
第 13 站 鄭州大學 第 14 站 北京工商大學
第 15 站 山東大學 第 16 站 華中科技大學
第 17 站 蘭州大學 第 18 站 紐約州立大學
第 19 站 東北農業大學 第 20 站 范長江新聞學院
2015年9月23日,清華大學,“方大曾校園行”第一站﹔而在2017年6月10日下午,為期近兩年的“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在四川內江師范學院范長江新聞學院進行了最后一站的講座。“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兩年二十站,十四個省市,一個國外,行程數萬公裡。
在內江師范學院講座時馮雪鬆圖文並茂講述方大曾的品德和作品,講述了他尋找方大曾經歷。范蘇蘇講了《略談方大曾思想形成原因》,解放軍報高級記者、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常務理事、第十屆“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喬天富講了《戰地記者對戰地記者的致敬》,他以兩次參戰的經歷,用照片展示了戰地記者,冒著戰火拍攝的歷史瞬間。他們的講述贏得了廣大師生的陣陣掌聲。
馮雪鬆講座時,常用一幅幅曾經被掩埋在歷史的塵煙中,飽含著新聞人情懷與對戰爭沉重思考的照片與文章出現在講壇的大屏幕上時,聽講的師生被深深震撼了。他們把熱烈的掌聲獻給了這位80年前穿過槍林彈雨,用837張底片記錄歷史,年僅25歲就失蹤在戰場上的高大、英俊記者方大曾。同時也把掌聲獻給央視高級編輯馮雪鬆,18年來用不懈的尋找,來填補歷史空白,來彌補家國記憶。他對方大曾高尚精神的認同和弘揚,及其新聞理想、職業素養、專業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馮雪鬆尋找方大曾及公益校園行,已成為佳話。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