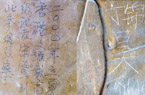【聚焦戛納】
中國電影市場處於井噴期,這似乎是一個事實。相較而言,這幾年中國電影在國際上引起的話題卻少之又少。如果沒有《天注定》,戛納電影節真成了一場中國明星紅地毯節了。
戛納電影節見証了中國電影的成長。本屆電影節,隻有三部華語片與戛納產生了關聯。一部是杜琪峰的最新商業片《盲探》,與競賽無關,更像是一次營銷﹔一部是中國香港新銳導演劉韻文的《過界》,入圍一種關注單元,顆粒無收﹔最值得關注的,隻有賈樟柯的《天注定》,這部影片以一種不可想象的高調態勢,獲得最佳編劇獎。盡管沒有讓中國人再次感受到金棕櫚的魅力,但賈樟柯仍像孤膽英雄一樣向法國人宣布了中國藝術電影的一絲脈搏,只是這次宣示來得過於悲壯,它可能很快就被新上映的商業片所替代。
這幾年國產商業電影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格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傳統的以馮小剛、張藝謀為代表的商業片格局,轉向了不斷涌現的“新人”導演,他們都是在電影業積累了大量經驗的工作者,又具備敏銳的市場嗅覺,能夠與好萊塢影片相融合。在這一點上,對商業電影的價值自然非同一般,我們總不能隻看某幾個導演的作品聊以自慰。可它們始終代表不了中國電影的藝術水准。
另一廂,藝術電影停滯不前。在歐洲電影節的主流裡,華語導演仍舊是以王小帥、賈樟柯、婁燁為代表的第六七代導演,我們實在看不到新面孔,更不要提所謂第八代導演是誰。這些步入中年的創作者保持著自身的態度,面對最困難的環境,堅守藝術,可作品始終未被觀眾接受。我們應該強調觀眾欣賞電影的品位,但另一方面也應該正視,我們看到的許多藝術電影,並不是觀眾真正所需要。藝術電影絕不應該過分糾結在自己的情結裡,正如《天注定》,它們需要冷靜地觀察這個時代,為電影賦予更有力的敘事。接受觀眾的贊譽,也要接受觀眾的批判。市場需要為它們提供更獨立的空間,作品也需要得到觀眾的廣泛支持,這樣才會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其中。不能讓藝術的堅持變成烏托邦,過分自我,隻會陷入一潭死水。
投資者的問題在於,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電影的基本功差,沒有講故事的能力。可是他們所認為的講故事的能力,更多的是在針對一些以好萊塢為代表的主流文藝片。這些電影貌似在敘述現實,實際卻與商業電影並無不同。
創作者另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妥協。更多的人在嘗試如何找到平衡點,既可以讓市場接納,又可以保持自己的藝術本色。這是一種更可怕的自我審查。面對電影節品位的改變,面對主流市場的沖擊,這些曾經信誓旦旦的導演,卻變得中庸,變得謹小慎微。套用《中國合伙人》裡的台詞,究竟他們是想改變世界,還是已經被世界所改變。
李安說,(電影)藝術是有人回應的東西,不是孤芳自賞或是火氣那麼大的東西。觀眾期待有內涵的藝術片,《少年P1》《悲慘世界》引起的關注足以說明這一切。如何回應觀眾的期待?接下來該看電影人的反應了。
□王沐(北京 影評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