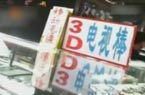【編者按】2009年福建東南衛視記者黃劍開始拍攝中醫紀錄片,三年間走訪300多位民間中醫、道醫,在其個人博客上發布了三百多篇採訪日志,所拍攝的紀錄片也即將在東南衛視播出。作為媒體人,他使普通大眾對於中醫的陌生、懷疑轉向敬佩和贊嘆,成為發掘民間中醫的重要力量。
此文為黃劍供稿,摘錄如下:
經過成都,一位姓王的中醫朋友給我留言,說是可以介紹他尋訪到的脈診高人給我。恰好有半天空檔,我趕緊登門拜見。
最近和脈診醫生緣分不淺,兩個月之間,我居然穿行在金偉老師、陳雲鶴道長、許躍遠老師、余浩兄弟這些脈法高人之間,見証不少脈法傳奇,聽到許多脈法精義。可惜可嘆可恨哪,這些年我粗笨的手指都用來按相機快門、鍵盤打字和拖行李箱了,從沒有想過用心學習脈法,甚至沒有完整看過一本脈書,錯失了許多學習脈診的良機。
“我們拜訪的老師叫王敬義,”年輕的骨科中醫小王在按門鈴前很認真地對我說:“黃老師,這位王老師脾氣有一點怪,說話很直接,如果有什麼不合適你不要介意啊。”
放心!我對小王說,我曾經見過一個據說三十年不出戶的的脈診醫生......Z醫生跟我說“后會無期”......三申道人曾經被關在洞裡八年背誦《秘傳黃帝內經》、為了嘗藥所有的牙齒都掉光了......許躍遠老師的三個手指頭除了摸脈來不做事......“這幾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拜訪怪人,有時候他們也說我很怪呵呵。”
推開王醫生家門,屋裡時尚的歐式家具和電子壁爐讓我眼睛一亮,要知道先前我見到的中醫大師們不是坐小板凳就是太師椅。王老師的手很柔和溫暖,面容平靜,我相信自己的望診能力:溝通肯定順暢。
裝著溫開水的一次性紙杯擺上,開聊。
沒有寒暄,直奔主題。王老師出生在中醫家庭,父親是一位頗有影響力的中醫教授,但是王老師說他的中醫脈診功夫卻不是來自家傳,而是自己摸索出來的。這時候孫曼之、許躍遠、華醫生、Z醫生......等老師的面龐立刻在我眼前浮現,還有華醫生那句鏗鏘的話:“隻要中醫經典書籍在病人在療效在,中醫就永遠不會失傳!”
“我是中醫學院畢業的,但是剛工作時帶我的老師是華西醫大的老師,他不懂中醫,所以我跟著他就隻有搞西醫。在接觸西醫的過程中,我再慢慢研究自己中醫的東西,回到中醫來。”當年喜歡研究難題愛思考的青年醫生王敬義身體特別不好,瘦得皮包骨頭,天天處於生病狀態。“一年365天,我可能有364天都在生病。但是我很喜歡治重症病人,比如說腎功衰,拉不出尿來的,我最喜歡。有時候累了,我躺在值班室的床上休息會兒,突然聽說來了個腎功衰的病人,我精神一下就來了,就去搶救他。我的搶救是先用西藥,等西藥把病人的尿通不出來的時候,我再上中藥。腎功衰的問題,小便拉不出來,醫院常規是用推速尿(一種利尿劑),它還出不來,這個時候我就用中藥,往往幾個小時小便就可以出來了,弄通了。這樣子來驗証中藥到底有沒有效果,我慢慢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經驗。還有像心臟方面的問題,全心衰的問題,慢性右心衰的問題......”
“那現在你治療這些心臟、腎病是中西醫結合?”
“現在純粹採用中藥來治療,足夠了。”
看得出王老師非常感謝那八年的西醫生活,讓他充分接觸到各種疑難雜症急症,讓他充分地對照了中西醫治療的思路。“大概八年后,我的身體不行了,太累了。然后我就調到一所學院的運動醫學系,給學生們上課教中醫內科。接下來我就開始研究脈法了,大概在1991年左右。”
一個在西醫醫院干了那麼多年,親眼見証西醫強大的診斷能力,為什麼還要鑽到那麼古老的脈診裡面?“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而知之謂之巧”,脈診是排在最后面一種診斷法,而且現在很多醫生都說了“如果黃帝老人家還在的話,也會讓病人去做B超X光檢查的!”
王敬義老師不緊不慢地回答:“中醫的特色是脈學,這可以說是中醫的絕學。我是在中醫藥大學長大的,那麼多老師我很了解,沒有幾個能摸脈的,包括我父親,(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看不上我父親的,我還是有點傲氣的。西醫的診斷很清楚,中醫的診斷不清楚甚至是模棱兩可的。我之所以研究脈學,就是因為診脈是絕大部分中醫臨床醫生包括教授們要露尷尬相的軟肋,我就是想搞清楚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真是假。我大概研究了兩年的時間,就覺得還可以,有點深入摸到門邊了。”
“您靠什麼來深入?只是病人嗎?”這個話題我喜歡,每次寫到脈診醫生的時候,我心裡也會跳出很多質疑。
“就是病人,我不太看古書的,一看古書就落入古書那個圈套裡面去了,老是找不到規律。你看從春秋開始,三千年了,歷代醫家那麼多寫脈學書的人,我覺得他們都沒有長進,古代醫生在脈學方面沒有長進的。內經沒人敢去突破它,那不行啊。到晉代的王叔和,他的書我也讀過幾年,反復地讀,我讀書很少,我要研究一個東西就是反復地看它。看到后來發現王叔和的東西指導不了我們,又讀李時珍(的書),讀完了發現也讓人理解不了,李時珍的腦袋也是混亂的,也沒把東西說清楚。所以到后來,我不看書了,還得回到寸關尺這來。我先借助西醫的檢查來推斷指導我的脈診研究,然后再慢慢定位,最后把全身臟器定到了這六個脈上。我的脈診完全定型的花了十四、五年,終於形成了自己的脈學體系。按照我的脈學體系,隻要你一摸就知道,它是什麼樣的臟器什麼樣的病,好比西醫的診斷出來了。比如鼻子的問題,你是過敏性鼻炎還是額竇炎還是上頜竇炎,都能確定出來﹔頸椎的問題,在第幾頸椎我都能定下來﹔又比如前列腺的問題,是增生了還是炎症階段,我都能定它。當然,不是所有的病我都能診斷出來,但是常見病應該沒問題。”
“不是說中醫應該辯証而不是辨病嗎,病有千千萬,每年都有新的病被發現,哪裡摸得完?”這個問題有點專業吧?三年中醫啊,這日子沒有白過,問完問題我有點小得意地望著王老師的眼睛。
“對,辯証是中醫脈學裡靈魂的地方。”王老師捋了捋額前散亂的頭發,“我先定位,比如鼻子吧,它的定位應該在這兒(右手寸部),最淺的一位,我叫的第一位。我在這個地方來摸,在第一位不應該出現脈,但是它出現了,就說明你的鼻子有問題,接下來我再定到底是受風寒還是風熱引起的,根據脈象上的粗大、細小、有力還是無力,我來定它了,這就辯証了。如果是受風寒引起的,應該是個緊脈,那我用疏風散寒的藥就可以治療你的鼻子,它就好了,就很簡單。如果是風濕,它是細的一個脈象,那麼在第一位出現一個細脈,那就說明有濕邪,就會出現頭部沉重,頸肩沉重等症狀,就辯証了,把西醫的辨病和中醫的辯証結合起來,特別好。你看我這個辯,有濕邪在頸椎上,我首先定你的頸椎有問題,然后再定出來是風濕,這樣症狀就可以定下來,症狀都是可以定的,比如手發麻、沉重。如果我在第一位摸到很大的一個脈象,它是風,風可能引起眩暈的,這個時候我定了頸椎的位置,病人這個地方會疼的,我都知道,通過摸脈就知道了。所以說,中醫的辯証和西醫的診斷就結合起來了,我們就採用先定位再定性,你定好了后就不會有偏差了.比如說頭痛,引起頭痛的原因太多了,你怎麼去定它呢?病人就說頭痛,醫生問他是怎麼個痛法,熱痛、脹痛…..病人有些時候是說不清楚的,全靠號脈來定它。”
“有一個人跟你研究脈診的路子簡直一模一樣,從外科醫生出來的,他叫許躍遠,明天我就要去合肥會他。”話音不落,“指下尋形心中成像”的許老師濃眉大眼的形象已經活脫脫現在我眼前。
“許躍遠,我知道,他寫的書叫《中華脈神》。”王老師轉身取了兩本他寫的《脈論》交到我手上,說是一本送給我,一本送給許躍遠老師。
我跟王老師匯報自己和醫生們組織了兩次道醫會,把我尋訪到的好中醫聚在一起,要求每個人要把絕活拿出來互相獻寶交流,“如果一個醫生學了十個醫生的本事,就不得了,中醫一下就起來了。以后道醫會我們准備按照主題走,比如脈診大會,把十個頂尖的脈診老師聚到一起,大家一起來談是怎麼摸脈的,辯証思路是怎樣的......”我眼前又來了畫面,激動起來:“我一定要拉一幕大帘子,從帘子中伸出幾隻手來讓大家摸脈辯病,這些病人身上都揣著醫院的最新檢查報告......”
王老師兩眼放光:“對對對!我也有過這個想法。來十個病人,帘子拉上,給病人排上號,我們脈診醫生坐在這兒摸,他有什麼問題都寫在紙上,最后來看,咱們中醫的脈診對不對准不准,這樣才能考出水平來。我太希望這樣的機會了!”
“有一天我會把幾位老師都聚到一起,來個英雄會。據我所知,東北還有一位叫四叔的,在農村裡面,也自學了一身高明脈法,還有福建北部有一位危醫生......西安還有一個脈診老師,是個回民,三十年不出門,瘋狂地研究脈法......許躍遠老師當年摸牙膏,摸壁虎尾巴,摸樹葉,什麼都摸,有十幾年時間拒絕所有的社交活動,完全投入進脈診的三寸之地......
“他為什麼要摸這些東西呢,我理解不了。”
”他想表達出脈象的狀態,想通過生動形象表述出來。有一天他把自己關在衛生間裡摸牙膏摸時,忽然開悟了。您是什麼時候開悟了,是循序漸進還是突然有一天豁然開朗?”
“突然的,的確是突然的!摸多了脈,摸久了之后,突然有一天摸到這個脈,好像就全部都通了,就是有這麼一剎那,一下接通了。”王老師看上去一臉的幸福,像是回憶起自己熱戀的那段時光。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