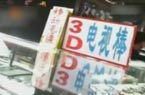【編者按】2009年福建東南衛視記者黃劍開始拍攝中醫紀錄片,三年間走訪300多位民間中醫、道醫,在其個人博客上發布了三百多篇採訪日志,所拍攝的紀錄片也即將在東南衛視播出。作為媒體人,他使普通大眾對於中醫的陌生、懷疑轉向敬佩和贊嘆,成為發掘民間中醫的重要力量。
此文為黃劍供稿,摘錄如下:
“對於未來我有三個目標。第一個,我希望能把中醫推進一百年!”兩斤黃酒下肚,任之堂主人余浩舉在半空的酒杯有點晃動。聽了這個圓臉雙下巴的年輕醫生的雄心壯志之后,我忍不住再次端詳起他來,他扣在酒杯上的手指甲縫黑乎乎的(每晚做藥丸留下的印記),但是小瞇縫眼卻越來越亮了。“一百年不算長,我聽說自秦漢以來,中醫慢慢遠離道家后,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我的第二個目標,把我的《醫間道》的稿費成立一個基金會,每年再投入一點錢進去,幫助那些成長中的中醫,推動中醫發展。”黑指甲把酒杯舉得更高了,接著用濃重的湖北腔大聲宣布自己的第三個目標:“這輩子永不收診費!
“一個永遠不收診費的中醫?”
“這個我支持!”回答我的是可愛的余太太,一位感冒了吃中藥的西醫碩士,“三個目標我都很支持,《醫間道》的稿費我們都預留在那了,隨時可以拿出來。”
“收診費會耽擱很多病人。有個外地的病人找我來看病,她在北京很多中醫堂看診,一個星期號一次脈,350元的挂號費,她看了六個月,光診費就七、八千塊錢,最后實在看不起了。”醫生把他的眼睛瞇得更小了,“老百姓大都是窮人,一個小孩子發燒、積食等病,我們一塊錢可以解決問題的,結果挂號要五十、一百,這不是麻煩了嗎?還有那些靠最低保障收入維持生計的人,別說吃藥,飯都不要吃了。 挂號費三百四百,病人看一次病看不好的,尤其是慢性病,一看三五個月要花大筆錢,窮人根本沒法治。他的病看不好,最后都不敢看了。所以診費擋了一大部分窮人看病......”
我想起羅大倫筆下一輩子治病不收錢的許叔微, 想起一年前醫生們討論的“谷賤傷農”,還想起老祖宗說的“千家吃藥,一戶出錢”,想起老中醫說有錢病人給個金蛋,沒錢病人給個雞蛋......
採訪任之堂主人余浩是一年前看了《一個傳統中醫的成長歷程》之后的計劃,在他的書裡,我看到一個叫“東娃子”的民間中醫成長故事,他四歲在太爺爺身邊開始感受中醫,七歲學習陰陽,八歲學脈診,九歲學望診,十二歲學五行......之后二十歲上湖北中醫學院,二十九歲開始行醫。這樣“血統純正”的中醫現在還真不多! 遭遇 了兩次婉拒之后,我終於在 濟南和福州兩位朋友的幫助下,敲開了他的門。
早上八點半, 走進任之堂大藥房,我第一眼落在地板上一個大大的陰陽圖上。在余浩的書裡有不少篇幅介紹他向道家學習傳統醫學的故事。藥房一百平米不到,充滿了濃郁的中藥的氣息。我躲在角落,靜靜地開始感受這個中醫學院畢業十一年,但已學習中醫三十多年年輕的“老”中醫。
最早進診所的是南京來的病人,一家來了五口。 像我認識很多“中醫家庭”一樣,人到中年的媽媽們是家庭健康的守衛者,也是最忠實的中醫追隨者。她不僅張羅一家人排隊待診,還拿出筆記本把醫囑記了又記。
“余醫生,我女兒女婿看病都可以報銷的,可是他們還是要跑到這麼遠來找你看。”
余浩正專注地在切脈,像是沒有聽見。余浩看病,不切脈不開方,如果你是個內向的病人甚至不需要開口。
一個老漢模樣的人佝著背住著拐杖艱難地推門進來,除去衣帽,原來是個年輕人。這位來自浙江的小伙子得了強直性脊椎炎,已經在余醫生這治療兩個月。現在在任之堂求醫問藥的病人有一半是來自外省。
看見我正舉著攝像機,對我微微一笑:“你是油麻菜吧?就知道你會來這裡的!”
這話聽得我心口一熱,慢慢地,我發現自己不是在做一件簡單意義的紀錄工作,而是跟更多的人的生活聯系在一塊。就像有的中醫留言,說在我的尋醫訪道故事裡,發現自己不再孤單。
特別喜歡看余醫生微閉眼睛在號脈的樣子,就像欣賞一位畫師在做畫,一個數學家在解題,一個將軍在排兵布陣。在他切脈時,我還能看到在那遙遠的小山村,一位老人為了教一個七歲的娃子學會切脈,讓他捉泥鰍、放風箏、切水、吹笛子......的畫面。
一個人的文字可能會騙人,但是一個醫生看病人的眼神很難騙人。
有的病人請余浩診病開方之后,拿著方子不付診金就離開了,對余浩來說很正常,對我來說很震撼。這兩年我見了多少中醫對自己的方子藏了又藏,對病人惜字如金。 余浩給病人開的藥方一般兩天。治病如打戰,戰局瞬息萬變,“病人要是因為害怕診費不敢就診,那不是貽誤戰機了?”
在診室邊還有一個熬藥間,有七八個爐灶一字排開,呼突突地噴著藥香。隻要一塊錢,病人就可以在這熬藥。
“我在最困難的時候,一天隻掙到29塊錢。”也不過是六年前的事,當時余浩的第一個藥房開在一個垃圾回收站邊,對面是個夜夜笙歌的歌舞廳。為了防賊,年輕的余浩醫生每天晚上都住在藥房裡,睜著眼睛等待又一隻在天花板上狂歡的老鼠落下來......
大約有三年時間,余浩寂寞地守在那個小小的藥房,每天還在一塊黑板上更新著健康知識板報。
“有人來看板報嗎?”
“當然有,很受歡迎呢!”來看板報的是周圍工廠的工人、農民、拾荒人......“那時候我一個人守著藥房,看病經常會誤了吃飯時間,鄰居們就經常給我送飯、送水餃。”一個年輕的中醫和一群底層生活的百姓就這樣相濡以沫度過了三年時間,這三年,余浩更加刻骨銘心地感受到百姓看病的不易。
“后來我搬藥房的時候,有一個拾荒的阿姨還送我一個紅包呢!”那個紅包有一百塊錢,八張五元的、六張十元的鈔票,用一根牛皮筋扎起來,余浩的眼睛濕濕的,“我會一輩子留著這個紅包的。”
任之堂的工作人員隻有倆,余醫生和小周。每天早上八點半之后,他們倆就像上了發條一樣停不下來。
“每天晚上,余浩要上網回郵件、寫博客、寫書、做藥丸......”余太太心疼地說:“有時看他很累,想幫忙搓藥丸他還不樂意,嫌我做的大小不一。”難怪每天看見余浩的指甲縫總是黑乎乎的。
“太累了!病人永遠是看不完的。以后每天上午正常上班,下午抽時間爬爬山,訪訪友,看看書...... ”這是上個月余浩在自己博客上的留言。在天氣好的時候,余浩就會帶上病人去爬山、打坐、唱歌...... 他說自己的小診所靠賣藥就可以養活自己,此外他還有一些寫作的收入,這個農民的孩子很誠懇地說:“錢夠用就行。”
為了照顧我這遠道來的客人,余浩決定抽空一天陪我上武當山走走。這三年來,他隻出過一次遠門,“因為總是有外地的病人,他們來一趟不容易。”
在去太子坡的路上,余浩摘了一枝兩面針,看了又看,想了又想。 “病人總是在問什麼病用什麼方子來治,其實這是沒有意義的。治病沒有好方子,隻有適合的方子。病人千萬不要盲從,一看別人進補就都進補,一聽見醫生倡議爬山就都爬山,大家打坐就都打坐,這是錯誤的。比如性格很沉穩的人就不適合打坐,他們氣血沉穩,上焦陽氣不足,這類人需要唱歌跳......有一些人呢,心浮氣躁氣往上沖,他需要打坐,搓搓腳心......”
一進到山裡,余浩的心情就特別愉快,停下來休息的時候話題永遠還是診病治病。“我跟你說一個偏方吧,我用它輕鬆治好過抑郁症!”天哪,又撿到寶貝啦!
“ 背誦《清淨經》!”余浩笑得滿臉陽光,“這方子對一些病人非常奇妙,我跟病人說隻要不開心或是感覺消沉的時候就開始背誦《清淨經》,真的治好了三個!”
“經常有中醫學院的學生來求學,我發現有很多人居然不相信脈診!”余浩放下手上的水杯,轉身指著遠處的山, “這脈象和眼前的山勢很像,看山勢不能隻看一座山,至少要看三座山,你看遠處的那三座山中間最高,就像人體中焦淤積很厲害。另外三座由低到高,那就是脈勢上行的。號脈看脈勢,就像看風水看地勢。抓住脈勢,調氣機改變不良的趨勢讓身體平衡,問題就解決了。因此癌症腎結石感冒都一樣是病,不要執著在病名上。”是啊,好像足球場上的后衛,放棄對對方進攻隊員的防守,一味跟著球跑,一定容易犯錯誤,因為你多半跑不過球。“看病最主要是守五臟,抓住氣機,順勢而為。”
“舉個例子吧,有個病人就診,切脈時左關淤得很厲害,這多見於膽結石或者膽囊內壁毛糙,患者說檢查過了,正常。病人的心脈也很好,我就問他有什麼不舒服症狀,他說膝蓋疼,上下樓困難。那會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我就想膝為筋之府,肝主筋,這個脈象反應的肝臟和它所管轄的范圍出了問題。所以膝蓋疼,我就為他調肝,養肝血,膝關節很快就舒服了。我們不要被病牽著走,比如飛蚊症、指甲枯黃像瓦片一樣粗糙、這些都是和肝相關的病,你不要眼睛疼治眼睛,指甲問題治指甲。你要調的是全局,改變的是狀態趨勢。好比你想要放倒一棵樹,必須砍樹兜子,不砍樹枝子。”
“治病最高層次是道,作為醫生要努力學習用道的運行法則來治病。好比要調整上熱下寒,不能隻考慮清上焦火或者補腎火,如果補下焦的火,很可能病人就上火了,如果清心火,病人下面沒准就更涼了。上熱下涼,是因為他身體內部陰陽轉換不順暢,你隻要把他的氣機調順,引導他的陰陽轉換就行了。打個比方,一個地方物產再豐富,但是物流不行,它的產品也隻能瘀滯在本地,腐爛變質。如果物流交換通暢,流通好了,就都是財富。”
“人體也是這樣,你把上面的火引到下面來,它就變成好東西,能補腎火。把下面的寒引到上面來,心火就下去了。 我們不要急著去補和泄,而應該先去協調,這樣才是道法自然。”
“再往下一個層次治病是根據陰陽,用陰陽的角度看問題,也很簡單。之后是五行,通過調五臟來治病。最下的治病是在萬物的層次上治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樣往往太復雜,沒法治。”
在一天門通往二天門的路上,有一道多達三百級台階的又長又直的高坡,我用攝像機的長鏡頭遠遠紀錄下余浩一個人努力攀登的背影。鏡頭裡的他有時候走得很累了,快要爬不動了,頭垂得很低,可是更多的時候他會左右擺動起雙臂,像是給自己鼓勁,提醒自己奮勇向上......
這個鏡頭將會是任之堂主人余浩的中醫故事的片尾畫面。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