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1993年5月1日,《東方時空》首播,該欄目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也改變了投入其中的“電視打工仔”的命運。今年是《東方時空》開播二十周年,時任《東方之子》編導、原新聞評論部副主任張潔,攜手著名紀錄片導演梁碧波,共同拍攝了九集紀錄片《點燃理想的日子--<東方時空>傳奇》,試圖以“獨立的立場和客觀公正的視角”,審視二十年前剛剛發生的歷史,探訪一代電視人的生命歷程,再現他們不一般的生活,“用他們所追求的理想,所負載的價值觀,影響當下的觀眾,促進中國社會更深層次的變革”。
紀錄片中一共採訪了58人,其中有決策的台領導,有負責欄目創意的“七君子”,但大多數是“打工仔”身份的策劃、編導、攝影、主持人。憑著這部紀錄片,第一代東方時空人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相聚,也進行了一次超越二十年的總結和反省。幾乎每一個訪談都進行了兩三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聊的話題也不斷地深入,圍繞著《東方時空》的創立和發展,圍繞著曾經的激情和理想,圍繞著成長的歡喜與疼痛。
囿於時間和內容的限制,一部紀錄片無法全面展示這些頗有價值的深度訪談。從中挑選一些精彩的有代表性的訪談構成一本相對完整、相對獨立的《東方時空》口述史遂成為共識,於是,我們面前的這本書,《點燃理想的日子--我與<東方時空>二十年》應運而生。
本書共收入19個深度訪談,既有已退休的老台長楊偉光,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七君子”,也有當初初出茅廬的白岩鬆、王志、水均益、周兵、章偉秋、李倫、李玉、鄢蔓、雷婷等﹔他們中間,有的仍留在電視圈子裡,並且卓有成就(如白岩鬆、水均益、章偉秋等),也有跑到圈子外面的人(如李玉成了知名電影導演,雷婷成了著名電視編劇,周兵成了紀錄片大導演等),但無論是散落在哪個領域,他們都取得了自己的成就--顯然,這與《東方時空》頭幾年的訓練是緊密不可分的,那幾年是他們成長最快的時光,那時候注入的理念和精神,那時候培養起的能力和眼光,已經成為這些人成就日后所有一切的隱形基因。他們是《東方時空》這個母親生下的若干孩子。
一代電視人的青春和成長
收入書中的19個訪談,有著同樣的底色--關於創新,關於開拓,關於理想與激情,關於自由與平等。但因為年齡不同,個性迥異,每個人的講述也各有特點。比如,《東方之子》的制片人時間傳遞的,不光是欄目的創辦過程和體制突破,不光是節目的形態和運作、主持人的挑選和培養,更重要的是做事的方式、做人的態度,以及應該怎樣思考、怎樣思想﹔而《焦點時刻》的一線記者陳耀文則是用一件件刻骨銘心的採訪事件和自己親自操刀的片子,來闡述自己作為一名新聞記者的成長,其中有得意的笑,也有痛苦的哭。
水均益幾乎是當時唯一一個從正式單位調來的員工,之前差點去外企當了經理,因此熱火朝天地工作的同時,他也在是冷眼旁觀,他說那群人,“說他們是‘北漂’都輕了,他們是一幫殉道者”。白岩鬆則是講述了自己整個的成長脈絡,人生重要的幾個階段和幾次選擇,他喜歡那個時代,但是拒絕傷感和復制,他說,不能埋怨環境變了,體制的束縛之外,更多的其實是自己的選擇,你依然可以選擇理想,選擇奮斗,而不是作為既得利益者,故步自封,甚至成為年輕人的攔路虎﹔他的下一步,就是努力去做一個很牛的中年人。而楊偉光台長從最高決策者的角度所講述的那些往事,可能許多人至今都不知道。
本書有著極強的可讀性和感染力,多角度的群體回憶反而更有力量,大家彼此勾勒、互相印証,更有助於拼湊起那個激情與理想交織的歲月。讀者在這裡體會到的,不止於19個人或58個人,不只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他們的歡樂和憂傷,夢想和低谷﹔而是一個有著理想主義色彩的群體,一個破繭而出、充滿創意的欄目﹔也是一個改革奮進的時代,一種“群體的瘋狂”。
在疲憊中呵護理想,激發正能量的“勵志書”
對於那些聆聽著《東方時空》的晨曲成長起來的讀者來說,本書無疑是一次懷舊與回首,是與白岩鬆、王志、水均益等人一同成長的分享與總結。二十年后的今天,當的創辦者和“打工仔”都已步入中年,沿著臉上的皺紋穿越時空的年輪,他們是怎樣看待那段日子? 二十年前選擇時的沖動、干起活兒來的激情、以及那樣一種青春的揮擲與不離不棄的夢想,是怎樣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甚至人生?《東方時空》的誕生怎樣改變了他們的成長路向?他們今天又是怎樣一種狀態?回望二十年前的青春,有何種總結與心得?……
而對於初入社會、正在職場打拼的年輕人來說,本書無疑充滿了洋溢著青春與夢想的勵志故事。周兵懷著“一定要做中國最好的導演之一”的夢想隻身來到北京,成為第一批“北漂”,住的地方卻連張床都沒有﹔大年三十還要去採訪,一天居然沒吃飽飯,在擦干淚水回到地下室的集體宿舍時,發現白岩鬆兩口子擺好了一桌年夜飯在等著大家。李玉也只是因為“不想每天生命是靜止的”而放棄了濟南電視台主持人的工作,“跳上火車”就來了﹔來了之后,沒有老編導帶你,大家都在忙--“你應該經受這種摔打,呵護不是一個做紀錄片的人應該做的事情,你就要在這樣的環境裡頭去磨。”雖然“開始特別茫然,甚至張惶地觀察”。
李倫則說,新人“就是牆角裡的蘑菇,進來之后,可能把你扔到牆角,然后大家都會往上撥臟水,扔垃圾,你要干最苦最累的活兒。直到有一天,那堆垃圾上長出一個蘑菇,制片人路過,這個蘑菇好啊,就把你摘走了”。所以對初來乍到的人、實習的人來講,“你要正視這個現實,沒有人應該把你放到桌上來”。陳虻、時間、張海潮這些制片人,沒有對新人進行那種呵護式的關照,但是他教給你一個很強大的內心,你能正視這件事。“雖然他會把你掃到牆角,但是他會每天看一眼那裡長出什麼了沒有。”
二十年后的反思和再出發
《焦點時刻》的制片人張海潮說,《東方時空》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有兩個,一個是它留下的一批人,一個是它留下的一種精神。二十年過去了,這些人依然在﹔而這種精神,還在麼?
《東方時空》在1993年出現有它的必然性,它是1992年中國政治改革對意識形態的訴求,是媒體對時代進步的回應,是當時的媒體人對電視功能、自身價值的反思和認知,對受眾需求的充分尊重和真誠表達。二十年過去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知識新技術新媒體沖擊著傳統的形式和內容。然而在表層之下,依然有一些東西根深蒂固地存在著。
作者張潔說:“一個好的時代是激濁揚清、除弊立新的時代,是不斷為生命解除桎梏,使人的思想力、生命力、創造力最大化迸發的時代。新聞是時代的鏡子,媒體進步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方時空》二十年聚合起來的個體回憶,不止於懷舊,不止於紀念。她是對青春的禮贊,對理想的呼喚,對自由的向往,對包容的贊美,對創造力的歌唱。回首,是為了向歷史汲取力量,是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
白岩鬆在書中也說:“回憶二十年前《東方時空》創立的時候,我們都感慨,很慶幸擁有了一段去做一個最棒的青年人的時代。今天,不該是守在中年人的歲月裡頭回望自己曾經有個多麼牛的青春,然后感慨青春不再。生命從來都是這樣,我覺得現在該思考的是,我能不能做一個很牛的中年人,下一步再過十年、二十年,再去思考,我怎麼樣做一個更牛的老年人,這才是《東方時空》的精神。”
2013年:“點燃”理想,喚起精神。
作者張潔在本書的后記中寫到:“我喜歡'點燃'這個動詞,中國現在不需要形容詞,需要名詞,更需要動詞。我對編導們說,如果我們的片子的質量達到我們的預設,播出后沒准兒”點燃“會成為熱詞,與”舌尖“一樣。但願”點燃·理想“會成為2013年中國文化的一個關鍵詞。2012”舌尖“勾起的是腸胃,2013”點燃“喚起的是精神。”
這也是三聯書店出版本書的目的所在。十年前,三聯書店曾出版了《東方時空》總制片人孫玉勝的《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2006年出版了新聞調查欄目組的《“調查”十年--一個電視欄目的生存記憶》。無論是以前的“電視語態”、“電視欄目”,還是今天的“電視人”,三聯書店一以貫之地對“理想”和“激情”、對“創新”與“開拓”表示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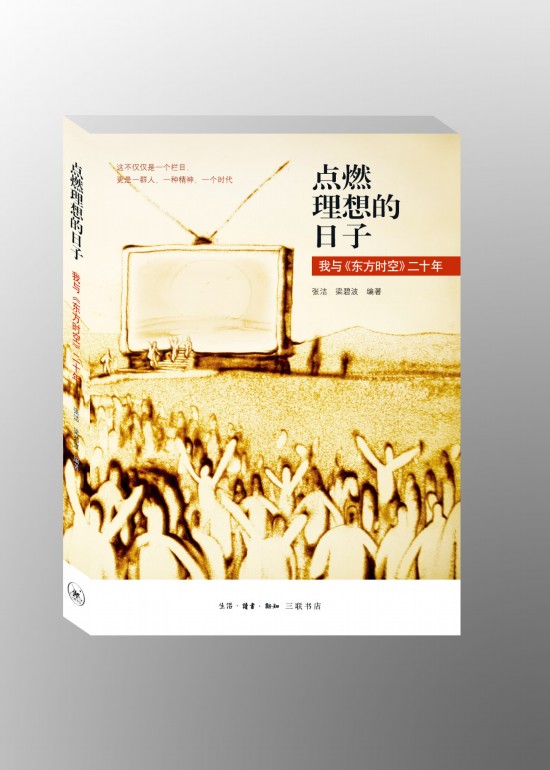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