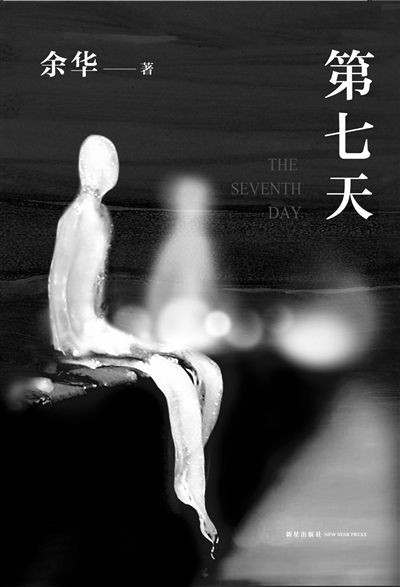

余華。田超供圖
余華蟄伏7年后的新書《第七天》自6月14日問世后,引來眾多爭議,甚至批評的聲音要遠大過贊揚聲。昨天,一直保持沉默的余華通過出版方向記者發來郵件,首度全面回應質疑。對於該書中爭議最大的地方,為何內容多來自新聞事件及微博熱點?余華回應稱第七天是他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我寫下的是我們的生活”。他說,當年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裡,也寫了很多當時哥倫比亞報紙上的事件和話題。
□關於批評
被評“最爛”已很客氣
記者:小說出版之后有很多極端的評論,有人說像中國版的《百年孤獨》,也有人覺得是你最爛的作品?
余華: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裡寫了很多當時哥倫比亞報紙上的事件和話題,他說他走到街上,就有讀者對他說:你寫得太真實了。《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獨》比,人家寫下的是一百年的孤獨,我只是寫下七天的孤獨,而且人家的一百年隻用了二十多萬字,我的七天花費了十三萬字。我深感慚愧。
有人說《第七天》是我最爛的小說,這個很客氣了。7年前《兄弟》出版時,有人說是中國所有小說裡最爛的。你想想,中國每年出版一千部長篇小說,十年一萬部,二十年兩萬部。
這些爭議被微博放大
記者:《第七天》上市后,來自讀者的批評你會關注嗎?會不會影響心情?
余華:我會關注讀者的批評,但不是現在,是以后。等到《第七天》冷下來了,我會拿出時間來認真看看讀者的批評,那時候冷靜的批評也會多起來。其實《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出版時也有很大爭議,只是那時的爭議局限在文學界,那時媒體不關心文學,更不會關心我,也沒有網絡。《兄弟》出版的時候媒體關注文學了,也關注我了,而且有網絡了,所以爭議被放大。這次《第七天》出版,有微博了,爭議更加放大。我把《第七天》交給陳明俊的時候就告訴他,等著大家來罵吧。他說,我准備好了。我在想,我下一部長篇小說出版時,也許五年以后,也許更久,我不知道網上是否會出現比微博更厲害的新式武器,那時候罵聲會更加響亮。
□關於創作
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
記者:新書《第七天》為什麼選擇一個鬼魂講故事的方式?小說是要拉近生活的距離?還是要遠離現實生活?
余華:作家如何敘述現實是沒有方程式的,是近還是遠完全取決於作家的不同和寫作的不同,不同的作家寫出來的現實也不同,就是同一個作家,在不同時期寫下的現實也不一樣。但是必須要有距離,在《第七天》裡,用一個死者世界的角度來描寫現實世界,這是我的敘述距離。《第七天》是我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以后可能不會有這麼近了,因為我覺得不會再找到這樣既近又遠的方式。
一直以來,在《兄弟》之前,我就有這樣的欲望,將我們生活中看似荒誕其實真實的故事集中寫出來,同時又要控制篇幅。然后我找到了這個七天的方式,讓一位剛剛死去的人進入到另一個世界,讓現實世界像倒影一樣出現。剛剛向外公布這部小說的書名時,就有讀者預測是《創世記》開篇的方式,太厲害了。我確實是借助了這個方式,當然中國有頭七的說法,但是我在寫的時候不讓自己去想頭七,腦子裡全是《創世記》的七天。
新聞活生生跑到面前
記者:書中的故事有很多來源於熱點新聞,這是有意的收集還是無意的積累,為什麼用這些新聞素材?
余華:我們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構成的,發生在自己和親友身上的事,發生在自己居住地方的事,發生在新聞裡聽到看到的事等等,它們包圍了我們,不需要去收集,因為它們每天都是活生生跑到我們跟前來,除非視而不見,否則你想躲都無法躲開。我寫下的是我們的生活。
□關於風格
敘述語言由小說本身決定
記者:有人認為,余華的語言才華未在新作中發揮盡致,有倉促的感覺,你覺得呢?
余華:這是一個從死者的角度來敘述的故事,語言應該是節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種生機勃勃的語氣。在講述到現實的部分,也就是活著世界裡的往事時,語言才可以加上一些溫度。一部小說的敘述語言不應是作家自作主張的語言,應該是由小說本身的敘述特征來決定的。
需要溫暖的部分給予希望
記者:小說裡有很多悲慘的故事,但也有溫情的部分。你寫的悲慘故事裡也都有溫暖的一面,比如鼠妹和男朋友之間的感情,李月珍和楊飛,李青和楊飛,你的重點是悲慘的現實,還是現實之后的溫暖?
余華:我在寫的時候感到現實世界的冷酷,我寫得也很狠,所以我需要溫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給予自己希望,也想給予讀者希望。現實世界令人絕望之后,我寫下了一個美好的死者世界。這個世界不是烏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
現實常以荒誕的面貌出現
記者:封面上有句話“比《兄弟》更荒誕”,為什麼寫現實的時候總是喜歡用荒誕的筆法?
余華:這是因為今日中國的現實常常以荒誕的面貌出現。昨天我看到一位叫陳硯書的網友鏈接到我的微博上說:“《第七天》爭議大的根源是民眾對荒誕的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乃至見怪不怪,對荒誕的縱容使荒誕化為平常。”我覺得他說得很好。
記者:你在小說裡用了特別多的“我”,似乎是一種有意識的重復和強調?
余華:我在修改的時候已經刪除很多“我”了,剩下的“我”都是不能刪除的,仍然不少。這是敘述的需要,《第七天》的敘述有點像圓規的作用,“我”在敘述裡是一個圓心,敘述的圓規一圈一圈往外劃出一個一個的圓。“我”的經歷是圓心,所見所聞是一條條圓線。
□關於未來
我的缺點是興趣多不勤奮
記者:你說這部小說寫了七年,《兄弟》之前其實就已經開始寫了,然后擱下了。為什麼創作中出現這麼多停頓,手邊有哪幾部作品還沒完成?
余華:我不知道自己的寫作為什麼總是卡住,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時間被切碎了的理由,總是有很多事來打斷我的寫作,比如明年和后年,《第七天》的國外出版高峰就會來到,我又將不斷出國去。所以我同時在寫五六部小說,還不包括在腦子裡轉了十年以上的構思。但是時間被切碎不是理由,我的缺點是很不勤奮,我興趣太多,總是被別的什麼吸引過去。有朋友勸我別到處跑了,趁著現在身體還行,多寫幾部小說出來,將來身體不行了,就寫不動了。我說,將來身體不行了,我也跑不動了。作為一個作家,我知道自己這方面的缺點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