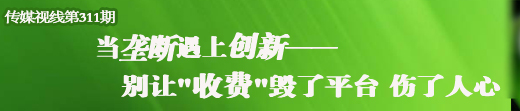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杨磊: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
杨磊: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2001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云南地方媒体工作,负责政法新闻报道,2002年底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负责突发及灾难事件报道。
杨=杨磊
李=李梓新
李: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前线?
杨:我5月14号早上到,本来打算12号去的,地震后我们就马上有记者去国家地震局了,当时找了地震局一个要去灾区的专家,我们说要跟他一起走。但是他说要收拾行李。三点半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他收拾行李,约在首都机场见面。结果他已经从南苑机场从军用飞机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被耽误了一天,改到13号的飞机,但是上午的航班都是救灾的,只有等到下午的航班,下午的航班飞到重庆,从重庆包车去成都。
李:当时和专家一块儿走是报社行为还是部门行为?
杨:报社当时是想派人去的,但是中宣部下了禁令,就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不允许去,报社就犹豫了。但作为特稿部,本身就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我觉得不能不去。成都站的记者也找不着,于是我就带着几个人去了。我们后来打听了南方都市报,谁都没有管禁令就去了。那天恰好是周一,我们每周一开编前会,领导们都在。
李:编前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地震的消息吗?
杨:2点半的时候开编前会正要开始开。编前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编辑说她血压低,头晕,后来大家才发现不是她的问题,是整个楼都在晃动。十分钟之后有人收到短信,说四川省发生了大地震,于是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大概在四点钟,我们就有记者去机场跟地震局的专家。我们又派了很有经验的记者徐凯从重庆去成都,他包了一辆车,到了成都是夜里十点多,他拉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家里受灾的,他就跟那人到他家写了一篇稿子,当天夜里十二点多发回来。
李:你们当时人员计划怎么安排的?
杨:当时我们在派多少人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认为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我以为加上我、徐凯、左志坚三个人就够了,后来总部从广东又派了两个人。因为当时从广东能飞成都。
李:5月14号的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杨:有15个人。加上当地记者站记者。
李:怎么样后来又加到30个人的团队呢?
杨:我们到了现场发现大家都乱了,也有人是没有报告总部就自己来了,我们有一个同事开始说因为母亲一个人在成都所以要回家陪母亲,但是到了当地以后没有回家,反而去绵阳采访去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真正有规划地增加人是第二个星期,5月19号左右。那时候现场救援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灾后重建,我们派去了一些常常在北京、上海跑政府的记者。如卫生、民政等,他们资源会更广。
前方当时去的有三个主任,我和其他两个人。我们分属不同的中心、不同的领导,后来派来了两位编委,指挥调度会比较好。成都也是一个天然的编辑部所在地。
李:后来为什么考虑要让编辑直接上前线?
杨:我们刚开始比较乱,记者写了稿子不知道该发给谁,也不知道怎样安排,放到哪个板块、怎么处理。于是从后方调了三个编辑,他们直接在前方组成一个编辑部,稿件统一归他们,他们来协调稿件。
李:你去的时候,怎么分条线的?
杨:我到了成都的时候整个成都站的人都归拢了,给大家开了一个短会。希望女孩子去的地方都是当天能回到成都的,男孩子去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比如北川。因为徐凯是比较有经验,我把成都到都江堰的路线给了徐凯,把绵阳留给我。我是14号下午到的绵阳。
李:到绵阳的路还通吗?
杨:从成都到绵阳的路还可以,一直可以通。但是再往里走就困难了。
李:那你们怎么再深入进去的呢?
杨:我们从绵阳包车到安县。到安县又包了一辆车,但是走到半路,就是亚洲风洞那个地方,就交通管制了,因为要进去的车太多,堵路了。当时我虽然拿着绵阳市委的采访证也没有用,后来我就走路上去了。
李:然后你只能步行了?步行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
杨:对,走路进去了,我减轻负荷,相机都没拿。就背了电脑,发稿用的,拿了一瓶水、一个手电筒、一个收音机。
李:收音机后来能够收到信号吗?
杨:时断时续。
李:后来走了多久 ?
杨:走了五个多小时。
李:大约多少公里?
杨:地图上标的是13公里,老乡说实际有15公里,因为路非常不好走,而且随时有石头掉下来,阻挡道路。而其运灾民的车也不照顾走路的人。所以人走在路边比较危险。
李:你看到过逃出来的灾民吗?
杨:灾民都在一大块空地等,因为有警察告诉他们不要走,会有车来运送他们出发。
李:有没有寻亲的,和你一起进去?
杨:有八个成都的人是来寻亲的。成都有一个老年大学,他们由学校组织去北川西乡羌寨参观,那天事发的时候就在北川参观,所以他们的孩子要来进去寻亲。但是警察也没有让他们进去,我是因为有证才被允许进去。我把电话留给他们了。
李:是不是后来在网上写下《北川寻母记》的那个人也在里面?
杨:那个人我是见过的。我给了他一包烟。他装备很专业,我还以为他是同行。
李:你到的第一个比较惨烈的现场是北川中学吗?
杨:擂鼓镇。我当时看到特别害怕。我不知道羌族人死了以后还要裹得那么严实,放在一个门板上,门板是悬空放着的,用砖头或者板凳架住。空隙里面点着一根红蜡烛,我原来看到亮光以为是活人,还想上去问路,结果后来才发现是死人。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比较恐怖的是镇上既有死人又有活人,但是看到活人更害怕。幸存的人都呆在那里。天上又飘起小雨。
李:天那么黑了,你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使你决定向前走呢?
杨:做新闻的人,基本的感觉是既然来了,还是要到现场去的。当时我看到那些,就想到现场肯定特别惨。我从来不能想像一大群大一群人坐在那边,跟傻掉一样,行尸走肉似的。手电一晃,他们都带着惊恐地刷地站起来,但又不说话。镇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安慰镇上的人,说我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空车,肯定是来救援他们的,但是他们也不理我。
李:于是你就继续向前走吗?是不是有些部队可以给你壮胆?
杨:我看不见,但是能看到军车往里面走。
李:你有同行伙伴吗?
杨:有,是《生活》杂志的记者。
李:后来就到了北川中学吗?
杨:是的。
李:到北川中学是几点?
杨:夜里十点半。我觉得特别震惊的是走到收费站的时候遇到了几个绵阳的小孩,其中的一个家里比较有钱的样子,他们当志愿者。我有手电筒他们没有,我们就一起走了,他当初在北川中学读过书,但是当我让他们带路的时候他在路上转了四圈,他都找不到那学校了。我觉得如果本地人都找不到,地震肯定特别严重。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亮光,才觉得是北川中学。进去北川中学的门,看到到处都是帐篷,迎面过来是一个冰柜车,冷藏车,是来运尸体的。当时还是比较乱的,很多帐篷都没有搭好,很多车进不去,我去的时候吊车已经在开始吊了。
我进去的时候车上的死人摆得特别规矩,每一个尸体落上去的时候他们量量身高,拍照,刚开始尸体落上去的时候还有声响,后来慢慢慢慢就没了,因为死人太多了。
李:当时现场有父母吗?
杨:有很多父母,都在现场哭。一方面他们想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看是不是活着,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他们后来都有经验了,知道一旦救援战士发现一个活人,都会喊医生;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救援队伍发现的都是死尸,于是直接扔上车。
李:当时你是在北川中学过夜的吗?
杨:对,当时没有地方住,我就从医院里拿了一个凳子,找了一个稍微暖和的地方和医生聊了聊,四点多钟睡了一个小时。
李:当时还下雨吗?
杨:下雨,山里头冷得不行,有风。帐篷后面又是尸体。
李:当时你就开始写稿了吗?
杨: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写稿了。
李:写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吗?怎么样去组织文字。
杨:当时没有太多心思去构思文字,就是觉得看到的东西就写出来,第一要大家知道这边很惨;第二去解释为什么这么惨;第三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我写稿的时候心理非常难过,后来和一个美国摄影记者聊天,他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他说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错,只是因为脚下的地球在移动,他们就丧生了。这种挫败感非常严重,因为我们什么也帮不了。
李:你写完之后怎么发回来呢?
杨:我当时拿了一个无线网卡,以为我手机能收到短信就能发稿呢。但是我试了很多个地方都没有发出去,导致当天稿件没有发出来。
李:夜里你们在路上怎么躲避那些滚下的石头,能听到声音吗?
杨:有些时候是有声音的,有时候是下意识的,因为对面不断有救护车,他们是抢时间的,不管路边的行人。我们就不能走在路上,只能贴山脚走。我们有时候走了一阵子感觉不对了,等一等,我一共带了六包烟,光在路上就抽了三包,因为有时候等待时感觉没事情做,就抽烟。也可以压压惊。
李:第二天早上你还在北川吗?
杨:待到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离开北川中学了,山里天亮得早,但天是阴的。而且尸臭开始出来了。我去找医生要了两个口罩,那时我们连口罩都没有。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去县城。当时很多人都劝我们不要去,说县城不断地掉石头。而且房子一小时前是一个样子,一小时后就完全另一个样子了。余震不停。北川中学门口的电线杆就像坐标一样,看到灯一摇,所有人就跑。
李:第二天你们走的什么路?
杨:我们走的山路,从堵住县城的两大块石头上翻过去,十几分钟的路走了两个小时,终于赶到县城。那里挖了很多人工的台阶,军队说他们的突击队从里面八个人抬一个伤员出来,上一个台阶要花15分钟。
李:进到现场以后你怎么感觉的?
杨:进去就震住了。因为我们要下去,下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垫脚石一样的东西,一看是个死人,可能是被别人裹起来的。踩下去的时候踩出一只脚才知道。然后就沿着河走,一直走到那个挂有奥运会88天倒计时牌的地方。基本上一步一个死人,而且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是被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有的只有半个身子,有的只露出一个胳膊,非常惨。我们还看到一辆警车挂在7楼的楼顶,还有的在树上,都是被石头砸上去的。
我们那时候根本分不清楚哪里是新城,哪里是旧城,我们看见一个武警在作业车上面救援。后来我们知道那是茅坝,也就是北川中学新区,但我们没有过去。我们决定先去老县城,因为觉得老县城伤亡更加严重。石头已经砸的裂口了,半座山滑下来,把建筑推了六百米,一直推到河边,大量的人都死在河沟里。
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市场,两层楼的市场,底层是商铺,上边是住人的。看到楼都已经要倒了。到市场我们本来想看看就走,但是听到人在那边小声哼,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挖人。因为看到人其实被埋得很浅,大概有三个人。我们试图去把人拉出来,但是刚抬开一个东西,那废墟就开始摇,好像是有余震。于是我们就退回来想等到不摇的时候再去救人。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几次灾难报道的经验,胆子都挺大的,还想继续救人,但是后来突然感到摇晃得比较厉害,在两座危楼中间站着的我和我的同事都愣住了,然后我下意识说了一声“跑”,我们就跑到了周围的空地上,余震了,一会儿我们就看着那个两层高的楼倒下去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救援队,好像是江苏省的救援队,我们告诉他们那里面有三个人还活着,他们不理,他们说他们主要的救援地点是学校,说他们会做标记,一会儿过去救。后来听说那边救出了三个人。
李:你还说你给过一个人矿泉水喝?
杨:那是在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对面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有一个火锅店,叫绿色火锅城。我们在那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人,他就在地面上,但是四层楼塌了,把他压在下面了。他一只手还能活动,但是看不清他的面容,也判断不出他的年龄。他说不出话,只会哼哼。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小孩的面貌看的特别清楚,是被压死的。于是我们给他水喝。我们跟他说旁边就有救援队,一会儿就来救他,但是第二天我们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而前一天他还能拿着水,我们还担心他拧不开水,还帮他拧开了瓶盖。还给他撕了巧克力放在那里。
李:你自己带的东西够不够自己用?
杨:不够。第一天我带的水就已经没了。在擂鼓镇的时候捡了半瓶水。我穿的鞋是防水的,但是鞋底非常软,石头硌脚,不好走,非常费力。我很快又把水喝完了,然后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辆桑塔纳,被山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开了后盖,司机已经不知死活,我就从车的后备箱里面找出了三瓶水,我对自己说我们是来行善的。这三瓶水支撑了以后的两天。
李:当时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
杨:没有,就有几块巧克力,但是到后来都不敢吃了。因为一是当时也不觉得饿,而是巧克力吃了更觉得渴,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水。我们看当兵的也非常惨,他们也什么东西都没有。
李:你为什么决定在北川县城住一个晚上?
杨:有两个理由:一是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现场;二是我实在没有力气再回去。
李:那天晚上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
杨:那天晚上天特别特别蓝,又有月亮,到处都是死尸,但又有生命的气息。现场没有太多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周围很多野狗。特别冷,我又没有睡袋。冲锋衣又不耐寒。我拿着手电,披着冲锋衣说走一走,正好赶上一个海南的消防队刚过来救人。他们是后半夜过来的,就直接救人了。他们有一个很小的柴油发电机,树了一个灯泡在那里,那是当时北川县城唯一的一点亮光。当时感到特别安静,一个原本充满了生机的城市突然之间变得那么安静让人非常害怕。而且虽然很多人死了,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仍然有灵魂,仍然活着,加上当时还不停地有余震,一有余震就是周围的石头在动,在响,所以整个现场都是非常吓人的。北川可能之前的那个县城都比较富,周围没有家的都是好狗。
李:你那天睡得着吗?
杨:当时还是比较困,于是休息了几个小时。路上把能扔的的东西都扔了,包括脏衣服。因为嫌太重。后来回去的时候发现只剩下一个电脑了。
李:后来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呢?
杨:5月16号回去的。15号晚上住在县城,当时要发稿,16号的时候太阳很大,县城已经都是尸体的腐臭气味了,人家劝我回去,因为疫情肯定要来了,又说要有洪水。我说我要发稿,就到设在北川中学的指挥部去排队发稿。
李:是通过什么方式发稿的?
杨:指挥部架起了一个海事卫星系统。可以支持10台左右的电脑无线上网。然后大家就排队。每人只准发一条稿子。如果要发图片的话还要向他们求情。当时电话不通但是短信通。
李:发完稿子就回来?
杨:然后同事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已经扛不住了,头发发硬,手一捋就变成不同形状了。因为最惨烈的现场已经看到了,我就回到绵阳去了。我们在旁边拦车,最后搭的是绵阳志愿者的车,拉了八个记者下去,一路还接了很多灾民。
李:你在前方的时候还和家人保持联系吗?
杨:我没有怎么跟家人联系,因为我女朋友也是记者,她虽然没有去第一现场都是也在跑部委,所以比较理解。一般我就和她所我现在在哪我挺好的。我们当时听说应急通讯只能同时保证500部手机通话,我们就不太好意思占用通信资源。觉得记者不要添乱就好。只是和后方发短信说要交稿子。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现场了。我都跟他们说我在外面出差。后来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李:回来之后你什么时候第二次进的北川?
杨:20号的时候。当时是为了堰塞湖进去的。当时从北川的堰塞湖要垮。我就又进去了。
李:这次地震报道一共前后呆了多少天?
杨:17天。
李:后期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事情?
杨:我们现场的记者后期转向报导次生灾害。因为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后来看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觉得次生灾害才是最大的灾害,因为它是针对活着的人的。后来我们的记者去了安县,说安县很多人拉肚子,瘟疫、疫情都开始出现,于是后来我们转向做那个。包括北川的重建。
李:经过过这次事件,你的自然观、人生观会不会有些改变?
杨:说改变也谈不上,但是地震给人最大的感觉是一种无力和无助。我进县城的第一天就感到,那种地方没有办法跑掉。我会觉得人都很可怜,因为很多事情是无力改变的。如果要说对我的改变,这次事件会让人更有恻隐之心。
李:你看到的种种惨状产生的挫败感、无力感会不会让你感到沮丧?
杨:沮丧一开始有,慢慢就没了。记者有一种职业立场,这个可能会冲淡沮丧。当时我们在那边采访很困难,我不忍心问别人,我们就像旁观者一样在听别人讲述。灾民想跟记者说的时候我也基本上都在听,并不提问。他们其实很有倾诉欲望。我虽然有一个录音笔在录,但是感觉其实并不必要,因为当时的记忆力会出奇的好,他们讲的每一个字都能够记住。他们给我讲他们有一个超市,石头掉下来砸了一个人,大家要来救那个人,但是石头非常大搬不动。然后那个被砸的人就要他们拿锯锯他的腿,但是可能由于锯太小了的缘故没有锯掉。然后那个人就让大家拿斧子去砍,后来砍断了他的腿才把他救出来。这种人对于的生存的渴望很让人震惊。
对心理的影响主要是挫败感,让人的脾气变得很大。跟后方联系的时候,觉得后方都是坐在办公室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不这么弄呢。就很容易吵架。
李:对你来说,回来之后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杨:我回来之后不太愿意跟他们讲那边的事情,只愿意和一同去的同事聊一聊。有很多人感觉回来之后活得非常真实,有选择性地安排忘掉一些事情。
李:你回来以后需要什么心理调适吗?
杨:我回来以后开始怕安静,本来报社安排我在家休息,但是我休息两天又回来上班了,觉得办公室里好多人热热闹闹地心理才安定。我们家住在16楼,白天特别安静的时候就有点想那天晚上的情景,我现在受不了安静,写稿的时候都要开着电视。
李: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恢复吗?
杨:我觉得会,因为我已经有很多突发事件的报道经验了。从2003年的非典到太平山矿难、邢台矿难等好多次矿难,还有松花江水污染、开县井喷、包头空难等等,我都去过。所以我认为自己的调节能力都是很强的。
李:这次采访中有什么第一次的体验或经历吗?
杨:我以前采访从来没哭过,但是这次采访的时候哭了。不是在北川哭的,在直升飞机上进茂县的时候,到了那边发现我要去联系的人不在,我说要不然我就在茂县呆着,后来同事建议去红十字会采访,回来的路上搭上了一架直升飞机,机上载的是孤儿。在飞机起飞的一刹那,孤儿从窗上看家乡,都哭了,很大声,一群人全哭了。我当时突然想到这次生在大山里的孤儿本来没有什么机会离开家乡,但是现在真正离开家乡的时候却是他们这一生看家乡的最后一眼了,于是就跟着他们哭了。我当时把所有的吃的喝的都留给了他们,并且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每个人分一点,上面留了我的名字、电话,怕别人抢他们的钱。当时我哭得很厉害。结果驾驶那架飞机的飞行员就是后来失事的邱光华。
李:是吗?所以你对他还有印象。
杨:我刚开始看到一架飞机失事的时候没有感到惊奇,因为那路很难飞,气流非常不稳定,我们当时坐飞机的时候特别害怕,觉得不掉下来是不正常的,即使那天是晴天。后来回到北京,回到办公室,我就看网上说掉了一架飞机,新浪网上挂了一个视频,是失事飞行员的影像,我一看就是他。他们机组有个机械师叫陈林,我当时还曾经跟他搭讪,说机长你好年轻啊,他就笑了,说他不是机长,是机械师。我们换了一根烟。他是失事机组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李:那你当时的感受是后怕还是?
杨:后怕。我当时像傻了一样,人呆坐在那里。他们走的线路也是我走过线路的一段。从理县到映秀,经都江堰到成都。
李:坐直升飞机是不是也是你的第一次体验?
杨:对,是我第一次做直升飞机。这也算是命大。
李:你手上戴的佛珠是不是也给你提供了心理支持?有什么来历?
杨:那是青藏铁路开通的那一年。我去采访时去了哲蚌寺,是一个活佛给的。
李:你是否觉得自己的职业感战胜了内心的害怕?
杨:我觉得勇气确实是出自我的职业感。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南方周末》长大的。我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在车上拿着《南方周末》看时,一定要把报头放在外面,让别人看到你在看这报纸。我们当时都被记者的职业精神所感动。我们2001年、02年入行的人职业责任感特别强,地震来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害怕,觉得这是记者的职业,是记者最应该做的。
李:你的从业经历是怎么样的?
杨:我2001年毕业时去了《云南日报》下面一个子报《云南民族报》跑政法条线。在那呆了一年之后,2002年下半年,《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筹建重庆站,我就去了。幸运的是很多大事我都赶上了。
李:你这次在现场得到什么外部资源的帮助了吗?
杨:这次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只要你说你是记者,政府各方能够配合的都会配合的,因为除了记者和救援人员,也不会有人去那里。
李:政府很配合,军队也非常配合吧?
杨:对,军队也非常好,大家都仿佛同命相连,互相鼓励。到后来就会慢慢希望记者做宣传,比如救援的时候把红旗插上去,而且有记者的时候就干得特别来劲。
李:这十几天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最难熬的阶段?
杨:应该是十八九号的时候我回到成都,那天晚上大家说成都有余震。因为如果是北川余震的话太正常了,但是回到四川看到灯红酒绿的,原来以为可以好好吃顿饭、休息一下了。因为余震预报,结果所有餐厅都不营业,大家都跑出来躲余震了,而且要在外面睡觉。那个时候是最难熬的。原来以为安全的繁华的都市结果也这么不安全,在灾区反而觉得更安全些。反差太大了。我一下子有一种错乱感,觉得很不真实。
李:那你回到北京之后有没有感到一种不真实呢?
杨:回到北京应该还好,但是回来的头两天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李:会不会还在灾区的氛围中?
杨:对,短时间还是恢复不回来。
李:你对自己的报道还满意吗?
杨:总体还满意,但是最遗憾的就是我在北川特写的稿子没有发出来,但是我却认为那篇是我写得最好的。
李:你觉得这次事件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有怎样的促进,毕竟经过这么一张大战役。
杨:现在还看不太出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变好,一种是经过一段时间又返回原状。但是这次表现很好的一点是记者非常配合;第二是这次后勤做得很好,让前线的记者感动。回到绵阳的时候,发现头盔都有整整一箱放在那里,手套一捆捆的。
李:你觉得这次事件对中国新闻史有突破吗?你怎么看待?
杨:我觉得会有突破的。一是在一线采访的记者会成为一批好记者,他们知道怎样追求真相。我们看到了一些没有经过报社同意就过来报道的记者;也看到了一些执意要发稿,不顾后方编辑部意见的记者。他们的职业感、正义感已经被唤醒了。我觉得这个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李:我知道这次你们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合作,合作怎样?
杨:非常好。中央台新上任的副台长王晓辉特别懂新闻,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大家的理念比较接近,他们的资源能力比较强。
李:是你们找他们?他们给了你们哪些支持?
杨:对,他们给我们协调部队方面的事情,比如直升飞机等。而且帮我们找大人物采访。我们的记者也帮他们做现场连线的电台报道。
李:这就是不同体制的媒体的合作。
杨:对,这也是一条可以探讨的道路。我们这次也尝试和自己的网站联动。
李:你们有直接发稿给网站吗?
杨:我们会用短信发消息过去,几十个字新闻这样。我们网站派了一个编辑在前方,在几分钟内可以立即上网。包括在北川,也会发消息,及时更新。
李:对于下次的自然灾害报导,你有什么总结吗?
杨:我觉得这种灾难报导要做得更有策略一些,比如在稿件的处理上。我觉得南方报业集团之所以做得好,还是因为比较有经验。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