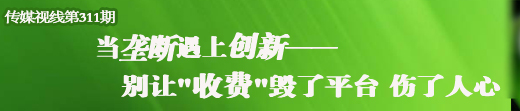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包军昊:我觉得央视可以打98分
包军昊:CCTV地震晚间直播总导演,《东方时空》制片人。1969年5月生,新疆石河子人。1987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从业12年,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节目、《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做一线记者和策划。曾担任“中国入世直播”节目的策划和多哈直播现场总导演。作为主创人员创办过三个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和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二等奖等。
包=包军昊
李=李梓新
李:我想先了解一下,你这次负责晚间直播的情况。
包:央视是5月12号那天开始的直播。按照分工,我算晚间8点到1点半时段的总导演。晚间我们一共两个导演组,我是其中之一,一人一天轮换。我这样做到5月30号。做总导演就是负责晚间整个时间段的编排,上什么不上什么,大概的报道的重点、主题。因为直播有一个串联单,这样前方记者采集之后,什么时候出镜,什么时间做什么报道,主要是做这个工作。
李:那么咱们还是从头聊起,这次地震中央台是从下午三点多就开始播新闻了吧?
包:对,三点多,准确地说是三点十分吧。
李:当时怎么样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包: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我,决定开窗口是新闻中心领导决定的。因为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都是个人管个人一摊的事儿。这是我们的常态,属于栏目化经营,直播属于“非常态”。当时事发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我给《东方时空》全体人员开总结会,因为上个星期刚好我们对于胡锦涛访日的报道结束,所以我说做一个总结,因为一方面有胡锦涛访日的报道,之前又有铁路撞车等一些大事儿,四月的大事件挺多的,我们就以为“五月份可以过正常的日子了”。而且5月12号当晚的播出计划是报道缅甸遭遇飓风的情况,本来是准备在上一周的周五就播出了。因为太忙推到这天。
我们栏目本身也有一个雷达机制,一发现新闻热点了快速反应。当时这个事是下午2点28分,因为当时我们新闻专题部的办公室在台外,没有感觉到震荡,但台里大楼的同事感觉到震荡,于是他们就往这边打电话,说是出了这个事儿。我们这边很多人网上都挂着QQ、MSN什么的,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就说发生地震了。我当时立即让我的同事给在湖北黄石的记者打电话,因为当时网上都说是湖北地震了。一问人家说黄石那边还行,也没有死人也没有楼倒塌,不厉害。但是网上就有人说地震得挺厉害的,说很多房子都倒了,后来有人说了一句,成都电话都打不通了,我说真的假的。我自己有成都的朋友,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无法接通。
面对这种情况,办公室里面所有人都在喧哗,我就告诉他们,所有人,只要你在成都有朋友,有认识人的,你们一定要往那边打电话。只要打通一个,这边就订机票,订了机票就过去。只要打通一个,听到他们说“我看见了”事情是什么样,我觉得就可以立即派人去报道。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打通。然后我又拨成都的114,也拨不通。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查飞机票已经查好了,我就让他们下单就可以买了。一般正常情况下这种突发事件,我们也就派一个记者,这次我们派了三个:两路去成都,一路去绵阳。当时还想万一有一路的机场不通,我们另一路的记者也能到。
李:当时订票的时候是几点?
包:应该是2点42分。
李:那反应很快了。
包:我们一听到地震的消息,第一想到的就是赶快订票。
李:而且当时你们想到了三路出发,这个反应比很多媒体都要迅速。
包:当时有两路到了机场,发现飞机飞不了,就改签了去重庆的飞机。当时他们是12号当天晚上到了重庆,然后连夜包车赶到成都。13号凌晨到的成都。然后还有一路是中途要求他们退票,这边联系了国家地震队一驾专机,他们半路就直接赶到北京南苑机场了。这样我们保证了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赶到成都。
李:这边的反应确实很快,当时很多媒体也没有预计到这次地震事件会这么严重,所以没有特别安排记者。
包:当时感觉是这样的:首先成都这样一个省会城市如果电话打不通这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严重了。而且当时网上很多网友都说他们那里地震了,说明波及面积非常大,所以根据这个来判断,这次地震事件还是非常严重的。到了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这个判断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我们着急的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到,班机什么时候能够起飞。
李:去的两三人是属于单独去还是在栏目化的操作下?
包:是栏目下的。
李: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们派什么任务?
包:去的时候他们这一班是7点多的飞机,我们的栏目是10点半播出。七点多起飞的话到那儿就得九点多,然后我当时想要是上栏目来不及的话就电话连线。有一路记者是跟着专机过去的,当时是这么想的,在飞机上就进行采访国家救援队。主要是看救援队那边怎么部署的,然后他们怎么响应的,因为主要是响应的规模能够证明地震的危害程度。这样的话一下飞机,第一时间把这个工作办完了。因为那个时候别的情况都不知道,包括地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就是这么安排的。这边后方我们有人收集震级、震感方面的资料,还想做一个地图,标明各地震级,把各个省市的记者电话连线做成采访,描述一下各省的震感如何,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李:那在后方是什么时候开始全盘打通?
包:13号,13号晚上8点的时候我就开始介入全面的直播了。13号上午我就和领导说了,要么让我上前方,要么让我做晚上的直播。后来我们就开始节目策划的讨论,我们采用合作的形式,我们《东方时空》栏目还有《一加一》栏目合作。到14号开始,就是我独立来操作策划。
李:前方记者是怎么打通的呢?
包:刚开始挺乱的,因为通讯不通,很多记者都是在栏目化操作体系下的,自己有了新闻反应就去了前方,他们有自己的任务。有的还是没有跟节目联系直接就到了现场,但是到了那边又跟这边联系不上。虽然乱,但有一点还是好的,就是他们还会尽量和新闻中心联系,新闻中心和他们说我们在负责。晚间新闻相当于一个汇总,于是别的栏目都知道找我们了。还有很多地方台资源也比较多,中央台因为节目太多,派过去的记者一共也只有一百多人。地方台报道的有四川台、成都台、重庆台、绵阳台,后期又加入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等,包括还有一些部队的记者站,所以资源、信息量是不愁的。很多采访堆积使后期制作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在发生的前几天信息量是充足的。
李:在具体报道的时候决定连线谁,前方记者是谁,这个是你还是谁在后方控制?
包:新闻中心包括采编部、新闻专题部、社会专题部等部门,平时各自为战,这时决定由谁连线都是由导演组来统一负责,我们有专门的小组,编串联单。
李:那你怎么掌握哪个记者去了哪里的情况?
包:新闻中心在5月15日出了一个联络图,进行分工,分了很多系统,比如早间时间段谁负责,晚间时间段谁负责,除此之外记者连线谁负责,后勤保障谁负责等。把这个联络图往各个地方一发。大家就都清楚了。前方的记者因为都是栏目派的,比如《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焦点访谈》派的记者,我们几个组就有一个负责给这些前方记者打电话,来汇总整合前方记者所有的信息。看每个人都在什么位置,然后在做什么采访。
李:这个能做到吗?每天打电话看在什么位置能做到吗?
包:电话通了基本都能做到。每天最早来的人就给记者打电话。
李:这一点还是相当难得的,我知道有一些媒体不能做到总部和前方定点的,定时的联系。
包:按说如果是一个成熟媒体的话,这些应该做到的。因为这个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大家乱了之后还要追求有序。当然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正常状态下的做法。
李:那刚才说这种打通的运作模式之前运作过几次?
包:完全意义上讲的打通以前还是没有的,时段有过打通,但这么大规模的还没有。
李:所以这次的打通还属于第一次?
包:看怎么说了。香港回归的时候也是连续72小时,但是72小时也是之前已经安排好了很多记者。香港72小时属于有计划的报道,这次完全是一场遭遇战。
李:这次时长也长很多。
包:对。原来我做过“嫦娥”飞船升空的直播,我也是总导演。时间是3天,每天下午和晚上。但是那次我觉得还与这次不是一个状态,不是整个新闻中心动起来。因为那次有些节目还正常播出,跟我们合作的有?10个部门,但也只是10个部门中的部分记者而已。
李:所以这次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意义方面都应该说是最大的。那么你怎么样选择节目的一个形态?比如前方画面和专家访谈等怎样配合安排。
包:这个也是一个原则方面的把握。首先你根据统计出来的每天的新闻焦点,多年来都能形成一个感性的认识。比如头几天救人是最要紧的,是否通路,有没有跟当地取得联系,当地情况到底怎么样,这都是百姓最关心的。跟这个有关的,我们就优先往前排,优先让这些新闻反复滚动。然后在这之外的一些专家评论,我们就往后排。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李:对于专家访谈我们有一种怎么样的功能定位?
包:定位在科普知识,所以这些内容都往后放。
李:如果是演播室的专家呢?
包:演播室的专家起到的一个作用我们叫“松紧带”作用。因为有的时候信号不通,信号送不过来。当电话打不通的时候,演播室的嘉宾就起到一个调节时间的作用。
李:包括在主持人方面我也知道刚开始是一两个人在顶,后来才慢慢开始安排人。
包:对,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张羽他们。还陆续有一些记者被派出去了。
李:你有没有统计前方的总兵力?
包:一百多人。摄像,记者,领导再包括后勤等有两百人了。
李:这个规模在这次媒体报道里面最大了。对于这次的报道人们也是交口称赞,你觉得是怎样的一种契机和环境使得这次中央台的报道做得如此出色?
包:我觉得第一点是社会环境的契机,人类对于自然灾难的一种同情,一种善良的人性,这是很基本的前提。听到前方的消息之后,所有人没有任何条件地都申请要去前线,这个很让我感动。在灾区的生活比平时任何日子都艰苦。白天在公共汽车里面不能睡觉,晚上也找不着地方睡觉,记者就像灾民一样拎着帐篷,只要有空地撑起帐篷就睡觉。大家对于灾区的关心体现得特别充分。这种环境下你不必为记者的敬业精神操心.
第二点就是在此之前的两件事引起人们对社会状况的思考,一个是藏独,一个是铁路撞车。藏独这件事使我们在国际上是比较被动的,西方舆论在国际上非常强势。反思这种被动局面,就从百姓的角度讲,我相信所有百姓都站在国家这一面,都反对藏独。但是国内媒体当时一直比较低调,没有怎么报道,导致国外的谣言、传言占据了主流的声音。后来国内主流媒体才开始大量报道,但是已经被动了。这里面包含一个传播规律,传播规律讲你要第一时间发出声音,进行报道,后续的声音再大也已经出于被动了,也是跟着前面的声音在辩驳,在辩解,这样就不好了。所以藏独这个事情让我们有了思考。
第二个是铁路撞车。按照以往经验,铁路撞车的事情,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原因是什么?二:责任人是谁?根据我们以往的灾难报道经验,这两点等到报出来的时候,距离事发,最短我看也得有半个月,有的甚至长达几个月才出来。可是如果你不及时报的话,谣言,猜测都开始散播。但是这次铁路撞车事件的处理不一样了,从事发到报道结果、原因不过半天,责任人是谁都非常清楚。要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这种事件节目怎么也要做几天。去挖掘“内幕、责任人”,但是这次感觉可挖掘的空间没了,答案非常清晰。媒体热点很快就转移了,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传播规律,一个传播的道理:引导舆论要有新思维,简单的管控是不符合传播规律的。但社会要认识这个规律还要有一个过程。
李: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么快地报道是否部分受到铁路事件迅速处理的提示,还是上面有开绿灯加快报道进程?
包:这我也不好揣测,只能通过结果来分析。当时总理到了现场,中宣部的一个领导也到了现场。没有领导的大力推动,报道也不会这么及时。
李:你能否谈一下节目发动社会力量的贡献?
包:当时筹备抗震救灾晚会时,我和领导说我们这次节目就叫“我们在一起”,也有人说要叫“你我在一起”。我说“你我”就显得你和我是分开的,好像受灾群众和没有在灾区的人是不同的,不好。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又想到有一个板块要把这个概念做出来,我们要做一个捐款的试验。我当时就在办公室里想这个晚会,说要试验看能否在捐款数额上面超过抗洪。后来没有做。
李:你觉得这种大规模的报道,全天候的报道,以及后期哀悼日开始后各地方台也转播中央台的新闻。你觉得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播效果,传播模式?
包:很多地方台同时转播中央台的信号。好像他们转播中央台的信号也不止是这一次。
李:中央台本身是国家大台,大台又把全部的信号主要转播地震,然后各地方台又传播中央台的信号,使得全部观众能够接受到的新闻都是有关地震的,形成一种很强烈的垄断性的传播状态,你对于这个怎么理解?
包:从基本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就像美国911事件之后,所有台都在滚动播出。毫无疑问,按照新闻规律来说,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地方台转播我们的信号,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缺乏资源。有的也是从新闻从业规律来做的。你如果不转播地震的情况,如果放娱乐节目,百姓也不乐意。
李:从这样的状态来说,中央台这次的报道影响到了整个世界,使得媒体在事件传播中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包:我觉得这次事件对中国的新闻事件报道都是一种促进,在历史上是意义深远的。我倒不是说所谓的功劳、功绩,只不过它对克服以往的很多报道不好的做法,不好的习惯的冲击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好多东西是不是通过这次事件发明出来,创造出来的,我却一直认为大家都有能力第一时间把事情报道出来,只是没机会这么做而已。一个国家媒体的进步都是震荡前行的,这是一种规律。
李:这个是否促成了中国媒体形态的一种转变?一旦国内媒体取得了一定的平台和范围来做一些事情,原有的情况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凤凰台对这次事件的报道开始就很一般,他们自己认为在资源各方面没法和央视比。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包:我一直认为央视从人才资源,从各方面来说肯定是优于凤凰的。凤凰主要是打了一个内容的”擦边球“,但在他们那不叫擦边球了。我们是主流媒体,承担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必须要稳重,有些确实难以完全按照新闻规律去操作。比如这次打通,大家都认识到了这样做很好,为什么以前没这么做?你会发现最后由于运做机制问题,不是央视内部的人也体会不到。通过这次,处于一种战时的状况,很多规矩大家不去考虑的,就开始运作了,这么做完了以后大家发现还是可以实现的。
李:你认为这次的报道是否能分为几个阶段?
包:头几天是救援,看失去联系的乡镇有没有回应,这是一方面。然后到了黄金72小时之后,是继续搜救,看能否再挖到人。再到后来就是堰塞湖,做堰塞湖的同时还报道搭帐篷,进行房屋安置等。
李:有一些受众觉得后面的英雄谱报道得比较多,是否有导向性呢?
包:作为一个国家媒体,需要承担鼓舞士气、引领社会风气的职能。前线所做的一些事情需要鼓舞,从社会氛围来说也需要倡导英雄主义。当然这个是主流媒体的角度。有些社会学家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他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里志愿者的一种善良,他们可以超越一种所谓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持这种视角的人对于“英雄”的说法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倒认为这个看怎么想了,任何社会,包括公民社会都需要英雄,像美国911事件也宣传救火英雄。这是一种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超越于党派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共同存在的,所以也别把这个当成那个国家的专利。但是在媒体看来,一个社会一定是需要英雄的。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宣传英雄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
李:会不会你们每天都会受到上级的指示呢?
包:跟上级的互动是一直都有的,这次跟以往都是一样的。
李:在新闻操作方面来说,你作为总导演,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包:这个跟以往相比就是天壤之别了,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和我们的常态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内行人可以批评我们打乱仗,无序等等,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都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李:你认为这种状态会持续吗?
包:这次地震报道会有一些遗产留下来的。原来我们的窗口是直播的窗口,是定死的,意味着不管别的节目再好,这个时间我们要播出了,其他节目都不能影响我们播出。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活的窗口。昨天《东方时空》就被放到11点16分才播出,因为10点半有一个堰塞湖的新闻发布会。以往大家的生产关系都是固定的,我的地盘我做主。地震之后各栏目的LOGO都不存在了,所有的栏目都是“抗震救灾,众志成城”。
李:在具体的新闻采访业务上,这一次也有人说记者该问什么问题,问地下灾民感受如何这样的问题。
包:网上有很多这个说法,而且我们的记者也很在意,觉得有这个东西是业务上的瑕疵。我们还真就这个问题追查过,发现较多是地方台的。我觉得这都是原来很多毛病、习惯的一种爆发。原来这个业务大家都在说,只不过很多后期剪辑,发现不好的问题都给剪掉了,这次来不及。我要说的是,我们平时这么多的毛病、问题,在直播时候都能被修正了大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相当可以了。
李:这次比较大的问题包括有拍福建捐款时候捐款人手里没拿钱。
包:那个是地方台传送造成的一个疏漏,我也看到了,这个完全是疏漏。
李:中央台这次反应也比较快,道歉之后大概也就过去了。
包:当时人家确实也捐了钱,但当地的摄像,因为他要保证自己拍的万无一失,需要强调的是,钱的确是捐了,当时拍了两盘,一个是演习,一个是真捐。结果传到中央台时就把两盘带子弄错了。而中央台平时和地方台合作还是积累了一些信用,没有发现问题就编了,当天传过来的信号,当天晚上就要上新闻,时间就不够了。这次内部开会也批评了。所以我说,因为我们平时积累了这么多的毛病,所以当打开聚光灯的时候,居然只暴露出这么点问题,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李:你的自评这次怎么样?
包:我觉得99%不敢说,98%或者95%差不多了。我倒不是说不看别人怎么评价,打个比方说像看孔雀开屏一样的,我是站在孔雀屁股后头,你想我看到了我们这么多毛病,开屏亮起来的时候才只露出这么少的破绽。多不容易!
李:这次在这么大灾难,这么大规模的现场报道,难免会比较混乱。你认为在节目制作、包括有些采访方面有哪些可以总结或提高的地方?
包:昨天大家开了一个总结会,总结的都挺多的,提到我们这次设备,摄像机太大了,不灵便,电池续航能力比较弱,在灾区又充不上电。比如说传送手段,缺乏卫星车跟那边联系不上,体积也非常大,应该换成那种轻便便携的,当然台湾同行很多都在用。我们这边因为做这种突发的比较少,这次经过这次演练,大家都提出这种需要。原来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原来只是我们的人认识到应该有便携的,但是也老不用。技术部门,财务部门等就难以协调,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这样就可以推动。
李:你前方有什么特殊的设备吗?因为你们政府资源比较好,比如直升飞机、海事卫星电话等?
包:没有。直升飞机后来是抗战指挥部给分配的一架,在初期的时候没有,完全靠记者跟着被采访单位跑,包括部队有卫星车,他们也跟着卫星车采访。
李:软的这方面的呢,意识啊,技术啊之类的?
包:软的方面我觉得主要是运行机制,关于运作机制大家也学习了不少,讨论了不少,但是要想全面改变是不可能的。目前运行的机制是由政府机制沿袭而来的,政府机制是根本性的官本位体制,它是按照职务高低来设定这一套运行架构的。而国外媒体电视台是业务部门。业务架构和政府架构可能还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两种体制我做了一个分析,各有优劣。完全的业务架构脱离了这个社会的土壤,也有它不合适的地方,不利于生长。政府体制也有优越性,效率高、整齐划一,因为大台比较严谨,讲究不出错,这是它的优势。缺点是运行容易僵化。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往往需要一个冲击,使它灵活运转一下,慢下来之后,又需要一个新的冲击。它不断面临动态调整的过程。
李:有消息说是中央台会在以后实行公司化?
包:早就有这个说法,这是所谓的制播分离。但是我感觉这个步伐还是比较慢的,比如《小崔说事》就是制播分离,崔永元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公司,然后播出是中央台在播出。这是个试点,但是我觉得文艺、体育、娱乐类节目还可以制播分离,新闻可能为时尚早。
李:你怎么看待地方台,比如东方卫视等自己的一些制作?
包:东方卫视我知道,它一直想做主流新闻。但他们的资源可能也不足。四川台表现不错,几乎集中了所有记者的力量去报道这件事。湖南台原来娱乐是他们的主打,我们这次抗灾也用了他们一些信号。所以说,我们这次直播里面打破了原来很多的条条框框。原来不成文的。
李:比如呢?
包:比如对于地方台报道大量的引用。在一个时段里,可能半个小时都是地方台,过去这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些门户之见。但是这一次不管新闻是什么来源,我都能拿来用。即使是CNN都引用了中央台的新闻,挂了中央台的LOGO. 大家意识到,只要是新闻,不在乎是哪个台的,只要观众关注就应该播出。
李:对于国际媒体这次的报道你怎么看?
包:国际媒体这次我接触到的都报道得比较正面,还比较认同我们的报道。他们有很多转载,也很多跟着我们的报道在走。比如说一开始一些国外的媒体到了现场,他们也在开始报有一些衣衫褴褛的人找不到家,说学校工程建设豆腐渣等。但几乎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你在这一刻提这些对于灾区有些不人道,因为没有面对现实。
一个国外媒体的记者,据说在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提问会上,记者本来计划准备问校园豆腐渣问题,结果到了现场他自己都觉得不合适。于是把问题改到了下一步抗灾的重点以及今后面临的问题。中国这次政府非常开放,让媒体随便去报,据说有五六百外国记者到了灾区。还有这次中国媒体也非常开放。很多信息也比较充分,也被国外媒体引用。引用之后便会影响西方社会对这件事的认识。认识充分之后,如果你再报这些问题,受众就会问,是这样吗?媒体也就会开始自我纠正,自我消化,把负面的事情给消化掉了。
李:你这么高强度地工作,心理有没有什么压力?是否需要调适?
包:我也经历过非典,非典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就说有很大的传染的危险。但是我认为既然做的是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定要去报道的。但是以前参与这样的工作从来都没哭过,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爱的奉献”那场晚会的时候,我看的还是上午的重播,看的时候都过去好几天了,我那天看的时候哭了一上午,一直在流泪。
还有后来我们大家在讨论节目的时候,说一些感人的故事,包括像张羽,大家都感动得流眼泪。还有就是哀悼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很多人在喊“中国加油”,当时也是非常感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这么多年也经历了许多事情,中国人已经四分五裂了,网上看也非常明显,任何一件事不论好事、坏事,网上的意见总是一盘散沙。但是这个事情令人感动是,中国人找回了一种信心,一种信念,看到中国人还是没问题的。证明了有大灾大难的时候中国人还能团结起来,为什么感动就是找回了这种久违的感觉。
李:有人说通过这件事情,唤醒了甚至是被遮埋藏了四五十年的中国人心中人性的东西。
包:大家通过这个发现,越是有大灾难,中国人越能团结起来。我们发现中国人将来只可能被糖衣炮弹打倒,不会被灾难打倒,所以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很不同。
李:这次报道你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
包:前几天都是后半夜两三点结束。后来几天是大家轮班,我们基本上是上午十点钟来开会,汇总信息。有同事讲他又获得了什么信息,我们专门有同事是连线组,打一圈电话了解前方记者的情况。然后有地方部的人讲又收集到什么信息,之后我们上午大概确定一下今天可能关注的焦点和主题是什么。然后下午一点半再次开会,有短片系统的,有连线系统的,还有策划的,制片的我们都在一块儿。前方需要视频信号,需要几路,这几路谁负责。短片谁来负责,串联单。然后三点钟开始做串联单。一般是五点左右,串联单就做出来了。
李:你在做的时候会不会有冲动去前线?
包:如果不在做直播的话我肯定去前线了,因为对于记者来说去前线是本职的事情。
李:最后你能否就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新闻意义做一下总结?
包: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们对于新闻规律的认识,我主要指媒体管理者对于新闻规律的认识,毫无疑义都是一次巨大的促进。对于媒体从业者来说,也是找到了兴奋点,找到自己理想的运行模式。我想建立了一个标本之后,你要想完全退到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影响极为深远的。让媒体认识到他们对于影响社会的力量;让媒体懂得应该如何引导大众;如何按照传播规律办事,达到效应最大化。也让央视在如何按照国际大台的规律和逻辑去办事,也有了一个标榜意义。有这样的推动,对大家毫无疑问都是一件好事。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