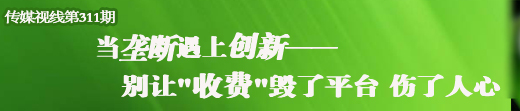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魏海波:如果记者去救人,是我的骄傲
魏海波: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中心主任
魏=魏海波
李=李梓新
李:这次南方都市报在抗震的报道中表现非常出色,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包括网络上的报道部分,与纸媒结合得都非常出色,你应该在这次报道中算是总指挥吧?
魏:也不应该算是总指挥,我是第二天就去成都做了一些前方的协调工作。
李:你是怎样决定要过去的?
魏:5月12号14点28分发生地震之后,当时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楼在晃动,而且我们迅速接到了读者的电话,说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震感,最接近的是重庆的。于是我们就断定这次事件会非常重大,我们启动了紧急的报道预案,因为我们平时都有重大事件的报道预案。有我们的数字报、奥一网、编辑部,消息越传越开,加上整个成都的通讯中断。当时新华社马上发表了报道,说震级是7.6级,我们紧急联系我们在成都工作的同事,结果过了两三个小时才联系上。很快有消息过来,说已经有3000多人遇难,而且还有一个聚源中学倒塌,于是我们整个编辑部包括执行总编辑都投入到事件的报道之中。数字报在事发半小时之后就已经开始报道了。
李:你刚才提到的报道的紧急预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魏:因为南都是一份比较年轻的报纸,真正建立紧急预案是在去年,去年我们建立了紧急指挥中心,重大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报告执行总编,启动整个中心,或者是跨中心、或者是报社的资源进行网络、纸媒的报道。
李:之前的事件中有没有运行过这个预案?
魏:有,之前广州发生的枪击事件也运用过,还有沉船事件。但是这次事件是我们建立预案之后最严重的。后来我们组织完当天的报道,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执行总编庄慎之从外面赶回报社,看当天的版面,而且要策划号外,于是决定派我第二天去成都。
李:后来号外出了没有?
魏:出了。
李:刚才你谈到事发当时在成都有出差的记者,他们一共多少人?
魏:当时因为成都地区的通讯中断,我们就查我们的记者,有哪些人来自四川,又有多少人在那边出差?发现有同事来自四川,甚至是都江堰,但人数很少。但是有两位同事恰好在四川那边,他们是经济新闻中心汽车条线的记者。一位在正在成都机场,另一位是回去奔丧的。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后来发现短信偶尔能够联系上他们,于是他们迅速去往聚源中学。另外重庆记者立即去北川中学,当天晚上八九点钟就到了。后来我们之所以第二天出号外就是因为我们记者在当时的重灾区都有稿件,能够证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你13号去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去前线?
魏:当天下午我们就已经调度各种类型报道的记者,包括深度报道的、突发事件的、摄影记者等,当天下午的机票买得虽然非常容易,但是直到晚上11点都没有起飞,空中管制,我们晚上决定派自己的越野车从广州出发。当天凌晨左右就出发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已经有各个城市的记者。最早的有早上七点多跟深圳的特警、边防去救援。
李:你到了成都,就在成都进行前线的指挥调度吧,你那时候感到的压力大吗?
魏:压力是比较大的。
李:后来一共投入了多少兵力?
魏:三天之后,南都在成都的采编再加上行政人员将近五十个同事。
李:作为南都这样一个日报,它是怎样兼顾它的话语以及专题、它的稿件特写之间的关系?我看到这次南都也有很多专题来讲述这次事件。
魏:当时我去成都已经是13号晚上了,到了成都之后开了一个会,大家觉得灾情基本上清晰了。映秀、都江堰、青川、北川、绵竹和什邡都非常严重。我们觉得应该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怎样面对灾难,以什么态度面对。我们有同事就提出这是一场国难,我们的身份不能说是旁观者而应该是参与者。第二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我们的一线采访应该做一种补充式的采访。我认为即使有100个记者都是不够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无法兼顾到很多东西,跟网络直播,以及中央台的资源和报道经验相比,我们的资源都是不足的。第三个是地震报道有自己的科学规律,在这次基础之上有可循规律,跟国家的政策、经济、文化都有一定关系。我们觉得还是要去现场看一看,于是派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很快,在绵竹、映秀、成都、都江堰等地,我们都设置了记者组。后来还成立了一个成都组,一个调查租。我们当时的模式就是先去现场观察。现场组的同事反馈回来信息;然后我们另外有调查组的同事来做选题。当时我们觉得地震报道是长期工作,刚开始的一个礼拜是救人,然后是安置、防疫、重建、心理辅导等。我们切合每个段的重点,尽量做动态。另外调查的话,有主笔制、选题制,比如说你发现了什么事情,可以让动态组的同事去采集信息,再由你来主笔。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在那样的现场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也更没有办法去兼顾。
李:这个机制很不错,它有一种日报和杂志的结合。
魏:后来我们还有一个航派组。
李:这个完全是商业考虑的吗?
魏:不仅仅是,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大家很容易去 合作。它是一个深圳中海直,负责去那边做救援,我们有记者搭上他们的直升飞机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现场救援的情况。
李:据你所知,这个航拍组是不是国内唯一的?
魏: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比我们做得更好。
李:在市场媒体里呢?
魏:我没有这样比较过。因为我们有同事住在他们基地,所以他们方便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们的记者。
李:这也是报纸在当地的人脉网络和解决能力的体现。
魏:后来我们当天晚上制定了报道的方向,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和通讯中断。后来我们组别的分割就是以车为中心,我们的四辆车14号凌晨从广州抵达成都,又租了一些车。我们要做到北川记者组如果一早出去,晚上回来,在现场没有通讯发不回来稿件,尽量给每个组多派一个人,一般是两个文字,两个摄影。我们规定一组凌晨出发,清晨天刚亮时他们就已到达到现场开始工作;另一组可以多睡一回,早上出发,中午到现场,两个组在两点钟左右互相交接。因为当时没有食物,记者也跟灾民差不多,他们一天可能只吃一片面包,喝一瓶矿泉水。我们虽然也在车里准备了东西,但是他们也都会捐给灾民。通过这种被迫的、最原始的方式,我们特定时间、地点去接记者,记者把当天所有的稿件都带过来,我们进行第一时间的报道。黄金72小时对我们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不具备央视专线传稿的优势。就像映秀镇,徒步进去虽然非常辛苦,我也要求哪怕走到一半,当天还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回来,去青川的记者当天也要有一个人回到广元,把稿件带回来,另外让我们知道大家都还安全。
李:其他资源的支持上,你们是否得到了一些帮助呢?
魏:其实当时很忙乱,比如我们因为知道自己的人手不够,所以寻求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四川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看谁愿意到报社来实习半个月,当时有十多个同学都愿意在我们这边实习。我们让他们留在成都,可以跑一下医院,相关机构等。至于企业合作方面,一旦我们发现企业有商业目的的话,都拒绝了他们。
李:政府方面你们有向他们寻求什么帮助吗?
魏:我们感觉政府在这次事件中做得非常公开、透明。从我掌握的信息来说,在前几天,他们就是想帮你也没有办法帮。在后面的几天中,包括和建设厅、地震局、疾控中心,在新闻发布会上等,我们都有比较密切的合作。我们还有一条线是专盯政府的,分别在北京和成都盯政府口。
李:当时前几天的主线以救人为主,慢慢转移到搜寻遇难者、防疫等等,是吧?
魏:从内容上面讲,南都比较快地建立了框架,对整个事件有我们自己的消息来源。我们从国家到四川省,到各地市都建立了信息源。后来我们的记者和他们的县长、县委书记都很熟,所以消息的来源还是比较丰富和广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同样存在,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我们记者采访到的活着的个案比较少,当时现场还是有一个共识,因为我们的记者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妨碍救援,而且很多伤员一旦被就出来立即转移,除了央视和中央媒体得到特许之外,所以我们不太容易采访到伤员,只能在100米之外看着。于是我们决定做专题的报道,比如失去孩子的家庭,或失去家庭的孩子,做讣闻。我们做一个片区的搜救,比如北川大营救,这是一个典型。后来我们又去做告别北川的报道,为这个城市做了讣闻。后来我们还做了一个系列,叫《学殇》。在客观条件下我们除了自主报道外,还利用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大社的信息进行补充。
李:在前线上,你需要指挥后方的编辑吗?
魏:我们后方有编辑负责人,我和这些同事也有联系,而且我们几乎没有争执。
李:这次的图片用得非常好,摄影记者这方面是怎么安排的呢?
魏:这次我们的视觉中心总监王景春是和我一起到了灾区,一起指挥前方的。
李:他带了有十几名摄影记者吧?
魏:有。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是一同被发派出去的,做搭档。
李:封面的大图一般是谁定的?
魏:我们后方有三个图片统筹,王景春在前线会把比较血腥的图片筛掉。一些惨烈的、未成年人的图片也会进行把关,选择后的图片传回这边,这边的编辑再进行编排,决定怎么上版,有没有做视觉方面的专题,如何进行当天的配题。
李:在成都,前方稿件大致就会完成编辑了吗?
魏:这个没有。成都只是一个稿件的收集,我们的习惯是记者主要传稿到报社稿库,特别重要的我会调阅回来看。其实我这次在成都主要工作是信息整合,做出判断,进行调度、安排记者,给予报道方向上的指导,以及后勤,买一些必备的防护物品,安排衣食住行。
李:去前线的记者回到成都之后,你是否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指导来防止心理上的波动?
魏: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特别地做心理调适,最多只能互相倾诉。因为前几天几乎每个人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吃一顿饭,大家都很忙碌,写完稿子一般到晚上11点,然后才能出去吃个热饭。吃饭的时候才能互相聊一聊。我感觉前三天大家聊得还比较理智,后来慢慢地,惨烈的事情都多起来了。大家心里都会出现一些波动。
李:派去的年轻的记者多吗?报道经验如何?
魏:我们派出的记者绝大部分就像警察刚从警校毕业一样,虽然已经办过案了,但是对这样的大案还是没有太多经验,有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办案了。他们都很年轻,很多都三十岁以下。
李: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需要轮岗休息的?
魏:我们后来强制他们轮岗休息,记者通常一待就是两周。
李:我之前也已经跟一些媒体聊过,发现南都在这次报道中的安排还是井井有条的,而且渗透能力也很强,南都怎样定位自己这次报道的特点、特色?因为南都一直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媒体。
魏:我们当时想的是尽量去真实地去记录、报道灾难。后来我们更多地是尽力做一点事情,或者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后来都没有用力做轰动性的策划。比如说我们在直升飞机上面航拍到一组乡村废墟的照片,没有太多救援迹象,是孤岛。我们决定把这些照片传到网上去,让记者与当地领导沟通。我们不敢说这个有什么作用,但我们也毫无保留。如果是为了发行量的话,我们甚至应该留一天,再去做报道,这样从新闻报道来说会更好。但是我们都没有,我们希望能够提醒救援的人员到当地进行重建。
李:你刚才谈到很多东西发到网上,这次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稿件直接供给网站了?
魏:我们南都本身有南都数字传媒部,所以我们也会直接发稿到数字传媒部的编辑,由他们处理后再在南都数字报和奥一网上发布。
李:稿件在网站和报纸上的分配是否会矛盾冲突呢?是否需要协调?
魏:大的冲突没有。网上的报道一般是抢时间的,有一些是静态报道,就没有必要放到网上。
李:这次你个人对最前线发出的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呢?
魏:我自己对稿件的评价标准不是满意不满意,而是哪些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是否达到了最初采编的预想,比如《学殇》系列、北川大营救等专题。其实现在我们也只做了一个开头,我自己感觉起码要花五年进行汶川地震的报道,比如对于那边的羌族文化的追踪。我们编辑部后方还完成了《七日祭》的特刊,并把这个特刊的内容提供给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拿来义卖。
李:可以看出,这次事件报道中,报社也已经超越了媒体的功能,承担起社会组织者的角色对吗?
魏:对。我们13号的报上就有倡议的捐助,我们12号当天就找到广东省红十字会,倡议捐助,共同开通帐号,最后这个账号上有3000多万。我们南都还进行了版面的义卖,我们拿出几个版面,版面上登的广告,收入都捐给灾区,我们的零售也义卖,还联系了广东医疗系统的专家,组织心理辅导队。南都的很多同事也为灾区捐了很多钱。对于这些我们都没有特别进行报道,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是热心的关心灾区的朋友们做得非常值得赞扬的事,南都只是一个平台。
李:我也看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在招工,是奥一网联系当地民工看能不能来广东找到工作。
魏:对,后来我们跟广东的各个市,尤其是珠三角城市区。看能否帮助灾区的人找到工作。我们做牵线搭桥。
李:想来工作的人多吗?
魏:还可以,他们很高兴。但是当地的很多人还想挖出废墟里的财物,还想盯一下善后的赔偿。所以现在申请的人还不多。后来我们还想到帮汶川卖水蜜桃、樱桃等等。后来我们和汶川的农业局局长还联系了。
李:你是否觉得在这次报道中,南都进一步突破了地域性的界限,确立了其全国性报纸的地位?
魏:从我个人理解,我觉得就南都作为一份报纸的志向和我们现在的影响力来对比,突破地域性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只能说尽量做好。
李:这次地震事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是最大规模的报道?
魏:就我本人经历的采访报道来说,它虽然是最大的,但我们在操作上不觉得措手不及。从十七大开始,我们对两会、雪灾等事件都进行报道,这种项目制都已经成为惯常,我觉得难度不比这回小。
李:你自己有没有去前线看一看?
魏:我心里非常矛盾,因为我自己也是成都人。我去过都江堰聚源中学、也去过绵阳,但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没有通讯信号,以为我的岗位是后方调度。在过去一个星期后,我曾经想过把指挥点搬到绵阳,离现场近点,但明显感觉绵阳的信息汇集速度不如成都,又很快搬回成都。
李:你是成都人,所以在人脉上是否会给去当地采访的记者提供一些帮助?
魏:没有,只是我心理上感觉那是我的家,我如果找的话肯定能找到一些资源。但是事实情况是到了现场我们就开始工作,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找人,而且我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广东,所以在老家也没有太多认识的人。我到了那边就告诉他们,一切靠自己,一定要坚定,靠自己就可以采集到很好的资料。
李:我采访到的一些记者表示,他们觉得救人比写稿更加重要,救人能够切实地帮助那个人,但是写稿却不一定。作为管理者,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魏:我不会强制他们一定要写稿,这种事情我从不过问,大家看着办,如果真觉得救人更重要的话那就让记者去救人。
李: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做呢?是不是在记者足够的基础上才能这样尊重他们的选择。
魏:我个人对他们非常理解,我们每天去前线的记者都会大哭痛哭,会一遍捐钱一遍进行采访,所以我认为首先要让他们做好一个人本能希望去做的事情,我对这个非常理解。在灾后的12天,映秀已经通车了,我们报社的记者几个人一起去映秀镇,当时想去采访校长,映秀镇还在救援和挖掘。映秀的小学伤亡惨重,当时现场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只有一位老奶奶,给我的同事的感觉是生命的蜡烛轻轻一吹就会熄灭了。当时是中午,太阳很晒,老奶奶坐在树下打瞌睡。因为有同事觉得老奶奶是不是已经走了,于是去晃动老奶奶,她的耳朵不是很方便,她一见到人就开始按照自己的逻辑给记者讲述她的故事。她说她还有一个小孙子,她最喜欢这个小孙子,大孙子经常逃课,不好好学习,但是小孙子很听话,一直好好上学,地震的时候还在听课。她这次来带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小孙子最喜欢的,如果小孙子能够活着出来的话,她就给他穿一套有颜色衣服,戴他最喜欢的帽子;如果小孙子已经死了的话。她也一定要给他穿上一套崭新的白衣服,送他回家。大孙子还怒斥这个老奶奶,不让她来这里受。
当时现场的救援人员也给我们的同事讲,这个老奶奶很让他们感动,她在现场发现了好几个还活着的小孩,让他们赶紧去救援。但是当她的孙子被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流脂的状态了。那个惨象,让我们的同事都受不了。后来他们甚至骗老奶奶,说随便找个人告诉她就是你的小孙子,但是还是不忍心。我们的记者劝她回去,但是她不肯,也不吃记者给她的东西。后来我们的记者就帮助老奶奶背着她的箩筐,像她的孙子一样走在已经变成废墟的映秀镇。这次我们很多记者都做了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骄傲,我不会限制他们。首先做好一个人,再做好一个新闻人,这是基本的事。
李:这句话我们在地震中听到越来越多。你在前线一共呆了多少天?
魏:我呆了半个月。
李:中间有没有什么最难熬的时候?
魏:对于我个人来讲,当时已经没什么时间概念了,打完所有的电话都已经是凌晨两点了,然后上网查一查资料就休息,第二天七点又会被电话吵醒,又开始打第二天的电话。每天都差不多是这样。
李:你也不担心余震吗?
魏:我觉得是生死有命,但我很担心在外面的同事。
李:这次事件对你的人生观、自然观有改变吗?
魏:我第一次遇到国悼,全国默哀,当时我是在绵阳的酒店,我同事都去干活了,我刚从九州体育馆回来,一个人在酒店。当时我就特别想看一下那三分钟,普通的街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个人是很矛盾的,因为我虽然觉得默哀应该是闭着眼睛,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睁开眼睛看。本来很繁杂的街道,警报一响起,所有的车停到一边,所以动的东西都静止了下来,一片汽笛声。酒店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曝晒的天气下列队。包括小卖店的老板都在默哀。我很感动。我想到了我儿子,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我一岁的儿子还在生病,我希望他会平安,这是我最大的寄托了。我现在觉得要学会珍惜,包括活着的生活,人应该真心相待。
李:会不会开始相信运气、命运?
魏:我一直很喜欢看自然、地理、历史方面的书。房龙在他的书《房龙地理》写道,大自然有它运行的规则,它要来惩罚人类的时候,人类没有上诉的机会。我一直认为人对于自然是要敬畏的。我因为生长在成都,小时候最喜欢做的游戏就是和我哥去河里捉鱼,那个时候水洼、池塘都很干净,但是我这次报道之后回家了以后发现,所有的水都已经变黑了,一些化工厂、造纸厂开始迁到农村,污染是肆无忌惮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生于唐山大地震那一年,在我人生经历的32年里面,我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有一些人对于财富的追求过高,这个是需要警惕的。
李:你这次回来报社有没有安排特别的休息?
魏:报社有一些专业人员进行的心理辅导;安排了体检;也给我们几天的休息,可能接下来会安排一次度假。我没有参加辅导,我知道我的心理某方面可能有问题,但我不太愿意回顾讲过去的事情,我觉得我更多地要靠自我愈合,可能和妻子讲一些排遣的话更有帮助。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