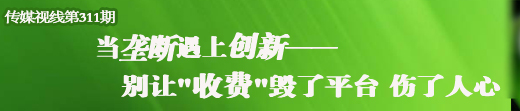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Lucy Hornby:我始终觉得有非常大的责任感
Lucy Hornby: 路透社驻北京女记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到武汉大学修读中文。历任路透社驻上海、北京记者。
Hornby=Lucy Hornby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么时候赶到现场的?
Hornby: 我是第六天去的。我是地震发生的下一个星期天去的。5月18日走的。
李:你正好赶上了哀悼,你在哪里进行了哀悼?
Hornby: 平通。我们到的时候路只到平通,想再往往里面车就走不了。如果你换成摩托车还可以过去,但是最大的问题食物过不去。那边有人在挨饿。
李:平武报道的受灾的人还不多,据您来看是这样的吗?
Hornby: 大部分的记者去了都江堰、映秀、北川等,没有多少记者去那里。
李:你为什么选择去平通呢?
Hornby: 我去平通也没有特意设计,因为我们在北川、都江堰都有记者了,我想不如我去一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看那边的情况。因为我们听说我不少灾民从北川跑出来,但我们估计可能有另外一批人从东面逃出来,所以我们的目的是找离开的灾民,但是没有遇见他们,越走越远之后走到了平通。碰到了一些滞留在那里的灾民,我也就留在那里
李:你去的时候有没有被分配任务?
Hornby: 没有。我们就是说你去吧,看到什么报道什么。
李:你们一共派了多少人?
Hornby: 第一个星期十四个,包括文字和摄影记者。第二个星期大概十个,第三个星期可能三四个,包括摄像师、摄影师等。
李:所以你们的反应上是很快的,地震第二天就派记者过去是吗?
Hornby: 对,当天就已经派记者了,只是成都进不去,只能到重庆后开车过来。然后第二天就进去了。
李:说到你在平通遇上的哀悼,你当时什么感觉?
Hornby: 平通哀悼日的前一天赶上李克强去看望灾民,所以平通弄得特别漂亮,帐篷都弄得好。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大的工作,他们也尽力了。但同时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人还是挨饿。可能因为我自己没有想得那么全面,我到那边才发现原来灾民获得的补给是不够的,能提供最基本的,但他们也许一天才能吃一顿饭,他们仍在挨饿。因为路是不通的,卡车进不去,能运进去的东西也很有限。通路是需要很大的工程的,我们要走的时候路本来已经通了,但是由于余震又断了,所以通路问题还是很大的工程。李: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Hornby: 我们包了一个车。
李:平通的损坏严重吗?
Hornby:很严重,大概只剩四个楼站着。
李:你到了平通之后第一印象是什么?
Hornby: 非常悲哀。平通也是死了好多学生。尤其是小地方的人,他们不仅为自己难过,还特别为别人难过,看到周边的好多学生也都死了,他们很多人用手救了很多人,但是救出来的时候那些人都死了,因为路还没有通。所以他们感到很无助。
李: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忽略了,因为对他们的报道不多。
Hornby: 我觉得因为李克强副总理来了,他们还觉得有一点骄傲的,因为他们能把平通弄得这么漂亮。但是周围的村民还是感觉被忽视的。尤其对于周围一些更偏僻、路又不通的地方,他们得到的帮助更加有限,饥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平通人他们对周围的县也非常担心。平通人很愿意跟我讲话,因为他们希望让我报道他们。
李:这次最开始大家都在说汶川,后来有人说北川其实更严重,于是大家才知道北川。其实这次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人去报道,比如甘肃。
Hornby: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一到成都,人们总是会去最容易去的地方,有开车两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开车去五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报道?但是当地人就会觉得他们也有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去报道。而且是同样严重的情况。
李:这个实际是我们在讲的就做新闻一块来说,在同样这么大的灾区里面,怎么样找自己的新闻角度,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角度?
Hornby: 对,比如我做了平通的一个处理死者的故事。可能对于北川大家还在谈怎样挖出人,但是我在平通碰到挖出来的所有人都死了,但是对于平通处理死者的我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例子,以此来探讨他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
李:你之前有没有进行过灾难的报道?
Hornby:我从来没有,但是我经历过。丽江地震的时候我在丽江。虽然丽江没有那么严重,七级,但是还是有很多楼倒塌了。所以虽然我从来没有报道过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对灾民非常理解。我经历丽江之后,一年里面,如果我在楼里,旁边经过一辆大卡车使路面发抖,我都会觉得是地震,非常敏感、非常害怕。采访时候我跟灾民说你们是不是心理非常不平静,我们心理都非常清楚。地震有一个最可怕,就是声音,像一个大动物,先听到声音才感到波动。我跟人家聊一聊,他们马上知道,我在丽江听过那种声音,但这个声音好像没人报道过。好像地球就是一个活的动物。
地震之后你没有安全感。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小偷来我的房子,我可能几个月以后在我的房子里没有安全感,但是我在办公室会有安全感。但是地震使得你在哪儿都找不到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在那方面我对灾民有一些了解,但是我也毕竟没经历过那样严重的地震,我的家人没有在地震中受到任何伤害,我不可能完全体会灾民的痛苦,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明白。作为一个大的地震,我可以了解。
李:你看到这些严重的伤情,你感受如何?
Hornby: 因为我是第二周到的,所以伤亡的人看的不多。但是这种地震的那种破坏性当然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周围都是伤亡的人。但是最难的是采访那些父母,感觉就好像没什么话能和他们说。你也不想哭,但是你也不能不哭。我觉得这个印象我自己也不能很好地形容。
李:你哭了吗?
Hornby:对对,但是这个很影响我继续采访,这个可能因为我经验不够丰富。
李:我很理解你,我是后来才去的,但是看到那些父母、孩子也还是特别难过。你采访那些父母的时候,他们都愿意说话吗?
Hornby: 还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学生的舅舅这样比较远的亲戚更愿意说话。然后就是一些负责抢救的人。他们也很难过,但是父母更难过。
李: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回忆他们如何逃出来的?
Hornby:是,有的人。
李:你认为这次采访对你心理造成什么压力或者影响吗?
Hornby: 因为关系越远的人越容易说话,因为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这点可能是我不够专业,因为本来应该采访那些离受难者关系最近的,但是他们最难。然后因为我第二个星期去的,他们开始有点恢复了,能吃饭了,所以他们更可以专注于孩子的问题。
李:你在那里待了多少天?
Hornby:六天。
李:去了什么地方呢?
Hornby: 去了都江堰、向峨、平通、绵阳、青川、江油这些东北边的地方。我认为我跑得远一点可以避免和同事重复。
李:你们在前线的时候有没有互相分配?
Hornby:我们基本上没有,都是互相打电话看其他人在哪里,然后去别人没有去的地方。如果有重复,大家就协调一下。
李:待在那个地方有没有给你造成心理压力,让你心理上非常难过?
Hornby:我觉得始终有非常大的责任感,因为你去每一个地方,后来看到报纸还在报映秀或者北川,你觉得我有责任感把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报道出来给大家看。因为问题是,你在里面的情况并不独特,可惜的是死的人太多了,没有房子的人也太多了。但是这个问题是普遍的问题,而你每一篇文章都要找一个不同的角度,虽然我也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报,但我每次找一些不同的态度,所以虽然报的故事差不多,但每次报上一个小城市的名字,也是给他们宣传一下。但是实际上每一个镇的情况差不多。
李:你出发的时候有没有带什么物品?
Hornby: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带一些茶,因为里面的人没有茶,都只有矿泉水。但是我们带的不多,因为军队把最基本的做得非常好,而且志愿者也做了很多。
李:你自己做了什么准备来进行保护吗?
Hornby:做重要的就是笔记本电脑、电话。但是我不喜欢带口罩,非常不喜欢,又热又不舒服,没有必要。因为跟人说话有距离感。我只在一个墓地时戴了,但一出来我就甩掉了。我还带了一个帽子,坐摩托车的时候用。
李:路透社为什么会派你去前线,女性的身份有没有考虑在内?
Hornby:对于所有的记者来说去前线都是他们期待的事情。他们说没有考虑性别的问题。
李:那他们为什么会派你去呢?
Hornby: 路透社要求所有的人都学一个课程叫hostile environmental course(敌对环境课程),所以我们这个办公室里所有学过这个课程的人都去了。有一些人非常嫉妒我们,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课程。这个课程是路透社请人来上的,比较简单的一些自救的方法等,最早设计这个课程是为了那些去报道战争的人。比如你是战地记者,要去伊拉克,你就必须之前受这样的培训。后来他们发现南亚海啸,这个不是一个战争,人们不能提前准备,但也同样非常危险,可以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后来他们觉得应该把这个扩展,让所有愿意接受类似任务的人都接受培训。所以只要通过这个课程的人都去了,但是不是同时去的,刚开始派了四个人。
李: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Hornby: 最早是只对去危险地方的记者,但是后来因为有了海啸之类的事件才改变的,具体的时间我不能确定。记者都很愿意参加这个课程。通过这个课程之后一旦有什么危急情况你都可以去报道,而且也是带薪脱产学习。
李:你花了多长时间通过这个课程的?
Hornby: 三四天。一年一两次,他们请国外公司专门来做。
李:你到了现场之后会不会有帮助别人的想法,是否觉得帮助别人比报道更重要?
Hornby: 因为我到了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那时候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如实报道。如果是第一周去的话可能还有挖人的可能。到了第二星期,能挖出去的都挖出去了。可能第一个星期去的记者会不一样,第二周去最多也就是带一些吃的。
李:你去采访的时候需要什么证件吗?
Hornby: 他们要我们到成都的外国事务办公室办了一个记者证。需要自己去办,但没其他麻烦。
李:办证件有任何困难吗?
Hornby: 没有任何困难,但是要自己去办。
李:后来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过任何阻拦吗?比如有一些地方不希望你去报道?
Hornby: 没有什么阻拦。只有后来去过两个地方,军队的人不是很高兴,不太希望我们去报道,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拦我们,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李:整体来讲,你对这次地震中国的公开度评价如何?
Hornby: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没有碰到任何问题,特别是当地的官员非常欢迎我们,跟西藏的完全不能比较。这次当地的人,特别是当地官员非常欢迎我们,这是与以往相比非常不同的。以前我们经常要解释很久才能得到采访机会。
李:你是否采访了当地的高级官员?
Hornby: 没有,我只是去参加了一个四川省副省长的新闻发布会,但是是比较规范的。
李:你是否得到了志愿者或者军队的帮助?
Hornby: 只是碰到了他们,但是并没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的地方,有一个志愿者非常友好,看我们没有蔬菜给了我一根黄瓜。
李:这次采访路透社对你们有没有什么采访的要求,给你们的采访一些定位上的指导?
Hornby: 没有。因为新闻每天都在变化。
李:这次地震刚好是在国际上对西藏问题报道反应比较强烈的背景下发生的,路透社的报道会不会把这两个事情联系起来对比?
Hornby:我觉得News is News,新闻每个是不同的。只是区别在于西藏政府堵住不让我们进去,而这次当地政府很欢迎我们,我们报道用的手法和伦理都是一样的,改变不在我们的身上。
李:你觉得这次报道受到的反馈如何?
Hornby: 我认为这次报道反馈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地震这个事件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大家都有家人,都能够想象如果哪一天家人全部去世的话会是多大的悲伤。所以大家对这个事件都非常关注,反馈也很多。比如我的家人,他们就每天都看报道,虽然对国际新闻平时都不关注。他们给我发信说看到报道以后非常感动,因为他们特别同情灾民。而且我也有一些朋友都说他们第一次看新闻都哭了。
李:你们在报道的时候是怎样努力与其他国际媒体不同的呢?你们的报道风格本身设定有什么不同呢?
Hornby: 当然我认为路透是最好的,最有代表性。但大部分在中国的记者都非常专业,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灾区发回的报道都非常专业,报道非常好。
李:这次整个新闻环境,你认为对于中国整个的新闻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Hornby: 这次中国记者也报道得很好,但是不是一个突破我想要等到下一个危机再看看,不清楚。这次事件整个过程都向媒体开放,政府也做得非常好,但是是否这样的形式会持续到下一个危机发生,我也不敢肯定。比如说松花江的污染事件之后,一些环境问题也报道得快了。或者SARS,我觉得SARS之后也能看到一些问题暴露得更快了。
李:经历这次事件你觉得自己需要接受心理干预吗?
Hornby:没有,我有一只小猫,和它很贴心,它就能帮助我了。老板说你们自己感觉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要尽管说。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FCC也组织了这方面的讲座。
李:你在那边碰见余震害怕吗?睡得着吗?
Hornby: 我不害怕,睡觉也没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过地震,所以我知道余震比地震小。一般来讲,余震都不会造成特别的危险。
李:你会相信命运、宿命这样的东西吗?经历过这种无常的事件之后。
Hornby: 因为每天都接触比较科学的东西,所以我不是特别迷信。
李:你以前去过四川吗?怎样在一个陌生地方迅速打开局面?
Hornby: 有,以前去四川都是旅游。我都是碰到人就开始采访。
李:你对自己的报道满意吗?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Hornby: 比较满意,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那边的时间太少的,如果在那边更长时间的话会有更好的东西报道出来。如果我可以决定的话,我还会多在那里留一段时间,因为我比较希望能够报道地震后续的事情,这样报道的过程比较完整。这个也完全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责任感的问题,作为一个记者总是有种责任感要把所看到的事实报道出来。但是公司由于希望给每个人去现场的机会所以就让每个人只去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李:你觉得这次路透社的报道有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募捐呢?
Hornby: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国外的人都看国际报道,而且这次募捐的力度确实非常大。我不敢肯定是否大家是因为看到了路透的报道,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报道总体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至于路透报道起到的效果我还不能肯定。
李:你在报道过程中跟中国的记者有什么接触吗?
Hornby: 有一些接触。
李:你对他们的印象如何呢?
Hornby: 我觉得他们非常好,这次在灾区他们也非常专业,不把我们当外国媒体看,我们都是一样的行业。
李:作为女性记者采访会不会有些便利,又有体力等方面的困难?
Hornby: 我的体力比我认识的大部分的男的还好。但在采访上,我不觉得有什么便利。
李:如果下一次再有类似的灾难报道,你将会怎么做?
Hornby: 个人来讲,如果下次再去类似的采访,应该多想一些办法,跟那些最困难的人交谈,比如说孩子的父母。因为这次我主要考虑到跟那些非常近的亲属交谈,肯定会跟着他们一起哭,然后哭了半天也没有用,反而会影响采访,所以我尽可能跟采访离受难者关系远一些的人。但是这些人往往不能代表最广泛的人,所以我认为以后应该找一些办法多问关系近的人,或者找一些他们更愿意回答的问题。
李:你觉得这次发生的损害是否也有地震来临之前科技报道太少的原因?
Hornby: 我觉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很多中国人不懂地震,很多人在博客上质疑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预测?这个是大家不太懂。而且很多人对于余震也特别恐惧。
第二,如果你发现一些建筑比其他地方建筑的要求、标准高,外国人都知道肯定是由于这个地方更危险,比如美国旧金山和日本。但是中国的建筑在这些危险的预防上做得很不好,去现场看了简陋校舍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第三,我还觉得中国很多学校和工厂会锁门,因为怕有人会逃跑,这个在地震的时候就非常危险,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跑出去。美国纽约在20世纪初就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大火,因为门锁了,全厂的人都逃不出去,全都死了,以后美国就出了条例规定必须要有紧急出口,方便人员的逃离。但是中国尽管已经有了好几次失火,但是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条例来保证人们的安全逃离。这些是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关心的,而且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