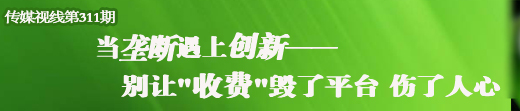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钱钢:从唐山到汶川今昔谈
钱钢:浙江省杭州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及记者,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媒体计划主任
钱=钱钢
李=李梓新
李:您是地震报道方面的专家,从唐山大地震到今天的四川地震的,32年过去了,从新闻报道角度来说,可以作何比较?
钱:有很多西方记者、香港记者也都问我这个32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进步很容易说的,如果离开国家大的变化,单独说新闻,不容易看清楚。32年来,国家的形态、体制、外观等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今天应该有的变化是理所应当的,而第二点来说,我们嫌它变化得还不够快。我曾说过,我无意赞扬。如果光拿今天和1976比,那么变化是很大的。
李:回到1976年,媒体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什么时间能够进入现场?
钱:媒体在地震发生之后什么时候进去,我记不得。但也不应该有误解的就是,当时的地震消息确实也是在第一时间内报道出去的,当时没有网络,不可能在发生的几分钟内就发出报道。当时所谓的第一时间就是“第二天报道”。7月28日发生的地震,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
李:就是那条说唐山、丰南发生地震,军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抗震救灾的新闻吗?
钱:它主要的思想就是说党中央慰问灾区人民。当时的报道不是说唐山地震,而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地震之后,党中央对人民表示慰问,当时的重点在于地震后,党中央对人民表示的慰问,然后第一次报的震级小,是7.5级,这里面还号召大家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深入批邓。记者也是比较快就到的,主要就是新华社的记者,《人民日报》的记者。
李:解放军报的记者呢?
钱:我当时不是解放军报记者,我是上海文艺杂志《朝霞》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是解放军,工农兵编辑。所以说我当年就是解放军报记者的说法是误传。
李:所以您是以解放军的身份,才能前去?
钱:我当时在编辑部工作。在第一时间就申请去了,但是上海虹桥机场不让我走,原因不是因为阻拦记者,我当时的身份也不是记者,我要去参加救灾,并且组稿,他们是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说当时去那边太危险。7月29号事情被报道以后,30号准备去前线,但是8月1日没有走成,于是我就换乘火车,跟着上海医疗队的防疫大队进了唐山。等我进去以后,十天以后,唐山机场那里已经有大量的记者,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记者都有。问题是那时媒体很少,主要是机关媒体,有没有电视媒体我不知道。我认识的人是新华社记者,可是报道的主旋律都是抗震救灾,包括还要继续批邓。
李:那个时候还是阶级斗争为纲,那您觉得这次四川地震报道中人性的东西体现得充分吗?
钱:体现得比较充分。我们拿这次地震与我写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比较。那是改革开放以后,1985、86年前后的社会氛围下面,这种人性的回归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不是等到今天才出现的。那时就已开始所谓弘扬人性的回归。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做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在2006年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问我写那本书会不会很难的时候这样回答:“我在那个时候也这本书有困难,但是不会比今天更难。”
李:那这是不是说今天对比1980年代在人性表达上进步并不大?
钱:进步是有限的。通过你对比我1980年代写的文章和今天的报道,从悲惨度上,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在80年代已经可以做了。还有一个,80年代时候我已经可以开始写反思了。当时我只遇到一个矛盾,国家地震局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要播放我的书的出版。把今天的报道,与80年代中期开始,跟8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的,如1988年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就是“红、黑、绿”的系列报道——三个对比来看,红黑绿的反思力度是今天都希望而没有做到的。
李:虽然进步不大,但是新闻的发展道路是不是走了一个U型的路线?无可否认1990年代中国媒体报道是呈一个下滑的趋势,而今天算是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比如说国力、公民意识觉醒等,重新往上走,其中有一个U型。
钱: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拿今天和32年前比较,进步很大;如果拿今天和SARS比较,进步比较大;和1998年洪水的比较,也有比较大的进步。我说的进步主要是灾难中悲惨的真相,灾难中的人性。这一点在SARS的时候,首先是压抑、隐瞒,到最后实在控制不住了才开始有一些惨状的报道,但是后面大量的还是弘扬抗疫等方面的报道。1998年的洪水,刚开始的时候不许报道,到了簰州湾失事,九江决口,突然转为可以报道,如果想报道灾民苦难实况也会受到批评。但是这一次,百姓的哭声、惨状都是有的,总理身边的哭声也不加删节,都出来了。这个是有进步的,这个方面与以前的几次事件比,与洪水、与SARS都是有进步的。
但是我们如果回溯80年代中期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们曾经新闻改革有很大的突破,1986-88之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还人民知情权,一系列的改革已经推动了新闻的很大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在1990年代又走了一个U字型。
李:希望这个U字型能继续往上长,变成J型或者什么样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80年代,您已经作出了这么富有人性的报道,但是不是今天的传播手段确实已经比80年代好很多?
钱:这个是无疑的,首先是传播速度的问题,我们有了手机、有了博客,这些技术手段都保证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
李:这次央视在报道过程中也传播了很多正面的信息,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钱:我在过去的时候就说,你只要稍微松松绑,中国传媒人就会表现出非常优秀的品质。央视这次度过了一段禁令很少的时期,这个禁令很少的时期使得央视展示出了能量的焕发。包括央视,也包括新华社,这个里面通常所说的黑白两分的党媒体、非主流媒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党媒体里面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新华社和央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面都有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表现都是很不错的,让人佩服。你给他们松绑就会使他们充分地发挥、展现实力。
李:今天的这种人性的释放已经能够成为媒体共识的基础,这个基础在八十年代是否也同样地强烈,还是说在八十年代只是像您这样先知先觉者的个人行为?
钱:八十年代的时候媒体并没有做到这样。媒体有这个理想、愿望,但是还是一部分人在吃螃蟹,就我自己所在的解放军报、或者是人民日报来说都没有能够达到。但是当时我们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尝试,比如通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在做,像其他人和我都是从另外一条路上来。作为一个观念大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文革是摧残人性的,而我们要做的是复苏人性,这是我们达到的一个共识。
李:所以说,那时候还是精英时代的人性传播,今天通过技术手段、比如电视等手段,多少可以把人性的思想传递给百姓。
钱:传递人性方面比80年代是强的多了,传播的效果也包括传播速度、传播面、传播宽度、广度等等,都是强的多了。
李:那您会不会觉得物极必反,这里面又包含着一种反效果呢?央视的报道铺天盖地抢占了所有电视台的节目,尤其是哀悼日的三天,只有少数几个认为自己有一定制作能力的台还在播出自己制作的节目。您认为这种传播效果如何?
钱:这个你看怎么说。在垄断的情况下,它用一种垄断的、统一的方式,但是做的是人性,在内容上可以肯定。在方法上日后是有改进的空间,但是就效果而言、就目的而言总体还是人性的。如果放手让大家去做这个节目的话,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够保证每一个台都能够做出央视的水准,也可能做歪。但是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能够容纳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
李:您能谈一下网络媒体在这次地震中发挥的作用吗?
钱:发挥的作用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网络媒体的话这次的报道怎么进行。我自己在得知这次地震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把我在唐山地震中知道的一些救灾的方式方法能够服务前线,但是每天一篇的文章不是每天都可以在纸媒上面发表出来,却可以在网络上发布。财经网首先登了我的文章,然后是腾讯和天涯,他们为我设了博客,我其实是博盲,我不知道怎么发表博客,但是有朋友在那边一看到我的文字出来就帮我登上博客。有一些文字在《南方都市报》中出来了,但是有的文字没有出来,但是所有在博客上都出来了。当《唐山大地震》2006年再版的时候没有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但是这次当博客上登出这本书的时候,引起了网民朋友们的强烈反响,很多的讨论都围绕书中记述的一些内容展开。天涯的人告诉我,每天的点击量、阅读量都是非常大的,达到100多万的点击量。这个是非常奇特的,他们不光看,而且讨论,这些都是出乎我意料的,造成了一个传播上我没有遇到的效应。而且速度非常快,想说什么话都说出来了。而且竟然也就都过关了。
李:您觉得32年前您在抗震救灾以及采访中的经验在今天的适用度如何?
钱:适用度上来讲肯定要大量地去更新,因为发展到现在,技术水平已经更新换代了好多,技术上当然要更新,这是其一。其二,记者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当时有短处、当时也有长处。当时的短处是信息不发达,因此没有人去抢新闻,没有抢新闻的必要。反而我这样一个不带功利目的的人,我以救灾队员身份在唐山的人,后来又以唐山家人的身份——像唐山人的孩子一样的——我在妈妈的朋友家里住下来在那边呆了三个月,这样的现象在现在又不容易了,当然现在报社能赋予记者这样的使命的话就更好了,但是现在不容易了,更多地是要抢,抢新闻。
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您有点像最早进行公民新闻写作的人。
钱:公民新闻写作今天如果是跑到灾区,能够住下半个月的都不多。
李:今天的公民新闻写作有这个意识,但是未必有这个资源。因为您这样的身份,使得您能够采访当时的一些官员还有灾民,能上直升飞机。今天的媒体能上直升飞机,但它又不是独立的公民新闻了。
钱:当时我没有上飞机,在上海上不了飞机,然后做火车去。我比较奇特的经历是由于我住的这个人家是管救灾的民政局长。所以他把很多救灾的事情都让我去做了,我去护送孤儿到孤儿院,我去采访盲人、残疾人,这都是他给我的机会。这些事情都非常有利于是我日后的报道。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快和以前的慢都是需要的。今天快的都出来了,但是如果说要对灾区有一个持续关怀的话,将来还是要有人进行慢的工作。
李:所以您刚才说的以前的短处不能够抢新闻,长处就是可以呆久。
钱:可以打深井。我当时呆的三个月不说,后来在长达将近十年的范围内,我多次去,这样就可以进行一定的考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相信,调查报告是短时间内很难做的,现在可以看出我当时三个月内做的那个大震前后国家地震局的预报只是一个雏形,这是要花时间的,短时间内搞不定。
李:对于现在很多记者临时带了这个本书上飞机,上前线恶补地震方面的知识,您会不会觉得记者在地震知识传播和科学方面有真空?
钱:有真空,但是这是很无情的一个事实。八十年代由于文革的信息封闭,导致地震十年之后1986年我的书才出来,被人们当作新闻来看。当时的报告文学家就有一个评判,把它称为“冰冻文学的解冻效应”。当时解放军公布的我们解放军就印了68万册,其实我知道很多盗版就印了四五百万册,机器都印坏了。但是U字型低端到来的时候,这本书又被忘记掉了,以至于连我儿子都没有看过我的书,这期间的时间当中有很大的断层,导致地震知识传播的不力。
李:您觉得这个断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们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好像我们把地震都遗忘了。
钱:在中国东部地区,迟迟没有发生过七级以上的地震,已经很多年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唐山以后就没有发生过。这次发生在东西交界线上,东西交界是从黑龙江的黑河划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线你一画就知道,今天的汶川正好在这条线上。这条线以东,财富、经济更加密集的地区,一直没有发生大地震,西部也没有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发生。只有在青藏高原上面发生过一次,但是完全没有人口伤亡。丽江地震已经算比较大的了。地震局反复说高潮期会到来,但是高潮期并没有到来,只是从这次地震以后人们才意识到高潮期有可能到来了。
李:您认为这次事件是否有可能导致以后科技记者的增多?
钱:一定会的。可能不光是地震,也许有科学、救灾、防范、医疗方面有经验的记者都会增多。
李:就采访本身的体验,您觉得在唐山地震的时候,心理的调节有问题么,面对着那些现场的冲击?
钱:现在想起来比较含糊,但是当时一定是有的,特别是看到解放军戴着防毒面具在运尸体,我自己拿着喷药罐喷着,但记忆有点模糊了。我特别感觉到,这一次因为媒体报道特别快,让好多人巨细无遗的感情表达第一时间都公诸于众了。当年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事后采访慢慢讲述出来是很不同的。所以在大家印象中,当年唐山大地震的人民好像比现在的人坚强,或者说麻木,这也可能是媒体传播放大效应的一部分原因,这次会放大很多东西的。
李:您做了那么多后期跟踪的采访、访谈、挖掘,这对今天四川地震之后的三年、五年、十年都是很宝贵的经验,您觉得有什么可以传递下来的吗?
钱:我就是特别希望他们去做,比较纯粹地去做。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两种驱动力的作用,分别是政治的驱动力和资本的驱动力。如果驱动力没有了可能就不会有报道了。政治的驱动力很简单,他有时候希望你去报道某一个事件,你就拼命去报道,但是政治驱动力是会转移的,过些天他又有可能希望染你去报道另外的一些事件,那就不是媒体所赋予你的任务了。另外一种就是资本的驱动力。现在这样做可以增加媒体的影响力、发行量、点击率和收视率,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可能没有了。那还会不会去做呢?这两点如果都除开,个人必须要有一种极大对人道主义关怀、对灾区的关怀,才可能推动你三年五年地不断做下去。
李:比如说更细的采访技巧,受难者心理伤口在愈合的时候,您会怎样打开他们的心扉,不使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更加痛苦?
钱:这里面有两类不同的人。一类人是比较坚强的,跟这些人打交道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对这些人我对他们的采访跟新闻记者通常的快速的采访是不同的。比如我采访的那个十三天被挖出来的老妈妈,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过,只是看着她在挂盐水。过了8年后再去找她,我从公安局卡片中大海捞针,从六个同姓名的人中找出这个老妈妈。然后我再见到她的时候一见如故,像成了她儿子一样,我甚至在她家包饺子、吃饭。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美丽的误解,她认为我就是当时救她的那个解放军战士。这个里面有很多拉近距离的方法。我跟很多唐山人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对我都非常好。因为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不是像现在的记者,不是拿着录音机、采访本去采访和记录。我后来的时候都是追记的,到后来都不需要记录。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八年以后采访、十年以后写出来的东西,到了地震30年之后的时候,2006年全国有很多媒体进行了追访,他们把我里面提供的线索又都搜寻了一遍,你会发现,他们很多说了和我一样的话。所以真的不要以为技巧是太重要的东西,要把自己当做普通的人。而他们更多把我当作救灾队员。你是来救过灾的人,所以他们心理上有亲近感。唐山人对解放军是特别有感情的,当年解放军特别好,因为我也是一名解放军,所以他们也就对我像对待亲人一样。比如我和矿工聊天的时候,就是坐在炕上和他们一宿一宿地聊。他们叫“唠嗑”。慢慢地就唠出了很多细节、很多故事。
李:如果您今天还是一个媒体的领导,派记者出去,您是否会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您希望记者很快地出稿填充版面,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能做得深入?
钱:我想这个问题是媒体第一需要和第二需要的问题。第一需要是媒体需要把事情、救灾抗灾的第一现场的情况最快的时间之中报道出来,用媒体参与救灾。这个时候你不能提出纵深的要求。如果要把一位大娘的心理描写出来,那是是过分的要求,而且没有必要,不合时宜。所以第一时间能做的就是现在媒体在做的事情。然后需要的就是第二需要、纵深方面的问题,是日后一个持续的关怀,需要更加从容、有耐心的采访。我现在如果是媒体领导的话,我就会让记者去抓灾区真相,像《南方周末》一样,报告和再报告。我不会让他们像我十年前一样,那个可能还是错误的。现在让记者坐在炕上和灾民唠嗑,不一定是正确的。
李: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呢?
钱:因为时机和心境不一定是最佳的时候。你如果有能力在旁边观察,静静记录是好的。随着伤口的愈合,灾民慢慢有自己的感受,那时候你再慢慢地进入,关心他们的问题,那个采访时机是好的。什么事情都是抓住最佳时机最关键了。
李:您当时在唐山采访的时候有什么装备或者其他物品准备吗?
钱:大蒜、黄连素,仅有的一瓶糖,椰子糖比较有营养,到了灾区的第一天就被发放完了。简单的笔和本是有的,那个时候我是文学青年。但是也没有录音的设备。但是我是解放军,有一些战备意识。
李:那个时候进入那个地方需要什么证件吗?
钱:有介绍信,我的介绍信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一定要有介绍信。后来我的蒋叔叔因为是民政局长,他给我开了很多绿灯。
李:您是否同意有些记者的想法,认为救人比写报道更重要?特别是第一批进入的记者,惨状还在面前,呼救声还在耳边的记者。
钱:我同意,但是记者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没有专业救援知识的话,得考虑怎样合理地和专业人员结合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有人需要搭你的车的话,肯定应该让灾民上车。
李:您对这次报道的主题、传达出来的东西有什么评价吗?
钱:就大方面来说,这次也生命为核心是对的。我统计了唐山地震和这次地震的头十天《人民日报》的报道。唐山地震中,头十天,《人民日报》中出现“生命”这个字眼的文章只有七篇;但是这次就有149篇。所以你也能理解,充斥在耳边全是“生命,生命”,这是好的。但是这次也不是没有值得反思、检讨的报道。我最担心的是媒体把”奇迹“报道得太多,干扰了救人。所以我在《最后一搏!为生命不为奇迹》的文章中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
李:这次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也有人反驳。您当时说面对这样的大灾难,质疑在那时是不合时宜的,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救人,但是针对这个也有人,如张晓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面对真相的质疑永远不会不合时宜,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钱:我说的现在不是时候,文章的标题是《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事实上不用我回答,大家做的都是救人。你看七十二小时里面,所有媒体,不要说想不想质疑和反思,到了前线都是想的去救人。我说的质疑不合适是说那个时候谈大的面上的东西搞深沉不合时宜。
李:但像《亚洲周刊》邱立本主编也谈到他们质疑了建筑质量,他觉得挺骄傲于这一点,因为他在地震第二三天很早就写出了这个文章。您是否觉得这种观点也是救灾的一种杂音呢?
钱:我不认为这个是杂音,我不支持的“反思”有特指。当时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就有人邀请我在广州参加一个反思会,我说我不参加。我说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我现在全部想的就是想任何办法,包括喷水、送风,把废墟中的人挖出来,而且我认为这是现在最应该做的。看过我写的全文的人不至于产生误会。我说你们要做的这些都是应该的,然后只是现在不是时候,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时刻。
李: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事情,当时如果做反思的话还可能可以做成,因为当时没有禁令。
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说真话的时候不会考虑是否我的话跟别人说得一样。政府是从控制的角度不让你反思,我是从救人的角度不支持反思,如果两者有重合,那没有问题。有人是偏要和政府反着干,政府不让你反思的时候偏要反思,这样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头三天让我去参加反思会,我绝不会去参加。至于说别人要反思,别人有反思的自由,我只是说这个不是时候,要玩深沉更不合适。所谓玩深沉还有一个含义,我拒绝了很多人第一时间要把我带到现场的建议,这是作秀,他想抢一个别的媒体没有的角度。让我现在就去谈历史上怎样怎样,我不会去做这个秀。
李:这次意见这么多,另一个驱动力也是网民比较敏感,反应也比较激烈,您怎么看待网民的意见?
钱:网民的意见我们择善而从。网民的意见如果跟你的见解不同,你让它们和你的意见独立存在,可以是一个并存的关系,这个没有问题。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去利用,更不应该让自己受网民意见的左右,或者为了迎合网民而说一些话。如果我的话有些触怒了网民,冒犯就冒犯了,那别无选择。因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你也可以不说。
李:您有没有想接下来为四川、为地震报道做点什么?
钱:因为我现在还是在香港做研究,我是为一线记者服务的,我自己是不可能做汶川的报道的,我愿意为真正的反思提供建议。比如大家想反思地震预报,我首先讲地震的资料应该善保勿失,我可以告诉大家资料在哪里,而且我列出了几条必要的资料。第一条就是历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它对于龙门山断裂、龙门山构造的判断是怎样的。从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以后的历年四川地震资料在哪里,那么多观测点的观测数据在哪里,因为我是在地震局工作过的,我可以提供给媒体人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你不会是从零开始,我希望看到的是切实的反思,不是情绪化的责骂。骂人不是反思。(i 汶川地震后不久,从六月开始,钱钢即闭门查阅史料,思考地震预警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在八月号在“地震反思”专栏刊登了钱钢的长篇论文《地震预警问题初探》 )
也包括对于豆腐渣工程,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跟坟墓一样的学校,你说它是豆腐渣工程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了。如果你要说周围十万公里全部的学校建造都是豆腐渣,需要证据,你要让我们看到证据。
我说的意思是,不要让豆腐渣工程的罪魁祸首——黑心的建筑商,有逃脱的可能性。四川全省地震的地震裂度是七度,设防就只设定到七度。只要在四川境内倒塌的校内,没有被你看到铅丝一样的钢筋,如果真的是黑心建筑商,就有逃脱的可能性。记者的责任就是要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我们这次都知道刘汉中学做得很好,但是我就没有看到报道中说刘汉中学地震是几度,是极震区吗?如果刘汉中学所处的地区是11级的极震区而它还没有倒,那么它就是奇迹。它为什么没有倒,那它就是做得和防原子弹一样牢固了。但在中国的设防是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筑做成军用建筑的。首先现在是市场社会,我可以做出能防原子弹的房子,但是你买不买呢?老百姓要买他们买得起的房子,它一定只能是某种程度的平衡。
所以这次,我觉得信息不明确,什么叫十万平方公里呢?什么叫破坏最严重的地方达到十万平方公里?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概念。我能够猜测的,十万平方公里是7度区的概念,就是地震七度裂度区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大地震才是大过唐山地震的。在这个区域里,我希望出现一流的记者,去调查哪些校舍应该是牢固的,同样在八度区,当然承包商是按照七度裂度去设防的。学校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设防的,但是为什么周围的房子没有倒呢?
还有一个维修的责任。有些房子是因为多年失修而倒的,还有的学生不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而受灾的,豆腐渣只是其中的一个符号。青川木鱼镇的学校怕学生中午去打游戏,把学生锁在里面,逃不出来的。这是人为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我希望记者现在去补充这种知识。
比如地震设防的标准是大震不倒,中震不坏,小震可修。大震不倒就是房子坏了,不可修了,但是不至于死这么多人。所以现在让我来表达一下的话,当然应该开始反思,但我希望这个反思建立在优良的新闻专业主义水准之上。我们应该把最近十年以来,中国调查报道记者已经积累的最好的品质,最重要的经验进行充分地发挥。我们不要简单地抱怨说政府让不让我们反思,但是我们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定有机会的,政府会改变的。
李:您有没有想过做一些培训?
钱:我在香港这边做了一些,在香港房屋署讲了一些。当然现在确实需要对地震方面有一定知识的人去进行宣传。这需要有一些积累,有积累的人还应该去考虑救灾预警机制的问题。
李:您有没有想过利用你所有的平台帮中国记者提高水平,甚至说让有些人专门做一些项目,达到您刚刚提到的独立、细致和深入地观察?
钱:我现在觉得不止是豆腐渣工厂、救灾反映、地震预报这三个问题,应该还有别的问题。有时候不止是政府做得不好,还有是政府努力做了,比如堰塞湖问题。还有一种中性的调查,着眼于未来的对策、应对,这方面也特别有意义。
李:您觉得这次事件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突破和意义在哪里?
钱:突破是一个证明,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以人为本。它已达到这一步,让人们看到了知情权的进步,它提供更多信息让你来获取的;第二是表达权,它让你有可能去表达了。这两点都要进步,而不要退步。我希望能够巩固。
李:您看好媒体环境的继续良性发展吗?
钱:审慎乐观,我并不兴奋,而且有进两步、退一步的思想准备。我特别想说,媒体人我们是共同体,我们都希望公开开放,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挫折放大,生活会充满了抱怨。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相互打气、舔舐伤口。“你也太CCTV了吧”这样的话很不利于媒体作为一个共同体。这种非黑即白,媒体里面把自己人为地划线是一种旧时代的思维,不利于今天的进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媒体之间不要竞争,要团结,我在汕头大学2005年举行的海啸研讨会上也说过这样的话,一篇好的报道,传得越广越好,为什么不可以让其他媒体来用呢?这个时候生命比任何职业荣誉都更重要。
李:您觉得这次地震之后,大家对于中国媒体的发展会有一些乐观的想法吗?会不会精神焕发,不至于死气沉沉?
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主流媒体中突破了过去的禁区和樊篱,会有一些记者比较昂扬;但是稿子被毙、节目被撤的记者可能会比较灰暗。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两种人都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比较昂扬的人要看到同伴的种种委屈;这次心情比较灰暗的同仁们也要看到毕竟还是有进步的一面。我还是持有一种比较中性的看法。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