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知》(下圖為海報)結尾處,“世界末日”將至,此時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第二樂章適時響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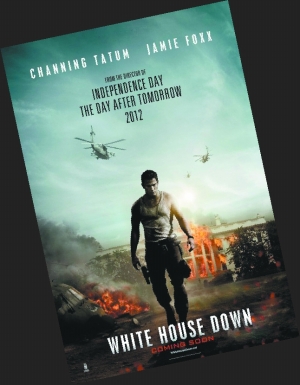
《驚天危機》(右圖為海報)中黑客作案時聽的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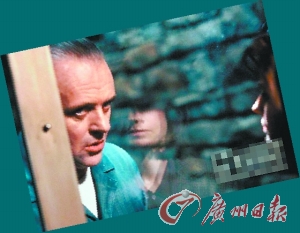
《沉默的羔羊》(下圖為劇照)中,大反派漢尼拔的個人主旋律是《哥德堡變奏曲》。

在《黃金大劫案》(左圖為劇照)中,配樂師王宗賢也曾通過配樂強化反派的個性,他用《在山魔王的宮殿》來強化一個軍官的冷酷瘋狂。
電影《驚天危機》已熱映數周,不少觀眾對片中黑客作案時聽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場景念念不忘。實際上,電影與古典音樂早已水乳交融,相互成就。記者發現,導演最愛貝多芬,這位音樂巨匠的作品在近20部電影中露臉﹔而犯罪、懸疑和驚悚類電影最喜歡巴赫﹔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中那些著名的變態、壞蛋都好熱愛古典音樂。
本報記者 李淵航
貝多芬很忙
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和瓦格納是情緒化的,有時跟畫面搭配的話會顯得太過了,貝多芬不會太過情緒化
經典案例
《國王的演講》:片尾處,國王開始演講,此時的配樂正是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有古典樂迷稱“這力量和勇氣是那樣的健康和純淨,正如羅曼·羅蘭在《貝多芬傳》中所說的,如阿爾卑斯山頂上的清新的空氣。”楊震對此也大為贊嘆:“運用得嚴實合縫,而且飽含寓意,音樂的節奏與整個電影的節奏完全切合,音樂的格調又與國王的貴族氣質匹配,我個人認為電影裡能把該曲用到此種程度的確實非常罕見。”
《先知》:結尾處主人公開車行駛在曼哈頓街頭,末日將至,車窗外人群惶恐慌亂。此時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第二樂章適時響起,寧靜安詳的旋律恰如尼古拉斯凱奇彼時靜如死水的心境,與電影畫面的混亂形成強烈反差。
記者統計了約100部使用古典音樂做配樂的經典中外電影。在有限的統計范圍內,貝多芬的作品最受導演和配樂師青睞,出現貝多芬作品身影的電影近20部。
著名錄音師楊震稱:“首先貝多芬的音樂很多人耳熟能詳,電影配樂直接用貝多芬的作品提高了電影情節、人物的辨識度。另外考慮到成本、配樂質量等因素,用現成的大師作品大大好過請人重新創作,重新創作的很可能難以超越貝多芬,用他的作品是品質的保障。而且貝多芬的作品大都表達的是正能量,但這是一個大范疇的表達,並無過於具體的指向,理解的多樣性決定了他的作品可以被廣泛地應用。”
楊震還稱,貝多芬作品可以跨度很大地出現在不同題材、類型的影片中,在於其作品大部分是大范疇地表達正能量,有豐富的理解空間,在電影中無論是正面地渲染勝利、輝煌,還是反襯悲哀、無望都很合適。“不像有些作曲家很多作品本身即為標題音樂,已寫明音樂所要表達的含義,這就大大限制該作品在電影中的應用,比如也寫了九部交響曲的德沃夏克,其《第9交響曲——自新大陸》向來隻被用作描寫場景,電影中隻有出現相關場景用此曲才合適。”
曾為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紀錄片、寧浩的電影《黃金大劫案》等配樂的王宗賢表示:“柴可夫斯基,布拉姆斯和瓦格納也是能夠戲劇化地表現情感的作曲家,但是他們是極端情緒化的,跟電影畫面搭配的話會顯得太過了。但貝多芬也不會太過情緒化。對於那些想表明‘這是影片中一個特別的、重要的並且感人的時刻’的制片人來說,貝多芬是極好的選擇,因為既引起了觀眾的情緒,同時又沒有打破平衡。”
巴赫很“驚悚”
他的音樂純美、質朴,作為犯罪、驚悚題材的背景音樂會讓觀眾覺得壞人更壞
經典案例
《沉默的羔羊》:漢尼拔冷血殘忍地吃著人肉,嘴角躺著鮮血,配樂響起《哥德堡變奏曲》。
《處刑人》:警察一邊拿著截斷指取指紋一邊聽巴赫。
不要以為愛好古典音樂的電影角色都是謙謙君子和窈窕淑女,不少電影中的殺手、變態、壞蛋才是“真愛”古典音樂。
巴赫的作品是犯罪、懸疑、驚悚類電影裡的常客,不時穿梭其中渲染氣氛。來數一數這一長串的電影名單吧:《虎膽龍威1》、《七宗罪》、《沉默的羔羊》、《賭城風雲》、《一級恐怖》……是不是有些毛骨悚然?
巴赫的《戈登堡變奏曲》用在《沉默的羔羊》﹔《G弦上的詠嘆調》用在《七宗罪》﹔《第一小提琴協奏曲》用在《一級恐懼》﹔《馬太受難曲》用在《賭城風雲》……巴赫的音樂是巴洛克時期的代表,純美、質朴,作為犯罪、驚悚題材的背景音樂會讓觀眾覺得壞人更壞。“就像007電影裡,很多反派都衣著考究,打扮妥帖,頭發梳得一絲不苟,但出手時往往最狠毒、最沒有底線。我們拍片,壞蛋出場都是不和諧音,凡是正面人物都是大三和弦,旋律流暢、光明偉大,這就是 ‘順’的配樂方法。‘反’著來有時更高明。”楊震分析道:“這源自古典音樂理解的多樣性和情緒上的復雜性。常規思維是殺手、壞人、粗人聽的應該都是挺臟的音樂,但如果讓他在干很臟的活的時候聽高雅音樂,這種對比的力量是不是更直擊人心?如果是選取巴洛克時期最高雅、純淨的音樂,效果就更明顯。”
王宗賢則進一步表示:“導演總想賦予反派強有力的身份,以使人印象深刻,通過音樂可以實現這一點——給壞人一個音樂上的動機和主旋律。《沉默的羔羊》裡反派的強硬性格就是通過《哥德堡變奏曲》作為他的主旋律來體現的。很多電影裡的反派邏輯嚴密、有條不紊、頭腦聰明,這種才華也體現在巴赫的音樂中——精確、有條理、高貴、優雅。”
在《黃金大劫案》中,王宗賢也曾通過配樂強化反派的個性。有一段士兵追捕毆打人的場景,王宗賢採用了葛利格的皮爾金組曲《在山魔王的宮殿》。“這個軍官在指揮士兵逮捕中國人,看起來他又像是在指揮音樂,採用葛利格音樂的開頭七個音符作為這個軍官的主題,可以強化他的冷酷瘋狂。”
這種配樂中反襯的手法在電影《教父3》中也有體現,結尾處的仇殺血腥慘烈,哀婉的《鄉村騎士》間奏曲緩緩流淌。“綿密、美妙的音樂渲染仇殺、暴力、痛哭的場景,反襯的力度非常大。導演科波拉這是在電影史挖了一個坑,以后導演此類玩法都難以超越他。” 楊震說。
記者觀察
大片更愛經典曲目
隨著電影制作愈加精良,配樂也做得越來越考究,而很多大片似乎都很青睞經典曲目。業內表示:“古典音樂比較宏大,跟大片氣質相符。大片選用一些經典曲目也比較保險,因為這些音樂已經非常成熟,觀眾對音樂本身不存在爭議。而且這也是電影制作人員一個挺討巧的做法,評論者最多隻能說電影配樂用得不合適,沒辦法說這音樂寫得不好。另外用經典做配樂,性價比高,考慮到預算問題,使用現成的作品好過重新創作,用的作品又是名家的,用得好,很容易出彩。”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