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及普及要求,使得科普期刊的出版研究依然存在熱議,當人們關注於它的經濟效益及傳播科學的功能要求上,逐漸忽略了它作為一種文化傳播背后所應有的價值理性,本文特對此點提出自己的思索。
【關鍵詞】科普期刊﹔人文關懷﹔價值理性
科學技術充當社會發展的重要媒介和手段的作用,在本質上驗証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功能。與科技帶來時代進步所相應的是各產業領域及社會大眾對於科學技術的工具性能濫用,則將越來越多人的注意力轉向環境問題、生態問題、能源問題、戰爭問題等一系列給人類發展帶來困境的高科技陷阱上,這在客觀上証明,單向度的工具理性破壞了主體所固有的審美特性、人文關懷特性、文化價值特性等。若要著手解決上述困境,首先就要從科普傳播的科學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開始。進入數字化時代,各種工具經驗的不斷累積、科學技術的高端發展與科技低端轉化的易得性,將一種理所當然的工具性的功利主義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人們在努力適應新的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各種消費生活方式的同時,技術生存概念亦侵入到人的自我意識和感覺中,大眾慢慢遺失了最初用於完善自我、修繕自身的價值理性,失去了對周圍世界的天然性好奇心。現代人類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各種工業商品的科技時代,卻忽略了追溯它的淵源,甚至忽略了對自身的人文關懷。大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需要基本的科學技術的技能,是作為科學傳播的科普期刊存在的基本需求價值,但科學工具理性逐漸強化的“霸勢”,使得科普期刊承載科技傳播學術創新和提高普及大眾科普素養的責任,愈趨失去人文價值理性,亦是科普期刊被學術界及受眾群冠以“雞肋”傾向的一大要因。
一
現代技術對個體社會的侵入,已使讀者的自由想象力逐漸萎縮,一種直面的觸覺隻相對於我們的視覺神經而感知,直接的“代替解讀”限制了受眾創造力的活動,進而導致幻想與分析力的萎縮,以及人與人之間個性的漸趨標准化(即使這是個人人認為彰顯自己個性的時代)。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最初,為了提高生存質量,推進自身生存狀況,分泌出一種追溯萬物本源的天性,這種自然特性與人際社會關系發展的社會需求融合后,孕育出了當今我們稱之為的科學技術。因為一切有生命的有機體都要從自然界獲取足夠的能量以維持自身生存,這種產生科學技術的最初沖動,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無思想的單純手段或工具而存在,它凝結著人類維持生存與發展的人文及理性價值需求。但由於人類物理性欲望的不斷膨脹、內心生物性貪婪的本能、理所當然攫取世界的天性,導致了在當代運用科技改進消費生活的同時,諸多社會性問題的層出不窮,為技術和文化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瓶頸”性制約。早就有學者發出預警:“科學與理性已經不再僅僅是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進步、啟迪民智、賦予人們力量和自由的利劍,它也可以是破壞人類的生存家園、殘殺生靈、擾亂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幫凶。”
康德認為“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人的價值為自身立法” ,黑格爾亦認為盡管理性是具體的,辯証的,科學理性更可以說是一切科學的靈魂,是人性的底蘊核心的重要構成部分,但人類對自然認知的能力同樣也是不斷深入的,過度的推崇往往也造成價值理性的缺失,甚至帶來人類生存的異化。特別是進入工業化自動時代,工具性能使得人類越來偏向知識獲取的便捷性及手段性,這也是科普出版行業步入新時代不得不面臨的一種工具性的技術倫理。科學理性則是理性的發展在近代與科學的結合,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其實都是一種目的理性,區別隻在於:工具理性所旨歸的目的是短期的、直接的和往往是功利的﹔而價值理性所訴求的目的是長遠的、終極的和往往是精神的。” 從人性角度看,理性其實包含了價值理性的所有因素在其中,其核心便是人的自由、平等、博愛等一切對人類社群自身的人文關懷。文藝復興時期所提倡的科學與人權並舉、理性與人性和諧統一的主旨便是在現代依然可以給我們一個不錯的借鑒與反思。通過韋伯的理論我們可以知道,理性有著其價值的維度,它並非只是指那些關於客觀世界的永恆不變的規律及本質,同時還包括人類借由思考與行動而理智生存的狀態。韋伯認為“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
多端技術的發展與大眾對科技工具性能的普及需求,在一定側面說明了當代的科學理性已經失去了文藝復興時期較理性的人文價值內涵。工業化時代中,在技術層面上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的客觀泛濫,在理論層面上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對事實與價值的區分所加速的學科間分裂態勢,以及對科普期刊在研究批判上注重普及、經濟效能的學術討論,都表明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從最初起源時的融合到如今功利性的對立關系已逐漸形成。在實証主義看來對於知識的認知方式完全取決於實際經驗,已有的科學實驗與技術發展似乎完全能夠証明知識或技術工具的准確性及有效性。單純的“形而上學”的對於知識價值理性的思索相對於科技的具體操作性能,於驗証來說意義似乎不大。就其局限性而言,它認為“一門經驗科學——並不能教人應該做什麼——而隻能告訴人能夠做什麼——以及在特定情況下——他想做什麼。” 。所謂價值理性,其基本內涵是指人們注重行為本身所能代表的價值,而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越來越依賴於科學技術來作為實現人對自然統治的工具。隨著科學理性在人類社會經濟中的膨脹,人存在的目的和手段逐漸發生了倒置。人成為物、機器的奴仆,成為情感淡漠、心靈空虛的工具,導致了人類自身觀念的局限、畸變以及生存困境。
二
科技能夠作為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一方面表現為先進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則代表先進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傳播,科技文化在與其它文化的互動中不斷整合發展,科普期刊的出版發行便是對於科學技術這種先進文化的另一種學術教育意義上的傳播媒介代表。科學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需要在傳播中體現出人類在精神層面對科學文化應有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而非臨時性使用的單純工具或手段的知識搜索引擎。當人們把對科普期刊的關注焦點放在其媒體運作、傳播方式與市場機制的相應要求上,以及“科學普及傳播”的信息廣泛搜集與信源准確傳遞並強化接受度的反饋需求上,或是在科普期刊的出版困境現狀面前,著力研究其他成功期刊的運營模式、編輯機制、市場操作等技術層面的把握上時,實際上就已經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作為一份高檔次的文化傳播期刊,其自身建立的“品牌”效益不僅僅包括上述的幾點外延發展性能,最本質的還有其隱涵於出版傳播內的——對人類自身——終極人文關懷的價值理性。而這個文化人類學傳播的究極釋義,並不是隻體現在期刊界用簡單文字概括出的出版宗旨、讀者定位、企業文化等層面上。
以《科學美國人》為例,期刊內容涉及了幾乎所有的科技領域,當然更多的是自然科學與技術,其編輯們對科學發展有著高度的敏感性,以公眾所喜聞樂見、通俗、生動的語言闡述深奧的科學內容,向公眾介紹科學領域裡最前沿的現狀和發展前景,以及這些科技領域對人類未來的商業、文化、倫理和政治等方面的深刻影響,立旨便是揭開某一事物的面紗讓人們了解真相,以增加人們應對的信心和方法,立足於讓讀者了解更廣闊的世界﹔除此之外,它刊載了大量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章,各期的首篇文章大多便是以社會科學為題,涉及與國計民生切切相關的各社會科學分支。人們盛贊期刊的編輯們獨擅其美,成就了一份高檔次打入讀者心中的期刊。目前該刊有大概16種國際版本,其創刊宗旨 “消遣 指導”也為讀者或其他受眾所熟知。本文隻簡單選取其在2012年下半年的雜志封面作為一個例子進行說明,並列出國內其他有影響力的科普期刊的同期封面作為對比。

圖片 1

圖片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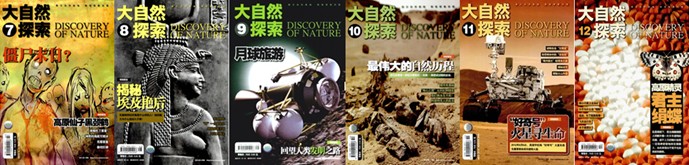
圖片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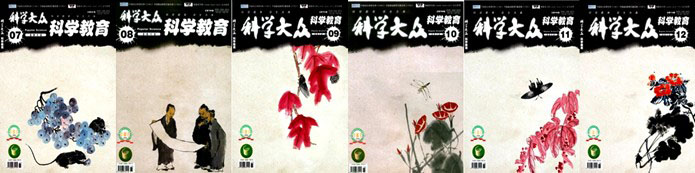
圖片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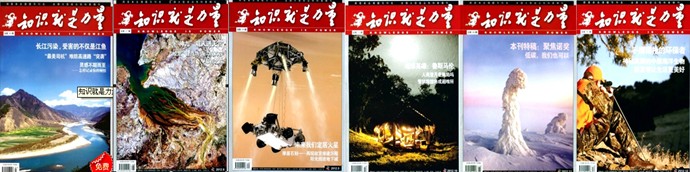
圖片 5
經由上文所給出的部分封面圖片所作出的簡單直觀的視覺性對比,我們幾乎可以完全感知到本土國內期刊一直存在的各種問題。除了在圖片類型豐富度的差異、同種類型的圖片信息量的差距、封面構圖設計的視覺差異、圖面層次靈動性的差異、封面色彩主題節奏等信息情感作用的傳遞差距、在多元結合中對細節問題的重點處理上等一系列不足外,最重要的就是所傳播的價值意義差距。《科學美國人》期刊在一系列的封面上,通過圖片主題展示與文本標題吸引,直面的視覺傳達與顯性的內涵價值傳播,都在向大眾“傾訴”著這份期刊的另一層傳播信息,那就是對“與人類自身生存發展有著密切相關層面的人文關注”。而反觀其他同類知名科普期刊的封面傳遞的信息量,僅有著科技發達的展示或對自然未知等的探索揭秘,人文理性的價值內涵幾不可見。“窺一斑而知全豹”,一份期刊所承載的價值(包括工具價值、人文價值等)是一個社會對科學技術及科學教育意義的認識理解。
期刊發行者對於封面圖片的把握,讓閱讀者(特別是匆匆翻閱瀏覽者)看到設計者充分了解到視覺科學、心理學、美學等相關知識,還有那迸發出電光石火般的人類人文價值理性閃耀的光芒。出版物的期刊圖片一般有兩種處理方法:一種是圖片顯示與文字毫無關聯的新內容——新奇的圖片促使讀者出於好奇心而去閱讀﹔一種是圖片本身就適宜出所要表現的——給那些原本打算隨意翻翻的讀者留下清晰的印象。出版物的成功與否,從刊載圖片的質量就可以窺出一斑,一張圖片的精心設計挑選與否足以決定了一切預期的效果,更罔論期刊的拼版藝術、顏色搭配、段落章節的配置等,這也正是人們通常所言的“細節決定成敗”, 圖片是一份出色的提高聲譽的出版物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發行者與設計者或者說是期刊本身個性內涵的直面展示。
通覽近些年《科學美國人》的封面主題設計可以看出,期刊在版面設計中永遠是將“人文關懷的價值理性”放在編輯的核心裡,“窺一斑而知全豹”,期刊在信息傳達中所要傳播的文化價值角度,在人類審美本能的美學角度的吸引力設計上都在闡釋著自己或者說創作者們的文化傳播價值觀念。在學術界流傳的“從一個國家的科普讀物是可以嗅察出其民族氣息的”基調,在上面給出的幾份國內期刊中則完全看不出,除了《科學大眾》摒棄了其他一切科技型的圖片設計,以簡單的中國元素作為主打,雖顯得有些難以僻類也不失一種“特色”,其他知名刊物均看不出自身獨有的特色。多數本土期刊的封面僅以一副挑選出的應景照片作為簡單的主題訴求與讀者好奇心吸引,完全無法觸及讀者的內在感性需求,自然也無法得到讀者在天性上自然的信任靠近。同樣地,若單獨將一份本土期刊整理出連續一整套的封面主題拿去研究,我們會不無遺憾地發現無法看出其中原本所能表達的系統性價值理念。反觀《科學美國人》等世界級期刊,單單從它們往期的封面圖片就已展露的期刊文化精神足以闡述一個統一的價值理念。
學界內常將學術期刊特別是科普期刊比作是“溫水裡的青蛙”, 一份原本應以自身文化傳播培養出大眾的科學素養與理性思維的科普期刊要走出這種尷尬的處境,除了需要研究其傳播的行為表述及技術層面問題,更要去關注其背后所能傳遞的文化理念。這不是簡單地借鑒其他出版物就可以做到的,最本質地是建立起符合自己國民性的文化傳播價值思索理性。在大眾文化傳播的環境中,讀者的表象需求容易通過一定的技術與營運達到滿足,而對深藏在人類內心最本質的生存人文關懷的引導與培養,才是一份傳播媒介最終的價值效果,才可能奠定出一種高檔次的精神讀物。
科普期刊作為社會媒介的意義就在於將科學知識傳遞給大眾。心理學研究表明,讀者閱讀時有四種心理需求,即求新、求真、求近和求短心理。這所有的需求都隱含在一個需求下:對人類自身的關注。雖然這種關注迷失在“文化工業”的工具理性中,僅作為一種獲取所需信息材料的手段以功利性的速成閱讀需求呈現,而雜志期刊的優勢本身則在於深度報道,需要在期刊編輯創新的過程中更多地去密切關注“深度”問題。曾擔任《科學美國人》主編及副總裁的唐納•米勒說:“出本雜志,就是要給讀者一些在 5 分鐘或 10 分鐘之內讀完的東西,也要有一二小時讀完的東西。”《科學美國人》對科學與人文、科學與人類生存及大眾生活關系的關注,並不體現在理論性的探討上,而是經由每個細節甚至一幅圖片、一段文字,以具有時代性的人文關懷精神去關注科學文化技術,在對科學的解讀中注入受眾的參與交流和互動概念。這就是所謂的把科普期刊不僅僅看作是知識信息源,更是思想精神源,它表象展示的是普及科技的成果,內在卻更應體現哲學的睿智和深沉的價值理性。這些都將重塑和培養起讀者的價值閱讀需求。
如果不能理解人存在的意義,不能理解人的全面發展,不能理解人類將走向何方,又怎能真正體現人文關懷呢?因此,如果能保持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相通的一致性,並將科學理性所建構的精神與人的創造精神相聯系,才能使科學理性擺脫狹隘的功利主義,同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保持內在一致。科普期刊作為一種集文化、經濟、傳播、審美、技術現象等於一身的社會性存在,僅僅以某一類型的知識進行理解和解釋,僅僅把傳播效果放在公眾科學素養的提升上,是完全不夠的。僅以《科學美國人》與國內其他科普期刊的封面做一個簡單的視覺對比,便猶如是作為人類文化傳播中的滄海一粟,而科學文化技術概念的普及與文化價值傳播流變重組和推進的理性思考,把我們推到了以人文精神為價值導向的資本、科學、技術等現代手段的文化傳播需求選擇面前。
三
人文關懷在功利主義的工具性能下的缺失,現代人群在高科技壓力生活中的迷失,甚至異化為技術的、最終被貨幣主宰的物的附庸,形成了人類心靈與生存環境的雙重困境。雖然編輯及創作者在進行期刊出版過程中,特別是對於科普期刊——這類需要在商業市場上取得效益以証明自己市場存在價值的出版文化,被動地去更多考慮將商品屬性(工具理性)一定程度上優先置於文化屬性(價值理性)的問題。但作為傳播先進文化技術的科普期刊,理應擔當起將人文關懷的價值理性在傳播活動中保持其必要的張力和動態恆量的狀態。我們重新倡導將人文關懷所蘊含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或技術性能在期刊編輯出版中進行一種理性意義上的整合,實際上就是要提倡科學理性的人文關懷重塑回歸。利用科普期刊的價值傳播將讀者引入對科學最初的理性思索與情感品德中,使其學會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正確認識人類及周圍生存世界與大自然、人類生存自身等社會關系,並盡量在科普期刊出版的文化傳播中靠近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融合實現。
科學技術的越高速發展,就越需要人類情感的注入,高技術的普及使用與高情感的人文平衡是當代社會文明發展的必然所趨。本文提及的對科普期刊出版所涉及的人文反思就是要以人為“本體”,從人文價值角度重新認識和理解以技術發展為藍本的文化傳播所應有的價值理性,從人類存在價值與發展意義的高度去把握科學技術文化的工具或手段作用。出版鏈的每一個環節都不能以單純的經濟價值與工具理性去束縛和限制人文意識,應在科普的文化傳播中把科學理性與人文關懷統一起來,把人與大自然、周邊世界看作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存在。這需要從發行者與編輯設計者開始,進而在擴大的傳播領域,都首要認識到科學理性的傳播所蘊含的人文屬性,真正恢復科學理性所包含的功能和作用,並在此基礎上發揮價值觀念的引導物質本能,發揮科普期刊作為先進文化代表的應有之義。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傳媒學院)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