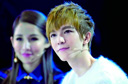前些天,看電影《黃金時代》時,不由得捫心自問:“我趕上了一個記者的黃金時代了嗎?”
我難以給自己一個答案。入行三年半了,有幸進入有著深厚特稿傳統的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我一直想著,踏踏實實地採訪、寫稿,寫出有分量而且有生命力的新聞作品。但近一年來,對於自己一直向往的這個行業,產生了一種焦慮感。
焦慮感是從今年開始積累的,感覺自己好像身處一個飄搖動蕩的“年代”。一方面,是一些記者的出走。所謂的出走,不是過去常有的從一家媒體換到另一家媒體,而是徹底跳出媒體圈,改干別的行當了。那些出走的記者,有一部分是過去我眼中的業界標杆。我是讀著他們的作品、仰望著他們的光芒,走進媒體圈的。出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大多數想必是考量整個行業環境,再結合自己的職業訴求而作出的選擇。來來去去的媒體人,揮一揮手,帶走一陣風,吹到我心裡,增添了幾分茫然。
另一方面,是“偶像”的跌落。如今,媒體圈人士涉嫌敲詐入獄的新聞已不會讓我感到意外。雖然入行時間不長,但已感媒體圈“魚龍混雜”,某些違規違法操作的事情也有所聽聞。我不禁想問:這個行業到底怎麼了?
或許是我個人的感受,感覺社會對記者職業的積極評價在降低。好幾次回高中母校看老師,一位負責學校辦公室工作的老師總跟我抱怨,“學校又被××報敲詐了”。聽到那番抱怨,我心裡微微地難過,很替那個同行感到羞恥,也為記者這個職業略感悲哀。
我在大學受過7年的新聞學教育。學了這麼多年的新聞學,不敢說長了多少本事,但是我深深地以為,“新聞是一個行業,記者是一個職業”。我從不高談新聞理想,但信仰新聞專業主義。我堅信的是,既然選擇做記者,就跟做律師、教師一樣,要遵循職業道德,按照行業標准做事,“打好這份工”。
行業丑聞時有曝出,除了個別人道德品質和法律意識的問題,是不是要思考整個行業哪裡生病了?從記者職業准入到行業自律、他律機制,或者行業生態本身,存在什麼問題?這讓我困惑。
除了那種“飄搖感”,真正讓我心生焦慮的是,在如今的時代到底該如何做記者?
傳播渠道、手段的更迭以及媒體影響力的分散,這些大的行業背景,不用過多討論。今年初,我去有名的“創業圈子”車庫咖啡採訪。一聽說我是報社記者,年輕的採訪對象們滿臉同情地問我:“報紙還有人看嗎?”他們的問題讓我有些為難。我隻能耐心跟他們解釋,“你們沒看報紙但可能看過報紙生產的新聞”、“門戶網站以及移動客戶端上的新聞基本上還是傳統媒體生產的”,如此雲雲,對方似懂非懂。
翻翻微信朋友圈,媒體朋友們都在轉發“××報社總編辭職了”、“××報正在轉型”或“紙媒新媒體部該怎麼辦”之類的文章,焦慮的情緒隨之蔓延。
作為傳統媒體中人,我時常搞不懂,自己辛辛苦苦不遠千裡出差、熬夜寫出來的一字一句,讓新媒體輕輕鬆鬆地復制粘貼過去了。之后,被轉發、評論,熱鬧是他們的,我好像什麼也沒有。
喧囂過去之后,我在心底裡衡量一個報紙記者的自身價值。有時,挺糾結的。感覺自己很像農民伯伯,辛勤在地裡耕耘,種出的果實被旁人莫名其妙地拿去加工和經營。但另一方面,我也在免費享受著別人制作的信息產品。
困頓時,我會想想初心。之所以選擇做一個特稿記者,是因為我對文字有感情,也是因為對寫好稿有追求,雖然這個過程幾乎都是辛苦和寂寞的。
在《冰點》周刊,我們將特稿比作一門手藝。在信息快餐的時代,制作特稿顯得有些奢侈,從選材、採料到烹飪,都要花費很多成本和心思。但《冰點》同仁始終相信,花心力去採寫這類新聞作品,還是有價值的。我想,仍然繼續從事這個職業,正是相信有些東西是值得堅持的,好的新聞內容是有受眾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因循守舊。身處變動的時代,媒體人應該思量當下的環境,比如互聯網的傳播規律,媒體和受眾的關系,新的技術手段和傳統內容生產的結合,等等。畢竟,我們還年輕,還可以去學。
但或者,最重要的還是,踏踏實實地採訪,盡心盡力地寫作,做個本分的職業人,有標准,有底線,即使不會贏得尊敬,至少會獲得尊重。
雖然困惑和焦慮還是有的,或許永遠也不會消失,但在接受那些變化的東西的同時,秉持一些篤定的東西,仍然能尋找到快樂和熱愛。(作者為中國青年報記者)
來源:《青年記者》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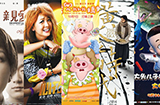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