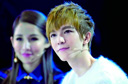當一名記者,是我從中學時代起就有的夢。那時,在我的眼中,記者無所不能,行俠仗義,打抱不平。大學畢業后,由於專業的緣故,先是干了和英語相關的活兒,但記者夢始終揮之不去。
幾經輾轉,夢想照進現實。不知不覺成為媒體人已經四年,自己最閃亮的青春時光,就定格在這一行行的文字裡。寫過的稿子,雖然大多沒有什麼大的反響,但仔細想來,也有的幫助到了需要幫助的人,或推動個別方面有一點點進步。為期不長的記者生涯,走過很多路,見過許多讓自己感動的人和事﹔面對過虛假和欺騙,知道了世界的多彩與多元﹔收到過感謝信,也受到過謾罵甚至聲討,知道了這個職業有很多無奈。
同很多年輕記者一樣,我曾經也有過彷徨和迷茫,但沒有退卻,因為我是如此熱愛這個職業。
我曾採訪過一位75歲的獨身老人。他叫肖世修,在一所學校旁修了30年的鞋,掙來的錢就放在身邊的盒子裡,有人有需要向他開口,他就會從盒子裡抓一把錢送出去。后來老人得了眼疾,沒辦法繼續修鞋了。我聯系了一家醫院為他做手術,在這過程中問他:“您不能總幫助別人不考慮自己,這樣怎麼養老啊?”老人豁達地笑笑說:“我不需要擔心啊,你看我現在有困難了,你們不就都來了,而我從前根本就不認識你。”
我一直記著老人的話。每當工作中遇到迷茫和困惑時,都會忍不住從記憶裡翻出來——我在做我喜歡做的事,那就去做好了,其他的不需要擔心。
2013年春天,我來到大眾網,成為一名網站記者。網絡媒體對速度的要求,讓我的生活節奏加快,承擔的工作量比從前大得多,而且很多領域都是陌生的,稿子不會寫,行業滲透不進去,處處碰壁,一度想逃。
直到有一天,又給家裡打電話訴苦時媽媽問我:當記者不是你自己選的嗎?不喜歡了?后悔了?
放下電話后,我思考了很多,認真問自己:還愛這個職業嗎?愛。愛還有什麼好抱怨的!遇到困難,是真的環境不好?還是自己的能力達不到要求?
在我找不到方向的時候,領導和同事也及時給了我鼓勵和指導。我開始調整自己。採訪中遇到不熟悉的領域,我潛下心來,用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去查找相關資料。每當從一大堆龐雜的信息裡找到有新意有變化的地方,心裡都會有發現新大陸般的興奮。自己採寫的稿子發出來后,我還會上網搜索看看轉發量和評論,當發現自己的稿子被大量轉載,尤其是被行業網站轉載的時候,不由得會對自己說聲“Yes!”。
學習是一種常態,對一些暫時用不著的東西,我也不肯放過。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我採訪一名養蜂行業的全國人大代表。採訪中,我提到不久前自己學到的山東省發布過的蜂業發展規劃的一些內容。他很驚訝,“這是我起草的,但沒想到會有外人關注這個偏僻行業”。哈,這種情況下的採訪自然順利又愉快。
就這樣,我不知不覺間成了“雜家”。學的多了,了解的多了,採訪對象當然願意和我交流,新聞線索甚至獨家線索也隨之源源不斷地涌到面前,自己對新聞稿件的駕馭能力越來越高,也就有了一些內容飽滿的稿子。稿子被肯定時的心情,除了開心還是開心。
因為真心熱愛,所以處處留心。我是黑龍江人,過年難得回去一次。而休假的時候,自己也不閑著,喜歡四處尋找新聞線索。回家過年,我曾在邊防哨所和士兵們一起度過除夕,也曾在看糧人的小屋裡度過大年初一。家人笑話我越來越像一名記者了:“怎麼總是到處找事兒,老是在想寫稿。”
我明白,自己在工作上的痴魔,一定是因為太愛。記者對我而言不僅是一種身份,也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生活狀態。
近年來,社會上對記者的印象不再像以前那麼高大。這讓我有時候有些郁悶和失落。但細想,人家對你怎麼評價,不在於你是干什麼的,而在於你是怎麼干的。於是,我就更覺得應該好好干,起碼不能因為自己的原因而讓別人對我們干這一行的有什麼看法。
現在的記者圈子,難免會有那麼一點浮躁。周圍常有一些聲音,比如抱怨媒體掙錢不多,吃青春飯,沒前途,想轉行、跳槽者大有人在。我想,困惑和動搖的時候,我們年輕記者應該以一代又一代的優秀媒體人為榜樣,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知道,社會越發展,文明越進步,記者的價值越會得以體現。因為,主流價值的傳播,影響社會的走向,影響每個人的命運。(作者為大眾網記者)
來源:《青年記者》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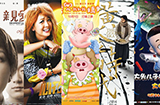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