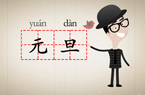香港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重要源頭。中國早期的近代化報刊,也就是所謂的“新報”,正是鴉片戰爭以后在香港興起的。其中,19世紀70年代是值得特別專注的關鍵歷史時刻,在此期間香港中文報刊經歷“雙重轉型”——形式上紛紛由“周三次刊”轉變為名副其實的日報,在更深的層面上則是中國報業先驅逐漸擺脫洋人操控,開始獨立辦報。不過,因為第一手資料的缺乏,新聞史學界對這段歷史一直缺乏充分考察。以當時並存的三大中文日報為例,《香港中外新報》僅存一份原件,《香港華字日報》隻有一期影印件,《循環日報》留存情況最好,約有半年的原件。
這些有限的原始資料,大多由卓南生教授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掘出來。依據發掘出的報紙原件,卓先生對早期的近代中文報紙進行了精細的考察,推翻了一些流傳多年的錯誤定論,貢獻了大量新穎可靠的知識和見解。對此,方漢奇先生曾贊嘆“在中國新聞史學界引起了石破天驚的效應”。卓先生的代表作《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也成為近代早期中文報刊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時隔近三十年后,卓南生教授再展光華,在新聞史料發掘方面做出新的貢獻。2014年11月2日,中國新聞史學會的盛大年會在暨南大學舉行,卓先生在大會主題發言中宣布了他的重大發現:《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初期兩年又三個多月(1872年5月6日第9號至1874年8月25日第442號,內有缺號)多達400余份報紙原件,現存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通過考察上述大量原始素材,該報早期面貌進一步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探討近代中文報業早期歷史的一些關鍵問題,從此有了新的線索與依據。11月6日,在“北大新聞學茶座”第42次活動中,卓先生進一步闡明這項重大發現的背景、過程及意義,並由此展開,與出席本次活動的青年師生分享了他對新聞史研究方法論的思考。

新發掘的最早一期的原件:第9號(1872年5月6日)
從“碩果僅存”的一份原件到400+
卓南生教授首先介紹了學界對《香港華字日報》的研究情況。1895年1月,該報報館起火,創刊以來經年累積的就存報紙,盡遭焚毀。此后數十年,因為缺乏第一手資料,該報的早期歷史一直模糊不清,比如最基本的創刊日期等信息,就存在多種說法。1923年,《香港華字日報》籌備六十周年紀念刊,將創刊年份確定為1864年,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一書中也持同樣看法。在這次紀念慶典中,該報曾經懸賞征求舊報,后來隻有一位澳門讀者應征,獻出一份1873年6月4日的報紙(第176號)。這份報紙,便成為唯一為人所知的早期《香港華字日報》,后來的研究者隻能憑借著一份報紙,來推斷該報創刊初期情況。

此前,被視為唯一留存的“176”號影印件
上世紀八十年代,卓先生對該報“創刊於1864年”的說法產生懷疑,因為按照簡單的推算,從1864到1873十年時間裡,如果每周一三五出版三期,報紙的總期數肯定遠遠不止176期。鑒於這份報紙在近代中文報業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為了正本清源,卓先生多方求索,努力尋找原始材料,最終在大英圖書館和香港大學圖書館找到《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中外新聞七日報》,該報在諸如“告白”等內容中,明確表示將在1872年4月易名為《香港華字日報》自行刊印(此前以中文專頁的形式,作為英文母報《德臣西報》不可分割的一頁,每周六出版)。1985年,卓先生在日本《綜合新聞事業研究》發表論文,憑借著上述直接証據,以及《香港藍皮書》等多則間接史料,旁參互証,精細辨析,卓先生令人信服地推翻了長期以來新聞史學界及《香港華字日報》自認的“創刊於1864年”的說法,得出該報創刊於1872年4月17日的結論,並推斷該報是在1873年6月4日之后才發展成為完整的日報。
如今,卓先生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發掘了該報從1872至1874兩年又三個多月400余份的報紙原件,一改此前隻有一份影印件可供參閱的窘境,使得該報一躍成為當時三大中文報刊中資料存留最豐碩的“富礦”。通過這些第一手資料,卓先生進一步厘清和印証了該報的早期面貌,確認了自己早年對該報創刊日期等諸多推斷,訂正了該報從“周三次刊”改為日報的准確日期:1874年2月21日。
介紹完這段《香港華字日報》的研究史,卓先生感慨道:“從事新聞史研究的人員,經常要面對資料殘缺的情況。甚至可以說,殘缺不全才是常態。”戈公振晚年經常隨身攜帶《中國報學史》,一旦遇到新材料,就著手補充和修訂自己的論述,卓先生對此表達了“同情與理解”,稱贊“戈公振的這種嚴謹踏實的作風,值得后人學習”。
新線索與新論據
卓先生認為,《香港華字日報》大量新原件的發掘,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為探討轉折期香港中文報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線索與論據。新原件不僅呈現了該報擺脫西報母體、獨立辦報的過程與足跡,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報業先驅們相互合作、共克時艱的密切關系。早在《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一書中,卓先生在“總結”部分便寫道:“萌芽期中國近代報業史,其實正是一部中國人要求擺脫外國勢力對傳媒的控制,爭取言論自由,從而表達國家民族意識的斗爭史。”新材料進一步佐証和充實了這個判斷。
卓先生先從“唐人主筆”的辦報理念、自我定位談起。最早於1857年創刊的《香港船頭貨價紙》(《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附屬於《孖剌西報》(The Daily Press),形式、內容及立場與英文母報高度相似,堪稱英文母報的中文版,不過從創刊開始,《香港船頭貨價紙》就強調要登載“有益於唐人”的文章。1871年3月創刊的《中外新聞七日報》,雖然只是寄生於《德臣西報》、每周六出版一次的中文專頁,但從一開始就打出“華人主持”和“沿著華人意旨辦報”的旗號。
不過,后來的事實証明,陳藹廷所夢想的“華人主宰”、“西人無預”的願景,並沒有實現,因為《香港華字日報》畢竟仍然附屬於《德臣西報》。1874年2月4日,《循環日報》的發刊詞《倡設日報小引》,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中文報紙的致命缺陷:“然主筆之士雖系華人,而開設新聞館者仍系西士,其措詞命意未免徑庭。”這正是中國報人痛定思痛,決心籌集資本創立一家“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報紙的原動力。
介紹完中國報業先驅們的辦報理想和現實困境之后,卓先生接著從中華印務總局、《循環日報》與《香港華字日報》的人脈關系和互動支援入手,考察他們同心同德、共克艱難的具體過程。《香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當時並存於香港,按照常理推斷,兩報應該為競爭關系。不過,翻看報紙原件則發現,《香港華字日報》從1873年2月至1874年2月連續一整年的時間裡,近乎每期都刊載《循環日報》出資方中華印務總局的啟事,包括宣布《循環日報》即將創刊和已創刊的告白。
卓先生認為,結合當時中文報刊謀求獨立的歷史背景及陳藹廷一度身兼兩報的行政主管來看,《香港華字日報》與《循環日報》之間的密切合作,恐怕不能簡單歸結為商業(廣告)往來或文人之間的志趣相投,更是體現了中國報業先驅們齊心合力,致力於“專裨益我華人”的共同新聞事業而彼此支援。
“新報”與“邸報”的關聯性
在卓先生看來,《香港華字日報》對邸抄、《京報》等內容的轉載情況,值得特別關注。翻閱新發掘的大量原件可以發現,該報在1874年2月改版(由“周三次刊”改為日報)時曾宣稱,將以《京報全錄》代替《選錄京報》,即從部分轉載改為全部刊登。果然,改為日刊之后,《京報全錄》經常佔到新聞版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而且,改版后《京報》內容轉載的版面位置,也變得更為重要——改變前的順序為:《中外新聞》、《羊城新聞》、《選錄京報》,且《京報》轉載經常省略﹔改版后的順序則為:《京報全錄》、《羊城新聞》、《中外新聞》。
除了《香港華字日報》外,另外兩家中文報刊《循環日報》和《香港中外新報》也大量轉載《京報》內容。由此可見,在19世紀70年代香港中文報業激烈競爭的轉折期,《京報》的內容仍是各中文報刊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進一步印証了卓先生在《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一書中的論斷:“盡管中國近代報刊的誕生出自外來的因素與刺激,但很快地就與中國固有的‘古代報紙’有所結合,先是模仿‘古代報紙’的書本式,后是轉載其一部分內容,並將之吸收為其組成的一部分(后者最終被時代所淘汰),而成為早期近代報紙的一大特色。”
上述新材料說明,在“新報”蓬勃發展的時期,作為“舊報”的《京報》曾有過回光返照的現象,這是中國近代報業史上的一大特色。卓先生提出,寓居“新報”的《京報》緣何一度受到格外關注與重視,又緣何沒落和最終被時代所淘汰,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話題。
卓先生認為,就研究方法論而言,為區分“新報”與《京報》(“古代報紙”是否為最恰當的用語固然可以探討)之差異,將兩者分割開來辨析,或許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但全面否定兩者之間的關聯性與連續性,恐有欠妥之處。
他強調,《香港華字日報》大量新原件的發掘,無疑為我們近代報史研究提供了解讀這一獨特現象及其所蘊含意義的重要研究素材與作業。
圖片:卓南生教授提供。
(撰稿/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李海波)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