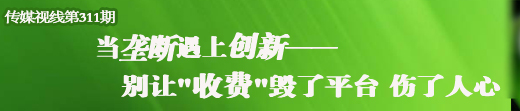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點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很多媒體同行已經在前線採訪或在奔赴前線的路上,人民網傳媒頻道把李梓新所著《災難如何報道》一書中的“汶川地震媒體操作實錄”予以刊發,希望能對在前線採訪的同行提供一些參考。該書2009年1月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裡,你可以讀到來自12家中外媒體的主編、主任和記者們對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憶和感想。
王愷:我經歷了極度憤怒的狀態
王愷:《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曾供職於《東方早報》
王=王愷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麼時候去的?
王:我當天從上海回北京之后,當時主動給編輯部發了短信詢問是否需要我去。 因為當時發生地震大家都知道,但究竟是什麼事情,沒有人清楚,去不去還沒決定,採訪的情況也沒有籌劃。 晚上六七點的時候,打電話來要我去,我就愣了一下,我說就我一個人去嗎?他們讓我先去,然后具體事情再定。
這時一個攝影記者也和我說他被派去了。晚上八九點鐘時,另一位同事告訴我他也受派遣和我一起去。這位同事的太太還正在懷孕期。 當時已經訂不到票了,隻能訂到重慶的票, 訂到13號下午三四點鐘。基本就確定我們去做救援為主的主題,做封面,然后再派幾個人去。我們有兩個女同事主動請纓去了。
這兩個女同事比較幸運,她們剛好訂到直飛成都的機票,所以反而比我們先到成都。我們13號晚上六點到了重慶,三個人立刻包了一輛車去成都。 當時很多人都要走,包車很貴,要1200塊,平時隻要五六百塊。我們當時情緒還不錯,我們第一次遇到這麼大的災難,而且沒有人能夠預料到究竟是怎樣的情景,具體死亡人數都不知道,而沒有人給我定任務之類的,領導也沒有指示。我們包車走了五個多小時,到成都已經是凌晨一點多。在車上的時候,我們就稍微談了一下分工。當時我確定去北川。而我那兩位女同事在飛機上碰到一批軍隊,就跟著他們直接去汶川。大致我們是以地點來分工的。沒有任何設想。 后來才知道后方也很著急。他們也很茫然,他們還很后悔沒有給我任何裝備,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帶了很多東西,我們什麼都沒有。 相對來說我們以前去的很多地方都是城市,很容易利用包車之類的交通工具,所以這次也大意了。我們三人居然穿著皮鞋。
李:你是凌晨一點鐘到成都的,沒有休息就繼續趕路?
王:當時就包車了,當時碰到南方都市報的兩個記者,他們包了一個旅游公司的越野車。我們從他們那租了一輛越野車過來,每天要1200塊。
李:看你的文章特別有印象的一段,是描寫從重慶到成都的路上,雨下得很大,給人以一種無形的壓力感。
王:那天確實有這種感覺。不知是主觀還是什麼,盡管我們說笑,但我們有種不祥的感覺。 確實那天雨很大,是扑面而來的,隻有車燈卻什麼也看不見,不知道前方是什麼。我們去的旅館電梯還不開,我們住的是五樓。這種種因素就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更為強烈的感覺是這件事是不能回避的,盡管我沒有跟家裡說要去災區的事情,怕家裡擔心, 但作為一個記者,處在這個時代,又帶著媒體的任務。我能知道這個是不能逃避的。
14號早晨就直接往北川走,路上還沒有管制,但路況不佳。我們從成都包車往綿陽走比較緩慢, 但是那天救災通道已經開放了, 你能看到消防車、救護車在走,收費口也已經開放了。 當時仍然沒有到災區的感覺,因為沒有真正看到死亡。而真正有災區感覺的是過了綿陽往北川走的時候,我們在等朋友的時候,看到有一些人陸陸續續的從去綿陽找自己親人的, 臉上都很緊張,膨脹著臉, 那時我才意識到面對的是什麼,這不是一個很輕鬆的事情,而是非常可怕的大災難,越往裡走,這種感覺越強烈。
5月14號已是地震發生后第三天,陸陸續續走出來的不僅是北川縣城的人,還有山裡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氣很熱,人們卻穿得很多,有人穿的是棉服,他們已經把家裡能夠拿的都帶著走。 他們不是痛哭流涕,而是一句話不說,比較木,低著頭往前走。這是人在遇到巨大災難后的反應。在沒有見到現場之前不會體會,聽到別人描述也不能夠明白。 我們的車走到安縣時被攔下來。但我們又攔到一輛車,裡面是中央電視台的人,有個人我認識,所以我們就坐上了,但這輛車能到的地方離北川也差很遠,剩下的路程我們隻能徒步。 但是沒有辦法,必須要進去。當時看到外國記者一位外國記者穿著吊帶裝和高跟鞋都在往裡走,那我們也沒有理由退縮。
沿途的路已經斷裂了。不過我們隻走了兩個小時就到了北川中學,而我的同事從都江堰走到映秀鎮,走了10個小時。我們進去之后看到災區的亂象,我的朋友拿起相機到處拍,后來找不到他了,而我有一直沒有那種沖動,是回避的感覺,我看到的是救災,那麼多的帳篷,那麼多的搶救。可怕的是我在北川台階看到的許多半截的尸體,看得出是學生,還穿著校服。那是兩個教學樓之間的台階。我呆在那裡,經過這兩天的整個過程之后才慢慢知道什麼是地震。 你看到人們的那種茫然,無論是找孩子的家長,還是搶救者本身。沒有人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我覺得我把自己的記者身份拋棄了, 你看到那些悲痛的人們,是無從問起的。 當時操場上有許多尸體,人們正在處理, 公安局的人叮囑要留下DNA以供以后鑒定。給我印象很深的是當時有一具的尸體,臉已經腫了,別人告訴我,這不是老師,而是一個小孩,在解剖學上叫腫大。在那樣的情況下,你很難有耐心和毅力去問那些家長,去盤剝。 當時北川中學后來成了一個所有人都會去的明星點,但我覺得最震撼的是家長的那種茫然,沒有哭聲。
當時有個一醫生告訴我他是專門去截肢的, 要迅速保留生命隻能截肢。 我那時覺得所謂救援之類的都是沒有任何意義,在一個災難面前人是很脆弱渺小的。當然北川是一個極端例子,我同事去的很多地方,都能夠讓人理性思考,但北川不行。整個都被摧毀了。
李:過北川中學后你就去了北川縣城嗎?
王:對。其實縣城原來一定很美,三面是山,淡藍色的。我當時沒有能力進行採訪。 很多人說時間在地震那一刻被凝固了,但我到了北川覺得可怕的是時間並沒有凝固。 山體仍在滑坡,余震還在不斷發生。 其實我在剛開始去的時候,並沒有感覺害怕,當時也會經歷一些余震,但隻有看到死亡的情狀之后才慢慢意識到恐懼。第三天的時候,我已經非常害怕。北川是一個死城,除了尸體的味道之外,什麼都沒有,沒有燈光和水。我不敢在裡面住。
李:你去的時候還有呼救的聲音吧,你有什麼感覺?
王:開始還有感覺,但是進入縣城,就變得更加脆弱了。到了北川縣城,人就更加木了。
李:你會不會想去救援?
王:我隻能拿棍子去敲,當時不能夠跟救援人員對話,會讓人想哭。 我隻能和其他人一起往外扒。 當時很矛盾的,你想去救人,但是無能為力,隻能看著救援人員用專業技術去救。而你隻能安慰家屬。你會覺得自己很差,沒有救援的能力, 我沒有聽到幼兒園裡小孩子的哭聲,但別人都說有,你慢慢聽。這一切都讓人感到沮喪、羞愧、崩潰。有時對救援力度不夠又產生了憤怒。 我們回去的時候沒地方睡,隻能睡在操場裡,晚上不斷余震。在現場是處於一個極度負責的氣場裡。
李:那時你想沒想過自己的任務?
王﹔當時我沒有做正規的採訪,僅僅就是與別人聊幾句。我是在回綿陽的路上接到主編的電話,他問我可不可以去一些縣城,那時他不知道我在北川,他們一直在進行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地區來分的。 我當時不想說話,就挂掉了,后來的電話也不接。到了晚上,他又來電話,說要讓攝影記者去拍照,而我堅決的就推掉了任務,覺得自己到了北川之后已經無法做其他事情了,還覺得所有后方的都應該被罵。
李:我採訪過的記者很多有這種狀態。后來你又是怎樣回到寫稿狀態呢?
王: 之后的幾天一直沒有採訪的狀態,一直想要去參加志願者,本能地想去北川,每天都走那段山路。有時會有開摩托車的農民義務帶你一段。我始終處於想幫人而幫不了的狀態。 到第三天的時候,已經沒法和人交流了。那時想找發泄口,有時會大聲罵出來。我覺得好在我們是周刊, 不需要像日報那樣每天都有計劃。 后來我去了醫院,本來覺得或許那裡的採訪會讓人舒緩一下, 沒想到那裡有許多小孩,情況更加嚴重了。我看到了許多人間地獄的現象,獲得的很多是畫面式的片斷。 我當時已經不關心我的同事在做什麼,我隻關心盡到我自己的責任。 星期六晚上,我跟編輯部那邊通話,只是為了和別人說說話。后方說我們都要面對這些,我們也不是要催稿子。這時我才知道我的兩個女同事去了映秀,另一個要去汶川, 還有一個跟著軍隊走。當時我覺得那是三聯歷史上最沒有策劃的一次報道。前方怎麼樣沒有人知道,我們都沒有反饋信息。
李:你們的截稿期是什麼時候?
王﹔我們的截稿期一般是星期日晚上。當時是5月18號晚上,但一般會拖到19號周一早上。最后回成都,不得不去寫稿子了。 因為我在綿陽沒辦法上網。我開始認為我應該把自己經歷的都寫出來, 但我已沒有謀篇布局的能力了,這一點就不如日報了,日報雖然每天都要寫,但交稿后就沒有事情了,而我們就不同。還有就是我不知道怎樣去把這件事用較好的語言寫出來。主編讓我們先寫一個我們路上的具體經過。我之所以心情能夠得到緩解,是因為看到北川劉漢小學的孩子們,他們全都安然無恙地住在綿陽的一個中學裡,孩子們讓我的心情得到了好轉,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災難,他們的天真讓我覺得人生很美好。 還有就是個人的斗爭的勇氣。如果說災難是洪水,那麼諾亞方舟就是人的勇氣。當時我寫文章的願望才回來。 我晚上寫到一萬字時,接到了有史以來主編給我的最溫柔的一個催稿電話。 其實經過這幾天的反思,我已經是從情緒中走出,能夠寫下來,帶著一種理性的感覺去寫,每一件事,這也是雜志的一個好處。 我分了兩天時間,寫了兩萬字,但寫完后的感覺是被耗盡了。
后來兩個女同事去了映秀,給我打電話。接到電話時真有點劫后余生的感覺。在成都的那天電視台預報有余震,要大家往外跑,我們站在路旁,沒有車,也不想往外走。后來想想,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包括以前爬廢墟時,路過的兩根鋼筋,我覺得自己真的爬不過去,但是沒有退路,隻能往前走。映秀那兩個同事也說,走了六七個小時之后,沒有退路,隻能往前走。
李:那你的兩個同事在映秀的時候是怎樣的?
王: 她們在映秀看到的沒有我的慘,她們主要是體力上的辛苦。 其實盡管我們沒有策劃的,但每個人的表現都不一樣。比如這兩個女同事就是大量採訪,要還原地震的情況,地震瞬間和之后的七十二小時。另外一個男同事注重理性思考,採訪了許多交通方面的人,他想要解答的是為什麼進不了汶川。我則解答北川是什麼樣子,人的狀態。還有一個同事要說的是為什麼人被救出來之后還會死。我們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興趣去解答自己碰到的問題。 這種沒有框架和方針的情況下,每個人去交易一份答卷,這對一本雜志來說是很可貴的。
李:你們主編朱偉說,他看到你們的文章就覺得整本特刊有底了。
王﹔我的文章是讓他哭得最多的。那時主編不知道我們每個人在寫什麼,但他計劃做一本全是地震報道的特刊。幸好我們每個人的每篇文章都能夠壓得住,都能做主文。那次也是第一次,整本雜志隻做一個主題。一百六十頁的雜志,來了十個記者,七個文字,三個攝影。平均每個人都要負責十多頁。這個任務能不能完成,他們也不知道。
李:那你們前方貢獻了多少文章?
王﹔一百多頁,后方支持的很少。我們前方每個人都寫了十多篇。主編還給我們發了感謝短信。我也挺感動的。
李:你們大家對這本雜志的評價怎麼樣?
王﹔我們看到的比較晚。回到北京后才看到自己的雜志。5月12日發生地震時,我們上一期雜志已經出了,所以那期我們一點都沒有做。但我們寧可晚一點,也要做自己的東西。我們第一期沒有提供理性思考,但我們解答了很多對地震的疑問,這是中央電視台不能夠給的。我們呈現了人的力量,人的精神,這還是發揮了三聯一貫的長處——比較重視人的故事。那期雜志還是形成了一個氣場。
李:我覺得大家習慣對三聯有所期待,對這樣的大事,這個主流的雜志會有什麼樣的反應。那一期出來,整本雜志文章還是比較平衡的。
王﹔比如我的一個同事就自己坐了好多天車去汶川,最后爬到一個小山頭坐軍用飛機出來,他差點掉下了山坡。 我們這一次不僅僅是對三聯負責,也是對自己的。
李:第二期怎樣策劃的?
王﹔我們沒有回來,第二期的人就來了, 當時想做災區的孩子。 到了星期五的時候,變成想做“家”的主題,主編的意圖比較強烈,我們此時所需要的不是理性思考,不是要做反思。我們的副主編說“哪有那麼多智叟,你救援的是兄弟姐妹,不是救援對象。”這話挺讓人感動的。
李:我覺得第二期還不錯,就是記者第一人稱的用法有點多,這是有意的嗎?
王﹔一開始就是這種范式,主編鼓勵我們把自己寫進去。
李:第三第四期就是策劃了?
王﹔對,策劃就比較明顯,比如第三期做的就是救援,採訪了一個救援專家,他說的還不錯。他是農業部的一個專家,談論的很多觀點,如不應該大規模的讓部隊進去,他們沒有裝備,隻能消耗當地物資,應該發動當地活著的青壯年展開救援。第四期的標題好像我還貢獻了點力量,叫“吾國吾民”,還是延續第三期。我們的主編因為此地震有些改變的,他自己也說,自己是喜歡競爭,強者勝的觀點,包括三聯,也是在強調這個氛圍,但是這次,大家普遍就是把那些受難者作為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樣的感覺。
李:那你是怎麼調整的,需要看心理醫生嗎?
王﹔回北京調整的,在四川時覺得肯定要心理醫生,當時都不能說話,不能接電話。回北京后參加一個叫心理訪談的節目,裡面有一個心理專家, 他告訴我當時的反應都是正常的。回來后最好不停的對人說,去講述,因為大家普遍的做法是回避,但是他發現這次災難太大了,不是輕易能夠忘記的,所以需要講出來。
李:你在災區呆了幾天,幾號回來的?
王﹔十三號去,二十二號回來。
李:你的那些心理問題對你的人生觀,修為之類的有沒有改變?
王﹔我在那裡的時候會覺得改變非常大,會覺得所有的爭名逐利都不重要了,因為這些都可能在一瞬間消失。回來后覺得倒是沒有那麼大,因為所謂的悲劇,所謂的英雄,最終回來都回歸到瑣碎。我覺得這種瑣碎沒有什麼不好,庸俗有時能夠消解掉悲劇。
李:你對你的報道滿意嗎,有沒有不滿意的?
王﹔略有遺憾的是,我會強調尸體的味道。並不是臭味,而我覺得是有點火焰的那種焦味,有口紅的味道,甚至有點香。我文章裡寫了,可能主編覺得這句話有問題,就刪去了。
我看了李海鵬的文章,比如尸體的顏色,我的文章裡也有,但是都被刪掉了。可能面對死亡我們不能有太多具體的描述。我覺得我隻能寫到這樣了。我知道會有更好的文章,我覺得我不會寫的更好了。
李:你覺得這次媒體環境有突破嗎
王﹔我覺得沒有大的突破,採訪條件仍然很不好。比如說,警察會攔你,去醫院要介紹信,種種的限制仍然存在。 相對於一般的小災難還是有些放寬,但這放寬不是有意的。我一開始要去北川,就是因為開始管的比較鬆,后來就不行了。一開始是比較開放,但這個開放不是主觀的。
李:你這次有沒有接觸過外國媒體,對他們的工作怎麼看?
王﹔我接觸的主要是國外電視台,我覺得他們永遠都沖在最前面,我算是去的比較早的,看見往裡去的都是外國媒體,國內的較少。
李:你這次有沒有什麼總結的經驗,下次採訪災難應該怎樣做,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王:我沒有任何技術上的進步,所以下次可以在這方面注意一下。 我感覺:第一,永遠要在風暴的最中心。 不是說花哨的解讀方式就可以的。每個人都要去經歷。 比如,中央台有很多優勢,包括直升機、沖鋒舟等,但是這些資源多的媒體並不比別的要好多少。 他們最多在時間上有一定的提前,但在人的力量,思考的力量上沒有給人很大的空間,還是靠每個人平時的積累。
李:你可能收獲了一些心理積累吧
王:可能會,我的同事有做過東南亞海嘯的,他們的反應,就比我要好一些,面對死亡的態度會比我更加達觀一些。
方玄昌:人性沖擊下沒有職業之分
方玄昌:中國新聞周刊科技主任,多年來從事科學報道。曾供職於《東方早報》等媒體。199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環境科學系。2002年-2008年工作於中國新聞周刊。
方=方玄昌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麼時候去前線的?
方:14號晚上8點多的飛機,飛到重慶,從重慶打車去成都。
李:你去的時候是否有什麼具體的任務?
方:剛去的時候沒有,那個時候是盲人摸象。出發之前我們已經做了一期解釋性報道的封面。我們想的是前線發回的報道一定要把感人的東西報道出來,要讓讀者熱淚盈眶,這一點是共識。15號早上抵達成都,大家按地域分工,每個人去了不同的地方。這裡就有經驗問題,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因為我們不僅要將大家分散,還要能讓大家收回來。。
我被分配進北川,我到了20分鐘就明白這次地震的嚴重性,歷史上少有這樣嚴重的地震。我當時的想法還很理性,我看到尸體,我還想應該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北川,把北川的問題做深入。有關北川的受災具體情況、北川的救援、北川的學校。以點帶面把整個災區的情況描繪出來,地震中人性的光輝都可以體現出來,這樣文章也可以有梯次感。進入北川20分鐘以后自然而然想到了一個策劃方案,想到了這個策劃方案之后確實沒有跟后方溝通,一個原因是電話不通暢,還有一個原因是知道后方不可能理解。因為在后方他們無法了解前方記者的感受。
李:你出發的時候做了什麼准備嗎?
方:我因為身體比較好,出發的時侯隻帶了水,后來還是《南方周末》的記者借給了我一個口罩,抵擋尸體腐臭的味道。穿了一雙比較好的鞋,沖鋒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李:你進北川的時候路好走嗎?
方:我們繞道江油進去,進去的路非常糟糕,而且非常危險。
李:這次你一共去了幾個災區?
方:安縣、綿陽、北川。
李:大概寫了多少文章?
方:我前后一共寫了7篇,但是現在發表出來的隻有4篇。
李:一共呆了多少天?
方:15天。
李:哪一天最難熬?
方:15號那一天。那是第一天到,看到那樣的景象已經真的被震撼了,有一種煉獄一樣的考驗。后來寫文章的時候一直在哭,因為需要回味細節,這對我來說是很殘酷的一件事。
李:你認為救人是比報道更重要的事情?
方:這是肯定的。
李:我在採訪其他記者的時候有人表示他們的天職就是報道,他們與救人無關。
方:也有可能是這樣的,因為不懂救援的人可能會添亂,但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大。我一直在做科學報道,有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關於地震發生、預防這樣的事情我都比較清楚。而他們不十分了解的話肯定就會斷定說救人不是他們分內的事情,他們隻應該報道。
在進入北川之前,我可能也面臨著職業和人性的選擇,但是在進入北川那一剎那,對於我來講就沒有什麼選擇可言了。我到了北川之后對北川的救援感到絕望,那麼大的山體崩塌,埋在下面的人們根本沒有什麼生還的希望。那個時間就想,隻要能救出一個人,做什麼都願意,在那種人性的襯托下,真的沒有任何職業可言。
李:雖然對救援感到絕望,在北川的時候你還幫助了一些人,對嗎?
方:幫助是正常的,我看到一些人逃難出來了,然后他們需要幫助,我們提供幫助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個也跟職業不發生任何沖突。
李:但這次的報道確實反映了一種人性和職業的沖突,我看到你的文章《穿越死亡谷六小時》也是這麼說的,你也想用第一人稱,想用參與者的角度,來紀錄這個過程。
方:的確是這樣,我寫文章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態呢?中國絕大多數人是不能像我一樣親歷前線的,並且,到前線和看電視,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夠帶這些不能去前線的人們走這段路。我的文章原來的標題叫《與君同行-北川六小時》,如果讀者能產生這種感覺,我會很欣慰。
跟央視的報道不一樣的是,我把很多血腥的場面寫出來了,這種場面我認為是有必要的,盡管上版的時候刪了很多。它和常規新聞也不一樣,但在這場災難下應該寫,因為這個也是喚醒人性的必然的場景之一。包括我自己怎樣被感動的經歷,這時我自己也成為文章裡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所以我要採用第一人稱的寫法。我真正要做的就是真實報道,喚起大家對於人性的一種認識,讓所有沒去過前線的人和我一起親歷前線。包括很多在前線遇到的事情,我都希望用我的筆完整記錄下來,我在北川縣城6個多小時的經歷,濃縮成十幾分鐘,讀者在讀我的文章的十幾分鐘當中如同親歷前線。經過我們后方編輯的反饋,我的文章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人在看我的文章的時候都感動得流淚了。
李:你會不會因為看到自己無力幫助他們而感到沮喪?
方:不止是沮喪,還有一種愧疚。我非常理解士兵和救護人員,他們花幾十個小時救出一個人來,但是那個人在短短的十分鐘內就死去的時候,他們非常悲傷。因為救出人來就仿佛你給了一個人生命或者一次再生,當看到他們還是死去的時候會非常悲傷。
有一個醫生叫盛?蓮老師,是第一批來到北川參與醫療救助的醫生中的一個,我是5月19日默哀三分鐘之后採訪她的。面對面採訪的時候,兩個人一直在流淚,因為她給我講了大量聽不下去的故事,讓我感動。
當時盛老師給我講了一個故事。13號早上,兩個士兵抱著一個小孩交給他,交給他的時候小孩還是溫暖的,但是已經在路上死掉了。這兩個士兵抱著小孩跑了一個多小時才來到醫生面前,當聽到醫生說小孩已經死了的時候,士兵怎麼也不相信,當場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讓醫生一定要救活這個小孩。他們花了十幾個小時才救出這個孩子,孩子媽媽還在后面瘋狂地往這邊跑。當時下著傾盆大雨,雨水把小孩的臉洗得干干淨淨,她看到了一張非常清秀的面孔,以及失血后慘白的嘴唇。
盡管孩子已死,盛老師還是不停給這個小孩做人工呼吸——她隻能這麼做,一直做到小孩媽媽從后面跑過來。她把小孩交給了士兵,一個人痛苦著跑掉了——她無以面對孩子的媽媽。她跟我說,這一輩子也無法忘記那個孩子的臉。
醫生當時的那種愧疚我很能體會,沒有去過災區的人無法想象那種心理的煎熬。
李:你在文章裡面提到過最后已經不忍心去採訪了,從傳統意義來說,你並沒有履行一個記者去多問、多了解的職責了。這裡面有沒有矛盾之處?
方:也沒有矛盾,這跟我的職業沒有關系,這是一種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為正常的人,在那個時候承受不了,跟我的職業依然沒有關系。作為普通的目擊者,我無法控制自己,要我繼續去冷靜地進行採訪,非常困難。在人性的光輝被激發出來的時候,人性的軟弱也被激發出來了,這個是自然的。我非常同意我一個朋友的說法,跟那些還能夠冷靜報道的記者相比,我們不夠偉大,不夠堅強。我覺得他是對的,雖然我不認為自己那麼不堅強。
我認為有兩個因素使那些記者還能冷靜地報道而我不能。第一個因素:我當時進城的時候,觀察非常細致。這是我的職業需要,在一隊記者當中,我走在最后面,我一直都在觀察細節,而一些記者就忽略掉這些細節了。第二點是運氣的問題,有一些記者就特別“幸運”地沒有被派到最悲慘的地方,或者他們沒有在第一時間看到。但我是在最殘酷的一瞬間看到了最殘酷的一幕,馬上聽到了最殘酷的復述,再和現場的場景結合起來,這個沖擊是最大的。到現在經過無數次的回味后,我已經可以比較坦然地面對比我描寫的更血腥的場景,但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之下,我無法做到冷靜,承受不了。所以反應的程度,跟個人是否堅強有一定的關系,但關系不是那麼大。
李:你以前看到過這樣數量眾多、慘不忍睹的尸體嗎?這樣的經歷是否也使得你不冷靜了呢?
方:跟這個關系也不大,我之前雖然沒有看到過這樣被扭曲了的尸體,也看過太平間裡面的一些尸體。后來我在成都做心理干預,和心理學家聊天的時候,他們很快地猜到了我的非理智反應、我的哀傷,很可能與我以前的經歷有關?.而我這次是第一次看到非正常死亡。
和我一起採訪的《南方周末》的記者陳江經歷過開縣井噴、包頭空難等。他說第一眼望過去尸體最多的不是這次,而是開縣井噴。但他也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尸體四分五裂的慘狀。我最大的感受是,生命的尊嚴,以及人作為一個特殊物種,一貫擁有的優越感都被災難擊得粉碎了。
我當初被尸體的那種扭曲、畸形震撼,但這只是震撼,沒有讓我哀傷、傷痛到不能自已。但是當我后來採訪遇難者親屬,與他們聊天並且將他們所講述的事情與前面看到的尸體聯系起來的時候,感到了一種人性的煎熬。在這種情況下,我才真正地不能自已。
李:你是什麼時候想去看心理醫生的?
方:我沒有去看心理醫生,我是去採訪心理醫生,然后心理醫生就給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那個時候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無數次的回味之后我覺得我已經很正常了,去的時候心理醫生大致給我做了一個測試,也做了一些開導,認為我還是比較正常的。
李:你平時是怎麼給自己做心理調試的呢?
方:我做心理調試的方法非常簡單,我讓自己去回味每一個細節。寫第一篇文章開始,我就已經習慣了這種回味。
李:這不是很殘酷嗎?
方:非常殘酷。我每天都要跟別人說這些事情,自己也一遍一遍地哭,到后來才會慢慢地好起來。這種方法對於別人來說可能不是十分可取,但是對於我來說卻是可取的。
李:后來有余震的時候,你感到過害怕嗎?
方:不害怕,因為我相信科學。我知道余震殺傷力不太可能很大,所以19號左右發布有6級以上余震的消息,大家都跑到街上去的時候我沒有跑出樓,預報發生在48小時之內的余震是非常不可靠的。我相信現代的建筑,抵抗余震還是沒有問題的。余震不可能有這樣的殺傷力。
李:看到很多人生無常的境況之后會讓你開始相信命運嗎?
方:不會。它使我感覺人是很脆弱的,可以在瞬間就像一隻螞蟻一樣失去了生命。螞蟻可以運氣不好被人踩死,人也可能運氣不好被房間那麼大的石頭砸死。
李:那你的人生觀、自然觀會發生變化嗎?
方:我當初到了北川縣城的時候,我曾經下了這樣的結論:這麼大的災難,會把壞人變成好人。但是這個結論當天晚上就被打破了,因為我聽說有人去偷東西。這些人可能為生活所迫。對我本人呢,我作為一個記者,對自己的人生觀更堅定了。回來之后我和同事說,在這麼大的災難后,我以后不會因為顧及別人的想法而改變自己,我會更加直率。我一直非常直率,但以后我會更直率。
李:你怎麼權衡工作和休息?
方:那些天就沒什麼休息。睡得很少。15天裡真正也隻吃了13頓飯。在那種狀況下,一個健康的人還是可以堅持的。
李:這次採訪家人支持你嗎?
方:家人開始的時候都不知道,但是后來知道以后還是非常支持。我二姐特別希望自己的兒子到北川支教,我三姐、四姐還要領養北川的孤兒,而我要領養的話一定要領養殘疾兒童,因為他們更需要大家的幫助。
李:這次你們第一時間到前線拼殺,有沒有得到報社的支持呢?
方:出發的時候一人給了一萬塊錢,我回來的時候還剩下一千塊錢。我出差的時候個人花費很少,但是車費很貴。對於生命安全方面的保障,我的要求也比較簡單,除了安全帽之外我也不需要任何的特殊保護。
李:前后方的協調怎麼完成的?
方:后方一般會以常規新聞來判斷前方的情況和想法。而這次新聞太不常規了,以至於在我文章中都加上“前方記者在震驚之余,也在職業與人性的選擇上掙扎”,其實對於我來講沒什麼可掙扎的,沒什麼可說,救人是首位的。
李:常規事情和特殊事情的問題,能否再解釋一下?
方:他們沒有區分開來,他們仍然按常規事情來做,如此巨大的災難他們沒有深切地體會到,這也讓他們對新聞的價值產生一些懷疑。比方說,他們希望還用理性的筆觸來描述、來報道,但是這個是不對的,因為新聞要求理性也要求客觀,而那個時候理性就已經不客觀了,理性不總意味著客觀。在那個特殊時候,理性可能就意味著一種不客觀,因為在那個時候你不能保持理性就是一種客觀反應。
比如說我后來申請到北川再多呆一些時間,后方要求我回去參與后一期策劃,要做疫情方面的新聞,那個時候疫情已經出現了。二次災難是值得做,但我認為那還不是時候,我那時候應該把感性的、人性的東西傳達給大家,而不是理性,我們前后方發生的分歧也使得我們那期的報道做得不太好。我在那時候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在北川的時候,后方打電話給我,我哭著跟他們說,採訪無法繼續進行。他們還是用了這樣的口吻:“你是一名記者,你要做到理智。”
以前跟我共事的人都比較了解我,知道我不能保持理智了就肯定是遇到了很特別的狀況,但是他們不能理解。如果再發生同樣的事情,我會直接告訴他們“聽前線的,你們后方什麼都不知道。”前后方溝通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想以后如果出現類似的事情,這樣的問題還會發生的。
李:這個是不是源於結構性的問題?
方:是的,是結構性的問題,需要非常強勢的編輯在前方做主持工作。他在接觸了第一線之后,冷靜地來思考。印尼海嘯報道的時候,我們前方的編輯就比較強勢。
李:你跟那邊的政府機構打交道嗎?有什麼經驗嗎?
方:后來的日子我都是跟政府打交道的。我理了一個光頭,這個光頭起到一些作用。后幾天去採訪的時候,一大半記者都在門外等,我因為趕時間直接沖到新聞發言人那邊問問題,他們馬上接受採訪。他們看到了我的職業程度。他們說是我的職業感、專業性讓他們願意接受我的採訪。他們的人后來跟我說,在我採訪之前,他們已經接受了四五十個記者的採訪,沒有一個人像我問的這麼具體,問一些非常專業的問題。
后來他們甚至把他們抗震救災時候第一時間草創的指揮圖拿給我看,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了。為了保護這樣的珍貴資料,我后來還讓一個攝影記者專門去拍照。
李:理光頭的原因是什麼?
方:兩個原因。首先是如果我受傷了,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裡面清洗傷口。第二個原因是我到北川的第二天理了光頭也是為了一種洗禮。那個地方給我帶來的沖擊太大了,這裡面有一種儀式感,要為這些死去的人默哀。總之是在一種非常復雜的心態下理光頭的,自己一時也說不清楚。
李:你跟志願者打交道嗎?
方:我回來的路上都在跟志願者打交道,跟他們聊得比較多。
李:你跟災民溝通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驗,會冒犯他們嗎?
方:不會。我剛去北川採訪的時候多是他們主動跟我說的,他們知道我是從北京過來的記者。我從他們臉上已經看不到哀傷了,但是他們心裡會有一些憤怒,對政府的一些行為他們不理解。他們當時埋怨北川政府沒有把他們移民出去。很早的時候北川政府想把他們移民但是最終沒有成功。他們就埋怨如果當時給他們移民的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慘狀了。
但是事實上,你知道中國人對家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何況北川那麼美,即使當時政府堅持給他們移民的話也未必能夠成功。那裡一直沒有過大災難,他們未必就能夠理解政府的做法。 李:會不會有過於哀痛不願意交談的災民?
方:按照心理學家的分析來說,表現得非常哀痛的人其實並不是最痛苦的,他們把這些哀傷的感情都表現出來了。最可怕的就是不表示哀痛的那些人,他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因為他們已經哀痛過頭了,已經不可能表示出來了。后來網絡上有一個評論,就說他們在新聞上不但看到了哭泣的畫面,還看到了不哭泣、不哀傷的表情,他們才發現那些更讓他們震撼。
李:你對這次自己的報道還滿意嗎?
方:不滿意。自己想做的東西還沒有來得及去做。對自己的報道不滿意是一個方面,但是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原因,我們感覺自己沒有給災民帶來實質上的幫助。
李:但你引起了關注,讓更多人關注到他們?
方:在我們的報道中,我們還看不到任何直接或者實際的幫助。
李:你覺得這次事件對於中國新聞史的突破,意義是什麼?
方:在中國新聞史上,這是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災難報道。在報道對於當事者實際幫助的方面,它沒有發揮到太大的作用,不如SARS。SARS的報道可以直接對老百姓形成指導,而這次不能。sars,是科學解釋可以解決問題的,但是地震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問題,有很多科學上尚未解決的問題。但老百姓還難以接受這一點。
這次災難遠遠超過了SARS,而在對災難本身的幫助來說,這次報道不如SARS。唐山大地震不一樣,那個時候媒體並沒有真正興起。
李:在新聞操作方面,這次事件的意義是什麼?
方:這個事件最好的一面是喚起了中國人沉寂了五六十年的人性中最光輝的一面﹔而科學報道反而沒有做好。地震是個科學話題,但是我認為做得一點都不好,這次大多數科學報道、解釋性報道都失敗了。科學性報道反而被偽科學報道所掩蓋,讓老百姓無所適從。
我在採訪的時候深有感觸。有一個採訪對象說,災區很多人是莫名的憤怒,憤怒的原因是為什麼中國政府沒有預測呢?或者是中國有這麼多國寶級的人物早就預測出地震的到來,為什麼國家地震局沒有採納?這就和我們的科學性報道不夠有關,以至於到了今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以為張衡在兩千年前就已經發明了地震儀,可以預測地震何時到來,而事實上,科學技術發展到了今天還沒有能夠預測地震的到來。這方面的最基本的解釋性工作我們的媒體沒有給大家解釋清楚,我同樣也沒有很好地做這個工作,我也趕到前線去了。
李:這次媒體在科學報道方面你認為表現怎樣?
方:在前期報道裡面,已經有一些媒體嚴重走偏了,他們報導“偽科學”,用特別的手段對事情進行解釋。我因為是科技記者,我更看重解釋性報導,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報導不如SARS。這次的解釋性報導是失敗,中國的科學解釋報道還停留在沒有怎麼發展的水平。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