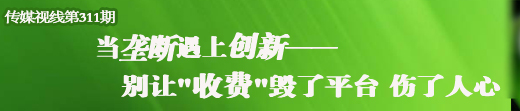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點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很多媒體同行已經在前線採訪或在奔赴前線的路上,人民網傳媒頻道把李梓新所著《災難如何報道》一書中的“汶川地震媒體操作實錄”予以刊發,希望能對在前線採訪的同行提供一些參考。該書2009年1月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裡,你可以讀到來自12家中外媒體的主編、主任和記者們對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憶和感想。
Lucy Hornby:我始終覺得有非常大的責任感
Lucy Hornby: 路透社駐北京女記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后到武漢大學修讀中文。歷任路透社駐上海、北京記者。
Hornby=Lucy Hornby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麼時候趕到現場的?
Hornby: 我是第六天去的。我是地震發生的下一個星期天去的。5月18日走的。
李:你正好趕上了哀悼,你在哪裡進行了哀悼?
Hornby: 平通。我們到的時候路隻到平通,想再往往裡面車就走不了。如果你換成摩托車還可以過去,但是最大的問題食物過不去。那邊有人在挨餓。
李:平武報道的受災的人還不多,據您來看是這樣的嗎?
Hornby: 大部分的記者去了都江堰、映秀、北川等,沒有多少記者去那裡。
李:你為什麼選擇去平通呢?
Hornby: 我去平通也沒有特意設計,因為我們在北川、都江堰都有記者了,我想不如我去一些稍微遠一點的地方,看看那邊的情況。因為我們聽說我不少災民從北川跑出來,但我們估計可能有另外一批人從東面逃出來,所以我們的目的是找離開的災民,但是沒有遇見他們,越走越遠之后走到了平通。碰到了一些滯留在那裡的災民,我也就留在那裡
李:你去的時候有沒有被分配任務?
Hornby: 沒有。我們就是說你去吧,看到什麼報道什麼。
李:你們一共派了多少人?
Hornby: 第一個星期十四個,包括文字和攝影記者。第二個星期大概十個,第三個星期可能三四個,包括攝像師、攝影師等。
李:所以你們的反應上是很快的,地震第二天就派記者過去是嗎?
Hornby: 對,當天就已經派記者了,只是成都進不去,隻能到重慶后開車過來。然后第二天就進去了。
李:說到你在平通遇上的哀悼,你當時什麼感覺?
Hornby: 平通哀悼日的前一天趕上李克強去看望災民,所以平通弄得特別漂亮,帳篷都弄得好。但是我覺得一方面是一個大的工作,他們也盡力了。但同時我也沒有想到那麼多人還是挨餓。可能因為我自己沒有想得那麼全面,我到那邊才發現原來災民獲得的補給是不夠的,能提供最基本的,但他們也許一天才能吃一頓飯,他們仍在挨餓。因為路是不通的,卡車進不去,能運進去的東西也很有限。通路是需要很大的工程的,我們要走的時候路本來已經通了,但是由於余震又斷了,所以通路問題還是很大的工程。李:那你是怎麼進去的?
Hornby: 我們包了一個車。
李:平通的損壞嚴重嗎?
Hornby:很嚴重,大概隻剩四個樓站著。
李:你到了平通之后第一印象是什麼?
Hornby: 非常悲哀。平通也是死了好多學生。尤其是小地方的人,他們不僅為自己難過,還特別為別人難過,看到周邊的好多學生也都死了,他們很多人用手救了很多人,但是救出來的時候那些人都死了,因為路還沒有通。所以他們感到很無助。
李:他們會不會覺得自己被忽略了,因為對他們的報道不多。
Hornby: 我覺得因為李克強副總理來了,他們還覺得有一點驕傲的,因為他們能把平通弄得這麼漂亮。但是周圍的村民還是感覺被忽視的。尤其對於周圍一些更偏僻、路又不通的地方,他們得到的幫助更加有限,飢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平通人他們對周圍的縣也非常擔心。平通人很願意跟我講話,因為他們希望讓我報道他們。
李:這次最開始大家都在說汶川,后來有人說北川其實更嚴重,於是大家才知道北川。其實這次還有很多地方都沒有人去報道,比如甘肅。
Hornby: 確實是這樣的,不過也很容易理解。因為一到成都,人們總是會去最容易去的地方,有開車兩個小時能到的地方,我們為什麼要開車去五個小時才能到的地方報道?但是當地人就會覺得他們也有問題,為什麼沒有人去報道。而且是同樣嚴重的情況。
李:這個實際是我們在講的就做新聞一塊來說,在同樣這麼大的災區裡面,怎麼樣找自己的新聞角度,一個與別人不同的角度?
Hornby: 對,比如我做了平通的一個處理死者的故事。可能對於北川大家還在談怎樣挖出人,但是我在平通碰到挖出來的所有人都死了,但是對於平通處理死者的我可以把它做成一個例子,以此來探討他們是怎麼做的,有什麼優點、什麼缺點。
李:你之前有沒有進行過災難的報道?
Hornby:我從來沒有,但是我經歷過。麗江地震的時候我在麗江。雖然麗江沒有那麼嚴重,七級,但是還是有很多樓倒塌了。所以雖然我從來沒有報道過這樣的故事,但是我對災民非常理解。我經歷麗江之后,一年裡面,如果我在樓裡,旁邊經過一輛大卡車使路面發抖,我都會覺得是地震,非常敏感、非常害怕。採訪時候我跟災民說你們是不是心理非常不平靜,我們心理都非常清楚。地震有一個最可怕,就是聲音,像一個大動物,先聽到聲音才感到波動。我跟人家聊一聊,他們馬上知道,我在麗江聽過那種聲音,但這個聲音好像沒人報道過。好像地球就是一個活的動物。
地震之后你沒有安全感。一般情況下,比如說小偷來我的房子,我可能幾個月以后在我的房子裡沒有安全感,但是我在辦公室會有安全感。但是地震使得你在哪兒都找不到安全感。所以我覺得在那方面我對災民有一些了解,但是我也畢竟沒經歷過那樣嚴重的地震,我的家人沒有在地震中受到任何傷害,我不可能完全體會災民的痛苦,但是從某種程度上我可以明白。作為一個大的地震,我可以了解。
李:你看到這些嚴重的傷情,你感受如何?
Hornby: 因為我是第二周到的,所以傷亡的人看的不多。但是這種地震的那種破壞性當然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周圍都是傷亡的人。但是最難的是採訪那些父母,感覺就好像沒什麼話能和他們說。你也不想哭,但是你也不能不哭。我覺得這個印象我自己也不能很好地形容。
李:你哭了嗎?
Hornby:對對,但是這個很影響我繼續採訪,這個可能因為我經驗不夠豐富。
李:我很理解你,我是后來才去的,但是看到那些父母、孩子也還是特別難過。你採訪那些父母的時候,他們都願意說話嗎?
Hornby: 還可以,沒有什麼特別的。好像學生的舅舅這樣比較遠的親戚更願意說話。然后就是一些負責搶救的人。他們也很難過,但是父母更難過。
李:他們是不是更願意回憶他們如何逃出來的?
Hornby:是,有的人。
李:你認為這次採訪對你心理造成什麼壓力或者影響嗎?
Hornby: 因為關系越遠的人越容易說話,因為對我來說是這樣的,所以這點可能是我不夠專業,因為本來應該採訪那些離受難者關系最近的,但是他們最難。然后因為我第二個星期去的,他們開始有點恢復了,能吃飯了,所以他們更可以專注於孩子的問題。
李:你在那裡待了多少天?
Hornby:六天。
李:去了什麼地方呢?
Hornby: 去了都江堰、向峨、平通、綿陽、青川、江油這些東北邊的地方。我認為我跑得遠一點可以避免和同事重復。
李:你們在前線的時候有沒有互相分配?
Hornby:我們基本上沒有,都是互相打電話看其他人在哪裡,然后去別人沒有去的地方。如果有重復,大家就協調一下。
李:待在那個地方有沒有給你造成心理壓力,讓你心理上非常難過?
Hornby:我覺得始終有非常大的責任感,因為你去每一個地方,后來看到報紙還在報映秀或者北川,你覺得我有責任感把看到的這些東西都報道出來給大家看。因為問題是,你在裡面的情況並不獨特,可惜的是死的人太多了,沒有房子的人也太多了。但是這個問題是普遍的問題,而你每一篇文章都要找一個不同的角度,雖然我也覺得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報,但我每次找一些不同的態度,所以雖然報的故事差不多,但每次報上一個小城市的名字,也是給他們宣傳一下。但是實際上每一個鎮的情況差不多。
李:你出發的時候有沒有帶什麼物品?
Hornby:有人跟我說你可以帶一些茶,因為裡面的人沒有茶,都隻有礦泉水。但是我們帶的不多,因為軍隊把最基本的做得非常好,而且志願者也做了很多。
李:你自己做了什麼准備來進行保護嗎?
Hornby:做重要的就是筆記本電腦、電話。但是我不喜歡帶口罩,非常不喜歡,又熱又不舒服,沒有必要。因為跟人說話有距離感。我隻在一個墓地時戴了,但一出來我就甩掉了。我還帶了一個帽子,坐摩托車的時候用。
李:路透社為什麼會派你去前線,女性的身份有沒有考慮在內?
Hornby:對於所有的記者來說去前線都是他們期待的事情。他們說沒有考慮性別的問題。
李:那他們為什麼會派你去呢?
Hornby: 路透社要求所有的人都學一個課程叫hostile environmental course(敵對環境課程),所以我們這個辦公室裡所有學過這個課程的人都去了。有一些人非常嫉妒我們,因為他們沒有通過這個課程。這個課程是路透社請人來上的,比較簡單的一些自救的方法等,最早設計這個課程是為了那些去報道戰爭的人。比如你是戰地記者,要去伊拉克,你就必須之前受這樣的培訓。后來他們發現南亞海嘯,這個不是一個戰爭,人們不能提前准備,但也同樣非常危險,可以造成人員傷亡。所以后來他們覺得應該把這個擴展,讓所有願意接受類似任務的人都接受培訓。所以隻要通過這個課程的人都去了,但是不是同時去的,剛開始派了四個人。
李:這個項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Hornby: 最早是隻對去危險地方的記者,但是后來因為有了海嘯之類的事件才改變的,具體的時間我不能確定。記者都很願意參加這個課程。通過這個課程之后一旦有什麼危急情況你都可以去報道,而且也是帶薪脫產學習。
李:你花了多長時間通過這個課程的?
Hornby: 三四天。一年一兩次,他們請國外公司專門來做。
李:你到了現場之后會不會有幫助別人的想法,是否覺得幫助別人比報道更重要?
Hornby: 因為我到了已經是第二個星期了,那時候最有幫助的事情就是如實報道。如果是第一周去的話可能還有挖人的可能。到了第二星期,能挖出去的都挖出去了。可能第一個星期去的記者會不一樣,第二周去最多也就是帶一些吃的。
李:你去採訪的時候需要什麼証件嗎?
Hornby: 他們要我們到成都的外國事務辦公室辦了一個記者証。需要自己去辦,但沒其他麻煩。
李:辦証件有任何困難嗎?
Hornby: 沒有任何困難,但是要自己去辦。
李:后來在採訪的過程中遇到過任何阻攔嗎?比如有一些地方不希望你去報道?
Hornby: 沒有什麼阻攔。隻有后來去過兩個地方,軍隊的人不是很高興,不太希望我們去報道,但是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去阻攔我們,所以我們基本上沒有遇到任何阻礙。
李:整體來講,你對這次地震中國的公開度評價如何?
Hornby: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沒有碰到任何問題,特別是當地的官員非常歡迎我們,跟西藏的完全不能比較。這次當地的人,特別是當地官員非常歡迎我們,這是與以往相比非常不同的。以前我們經常要解釋很久才能得到採訪機會。
李:你是否採訪了當地的高級官員?
Hornby: 沒有,我只是去參加了一個四川省副省長的新聞發布會,但是是比較規范的。
李:你是否得到了志願者或者軍隊的幫助?
Hornby: 只是碰到了他們,但是並沒有什麼需要他們幫助的地方,有一個志願者非常友好,看我們沒有蔬菜給了我一根黃瓜。
李:這次採訪路透社對你們有沒有什麼採訪的要求,給你們的採訪一些定位上的指導?
Hornby: 沒有。因為新聞每天都在變化。
李:這次地震剛好是在國際上對西藏問題報道反應比較強烈的背景下發生的,路透社的報道會不會把這兩個事情聯系起來對比?
Hornby:我覺得News is News,新聞每個是不同的。只是區別在於西藏政府堵住不讓我們進去,而這次當地政府很歡迎我們,我們報道用的手法和倫理都是一樣的,改變不在我們的身上。
李:你覺得這次報道受到的反饋如何?
Hornby: 我認為這次報道反饋還是非常多的,因為地震這個事件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大家都有家人,都能夠想象如果哪一天家人全部去世的話會是多大的悲傷。所以大家對這個事件都非常關注,反饋也很多。比如我的家人,他們就每天都看報道,雖然對國際新聞平時都不關注。他們給我發信說看到報道以后非常感動,因為他們特別同情災民。而且我也有一些朋友都說他們第一次看新聞都哭了。
李:你們在報道的時候是怎樣努力與其他國際媒體不同的呢?你們的報道風格本身設定有什麼不同呢?
Hornby: 當然我認為路透是最好的,最有代表性。但大部分在中國的記者都非常專業,所以我覺得大家在災區發回的報道都非常專業,報道非常好。
李:這次整個新聞環境,你認為對於中國整個的新聞發展有著怎樣的意義呢?
Hornby: 這次中國記者也報道得很好,但是不是一個突破我想要等到下一個危機再看看,不清楚。這次事件整個過程都向媒體開放,政府也做得非常好,但是是否這樣的形式會持續到下一個危機發生,我也不敢肯定。比如說鬆花江的污染事件之后,一些環境問題也報道得快了。或者SARS,我覺得SARS之后也能看到一些問題暴露得更快了。
李:經歷這次事件你覺得自己需要接受心理干預嗎?
Hornby:沒有,我有一隻小貓,和它很貼心,它就能幫助我了。老板說你們自己感覺如果需要幫助的話,要盡管說。北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FCC也組織了這方面的講座。
李:你在那邊碰見余震害怕嗎?睡得著嗎?
Hornby: 我不害怕,睡覺也沒問題。因為我也遇到過地震,所以我知道余震比地震小。一般來講,余震都不會造成特別的危險。
李:你會相信命運、宿命這樣的東西嗎?經歷過這種無常的事件之后。
Hornby: 因為每天都接觸比較科學的東西,所以我不是特別迷信。
李:你以前去過四川嗎?怎樣在一個陌生地方迅速打開局面?
Hornby: 有,以前去四川都是旅游。我都是碰到人就開始採訪。
李:你對自己的報道滿意嗎?有沒有什麼遺憾呢?
Hornby: 比較滿意,唯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在那邊的時間太少的,如果在那邊更長時間的話會有更好的東西報道出來。如果我可以決定的話,我還會多在那裡留一段時間,因為我比較希望能夠報道地震后續的事情,這樣報道的過程比較完整。這個也完全就是我之前所說的責任感的問題,作為一個記者總是有種責任感要把所看到的事實報道出來。但是公司由於希望給每個人去現場的機會所以就讓每個人隻去一周左右的時間,這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李:你覺得這次路透社的報道有沒有幫助世界范圍內的募捐呢?
Hornby: 我覺得有可能,因為國外的人都看國際報道,而且這次募捐的力度確實非常大。我不敢肯定是否大家是因為看到了路透的報道,可以肯定的是這次的報道總體上引起了人們很大的關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至於路透報道起到的效果我還不能肯定。
李:你在報道過程中跟中國的記者有什麼接觸嗎?
Hornby: 有一些接觸。
李:你對他們的印象如何呢?
Hornby: 我覺得他們非常好,這次在災區他們也非常專業,不把我們當外國媒體看,我們都是一樣的行業。
李:作為女性記者採訪會不會有些便利,又有體力等方面的困難?
Hornby: 我的體力比我認識的大部分的男的還好。但在採訪上,我不覺得有什麼便利。
李:如果下一次再有類似的災難報道,你將會怎麼做?
Hornby: 個人來講,如果下次再去類似的採訪,應該多想一些辦法,跟那些最困難的人交談,比如說孩子的父母。因為這次我主要考慮到跟那些非常近的親屬交談,肯定會跟著他們一起哭,然后哭了半天也沒有用,反而會影響採訪,所以我盡可能跟採訪離受難者關系遠一些的人。但是這些人往往不能代表最廣泛的人,所以我認為以后應該找一些辦法多問關系近的人,或者找一些他們更願意回答的問題。
李:你覺得這次發生的損害是否也有地震來臨之前科技報道太少的原因?
Hornby: 我覺得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很多中國人不懂地震,很多人在博客上質疑中國政府為什麼沒有預測?這個是大家不太懂。而且很多人對於余震也特別恐懼。
第二,如果你發現一些建筑比其他地方建筑的要求、標准高,外國人都知道肯定是由於這個地方更危險,比如美國舊金山和日本。但是中國的建筑在這些危險的預防上做得很不好,去現場看了簡陋校舍的人都知道中國在這些方面做得遠遠不夠。
第三,我還覺得中國很多學校和工廠會鎖門,因為怕有人會逃跑,這個在地震的時候就非常危險,因為地震發生的時候沒有人能夠跑出去。美國紐約在20世紀初就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大火,因為門鎖了,全廠的人都逃不出去,全都死了,以后美國就出了條例規定必須要有緊急出口,方便人員的逃離。但是中國盡管已經有了好幾次失火,但是還沒有出台相關的條例來保証人們的安全逃離。這些是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關心的,而且跟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問題。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