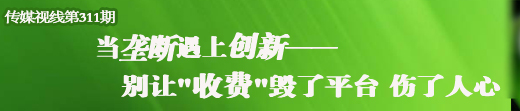4月20日8點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很多媒體同行已經在前線採訪或在奔赴前線的路上,人民網傳媒頻道把李梓新所著《災難如何報道》一書中的“汶川地震媒體操作實錄”予以刊發,希望能對在前線採訪的同行提供一些參考。該書2009年1月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裡,你可以讀到來自12家中外媒體的主編、主任和記者們對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憶和感想。
錢鋼:從唐山到汶川今昔談
錢鋼:浙江省杭州人,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及記者,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一書作者、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媒體計劃主任
錢=錢鋼
李=李梓新
李:您是地震報道方面的專家,從唐山大地震到今天的四川地震的,32年過去了,從新聞報道角度來說,可以作何比較?
錢:有很多西方記者、香港記者也都問我這個32年的問題。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進步很容易說的,如果離開國家大的變化,單獨說新聞,不容易看清楚。32年來,國家的形態、體制、外觀等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從這一點來說,今天應該有的變化是理所應當的,而第二點來說,我們嫌它變化得還不夠快。我曾說過,我無意贊揚。如果光拿今天和1976比,那麼變化是很大的。
李:回到1976年,媒體在地震發生之后的什麼時間能夠進入現場?
錢:媒體在地震發生之后什麼時候進去,我記不得。但也不應該有誤解的就是,當時的地震消息確實也是在第一時間內報道出去的,當時沒有網絡,不可能在發生的幾分鐘內就發出報道。當時所謂的第一時間就是“第二天報道”。7月28日發生的地震,7月29日《人民日報》報道了。
李:就是那條說唐山、豐南發生地震,軍民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抗震救災的新聞嗎?
錢:它主要的思想就是說黨中央慰問災區人民。當時的報道不是說唐山地震,而是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地震之后,黨中央對人民表示慰問,當時的重點在於地震后,黨中央對人民表示的慰問,然后第一次報的震級小,是7.5級,這裡面還號召大家以階級斗爭為綱,繼續深入批鄧。記者也是比較快就到的,主要就是新華社的記者,《人民日報》的記者。
李:解放軍報的記者呢?
錢:我當時不是解放軍報記者,我是上海文藝雜志《朝霞》編輯部的一個編輯,是解放軍,工農兵編輯。所以說我當年就是解放軍報記者的說法是誤傳。
李:所以您是以解放軍的身份,才能前去?
錢:我當時在編輯部工作。在第一時間就申請去了,但是上海虹橋機場不讓我走,原因不是因為阻攔記者,我當時的身份也不是記者,我要去參加救災,並且組稿,他們是考慮到安全的因素,說當時去那邊太危險。7月29號事情被報道以后,30號准備去前線,但是8月1日沒有走成,於是我就換乘火車,跟著上海醫療隊的防疫大隊進了唐山。等我進去以后,十天以后,唐山機場那裡已經有大量的記者,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記者都有。問題是那時媒體很少,主要是機關媒體,有沒有電視媒體我不知道。我認識的人是新華社記者,可是報道的主旋律都是抗震救災,包括還要繼續批鄧。
李:那個時候還是階級斗爭為綱,那您覺得這次四川地震報道中人性的東西體現得充分嗎?
錢:體現得比較充分。我們拿這次地震與我寫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比較。那是改革開放以后,1985、86年前后的社會氛圍下面,這種人性的回歸在那個時候其實已經出現了,不是等到今天才出現的。那時就已開始所謂弘揚人性的回歸。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可以做這個事情了。所以我在2006年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問我寫那本書會不會很難的時候這樣回答:“我在那個時候也這本書有困難,但是不會比今天更難。”
李:那這是不是說今天對比1980年代在人性表達上進步並不大?
錢:進步是有限的。通過你對比我1980年代寫的文章和今天的報道,從悲慘度上,並沒有很大的突破,在80年代已經可以做了。還有一個,80年代時候我已經可以開始寫反思了。當時我隻遇到一個矛盾,國家地震局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不要播放我的書的出版。把今天的報道,與80年代中期開始,跟80年代后期已經出現的,如1988年大興安嶺火災的報道——就是“紅、黑、綠”的系列報道——三個對比來看,紅黑綠的反思力度是今天都希望而沒有做到的。
李:雖然進步不大,但是新聞的發展道路是不是走了一個U型的路線?無可否認1990年代中國媒體報道是呈一個下滑的趨勢,而今天算是在一些新的條件下,比如說國力、公民意識覺醒等,重新往上走,其中有一個U型。
錢:這個很有意思,如果你拿今天和32年前比較,進步很大﹔如果拿今天和SARS比較,進步比較大﹔和1998年洪水的比較,也有比較大的進步。我說的進步主要是災難中悲慘的真相,災難中的人性。這一點在SARS的時候,首先是壓抑、隱瞞,到最后實在控制不住了才開始有一些慘狀的報道,但是后面大量的還是弘揚抗疫等方面的報道。1998年的洪水,剛開始的時候不許報道,到了簰州灣失事,九江決口,突然轉為可以報道,如果想報道災民苦難實況也會受到批評。但是這一次,百姓的哭聲、慘狀都是有的,總理身邊的哭聲也不加刪節,都出來了。這個是有進步的,這個方面與以前的幾次事件比,與洪水、與SARS都是有進步的。
但是我們如果回溯80年代中期我們做過的那些事情,我們曾經新聞改革有很大的突破,1986-88之間,隨著政治體制改革,還人民知情權,一系列的改革已經推動了新聞的很大變化,但是這個變化在1990年代又走了一個U字型。
李:希望這個U字型能繼續往上長,變成J型或者什麼樣的。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80年代,您已經作出了這麼富有人性的報道,但是不是今天的傳播手段確實已經比80年代好很多?
錢:這個是無疑的,首先是傳播速度的問題,我們有了手機、有了博客,這些技術手段都保証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傳播出去。
李:這次央視在報道過程中也傳播了很多正面的信息,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錢:我在過去的時候就說,你隻要稍微鬆鬆綁,中國傳媒人就會表現出非常優秀的品質。央視這次度過了一段禁令很少的時期,這個禁令很少的時期使得央視展示出了能量的煥發。包括央視,也包括新華社,這個裡面通常所說的黑白兩分的黨媒體、非主流媒體的界限變得模糊了。黨媒體裡面也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人,新華社和央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裡面都有很多優秀的人,他們在這次事件中表現都是很不錯的,讓人佩服。你給他們鬆綁就會使他們充分地發揮、展現實力。
李:今天的這種人性的釋放已經能夠成為媒體共識的基礎,這個基礎在八十年代是否也同樣地強烈,還是說在八十年代只是像您這樣先知先覺者的個人行為?
錢:八十年代的時候媒體並沒有做到這樣。媒體有這個理想、願望,但是還是一部分人在吃螃蟹,就我自己所在的解放軍報、或者是人民日報來說都沒有能夠達到。但是當時我們也採取了不同的方式進行嘗試,比如通過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在做,像其他人和我都是從另外一條路上來。作為一個觀念大家也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文革是摧殘人性的,而我們要做的是復蘇人性,這是我們達到的一個共識。
李:所以說,那時候還是精英時代的人性傳播,今天通過技術手段、比如電視等手段,多少可以把人性的思想傳遞給百姓。
錢:傳遞人性方面比80年代是強的多了,傳播的效果也包括傳播速度、傳播面、傳播寬度、廣度等等,都是強的多了。
李:那您會不會覺得物極必反,這裡面又包含著一種反效果呢?央視的報道鋪天蓋地搶佔了所有電視台的節目,尤其是哀悼日的三天,隻有少數幾個認為自己有一定制作能力的台還在播出自己制作的節目。您認為這種傳播效果如何?
錢:這個你看怎麼說。在壟斷的情況下,它用一種壟斷的、統一的方式,但是做的是人性,在內容上可以肯定。在方法上日后是有改進的空間,但是就效果而言、就目的而言總體還是人性的。如果放手讓大家去做這個節目的話,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這個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夠保証每一個台都能夠做出央視的水准,也可能做歪。但是我們希望的是一個多元的社會,能夠容納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
李:您能談一下網絡媒體在這次地震中發揮的作用嗎?
錢:發揮的作用非常大,我們很難想象沒有網絡媒體的話這次的報道怎麼進行。我自己在得知這次地震的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要把我在唐山地震中知道的一些救災的方式方法能夠服務前線,但是每天一篇的文章不是每天都可以在紙媒上面發表出來,卻可以在網絡上發布。財經網首先登了我的文章,然后是騰訊和天涯,他們為我設了博客,我其實是博盲,我不知道怎麼發表博客,但是有朋友在那邊一看到我的文字出來就幫我登上博客。有一些文字在《南方都市報》中出來了,但是有的文字沒有出來,但是所有在博客上都出來了。當《唐山大地震》2006年再版的時候沒有引起這樣大的反響,但是這次當博客上登出這本書的時候,引起了網民朋友們的強烈反響,很多的討論都圍繞書中記述的一些內容展開。天涯的人告訴我,每天的點擊量、閱讀量都是非常大的,達到100多萬的點擊量。這個是非常奇特的,他們不光看,而且討論,這些都是出乎我意料的,造成了一個傳播上我沒有遇到的效應。而且速度非常快,想說什麼話都說出來了。而且竟然也就都過關了。
李:您覺得32年前您在抗震救災以及採訪中的經驗在今天的適用度如何?
錢:適用度上來講肯定要大量地去更新,因為發展到現在,技術水平已經更新換代了好多,技術上當然要更新,這是其一。其二,記者有一些不變的東西。當時有短處、當時也有長處。當時的短處是信息不發達,因此沒有人去搶新聞,沒有搶新聞的必要。反而我這樣一個不帶功利目的的人,我以救災隊員身份在唐山的人,后來又以唐山家人的身份——像唐山人的孩子一樣的——我在媽媽的朋友家裡住下來在那邊呆了三個月,這樣的現象在現在又不容易了,當然現在報社能賦予記者這樣的使命的話就更好了,但是現在不容易了,更多地是要搶,搶新聞。
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您有點像最早進行公民新聞寫作的人。
錢:公民新聞寫作今天如果是跑到災區,能夠住下半個月的都不多。
李:今天的公民新聞寫作有這個意識,但是未必有這個資源。因為您這樣的身份,使得您能夠採訪當時的一些官員還有災民,能上直升飛機。今天的媒體能上直升飛機,但它又不是獨立的公民新聞了。
錢:當時我沒有上飛機,在上海上不了飛機,然后做火車去。我比較奇特的經歷是由於我住的這個人家是管救災的民政局長。所以他把很多救災的事情都讓我去做了,我去護送孤兒到孤兒院,我去採訪盲人、殘疾人,這都是他給我的機會。這些事情都非常有利於是我日后的報道。我還是覺得,今天的快和以前的慢都是需要的。今天快的都出來了,但是如果說要對災區有一個持續關懷的話,將來還是要有人進行慢的工作。
李:所以您剛才說的以前的短處不能夠搶新聞,長處就是可以呆久。
錢:可以打深井。我當時呆的三個月不說,后來在長達將近十年的范圍內,我多次去,這樣就可以進行一定的考訂。還有一個就是你要相信,調查報告是短時間內很難做的,現在可以看出我當時三個月內做的那個大震前后國家地震局的預報只是一個雛形,這是要花時間的,短時間內搞不定。
李:對於現在很多記者臨時帶了這個本書上飛機,上前線惡補地震方面的知識,您會不會覺得記者在地震知識傳播和科學方面有真空?
錢:有真空,但是這是很無情的一個事實。八十年代由於文革的信息封閉,導致地震十年之后1986年我的書才出來,被人們當作新聞來看。當時的報告文學家就有一個評判,把它稱為“冰凍文學的解凍效應”。當時解放軍公布的我們解放軍就印了68萬冊,其實我知道很多盜版就印了四五百萬冊,機器都印壞了。但是U字型低端到來的時候,這本書又被忘記掉了,以至於連我兒子都沒有看過我的書,這期間的時間當中有很大的斷層,導致地震知識傳播的不力。
李:您覺得這個斷層的主要原因是什麼?特別是我們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好像我們把地震都遺忘了。
錢:在中國東部地區,遲遲沒有發生過七級以上的地震,已經很多年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唐山以后就沒有發生過。這次發生在東西交界線上,東西交界是從黑龍江的黑河劃到雲南的騰沖,這條線你一畫就知道,今天的汶川正好在這條線上。這條線以東,財富、經濟更加密集的地區,一直沒有發生大地震,西部也沒有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發生。隻有在青藏高原上面發生過一次,但是完全沒有人口傷亡。麗江地震已經算比較大的了。地震局反復說高潮期會到來,但是高潮期並沒有到來,只是從這次地震以后人們才意識到高潮期有可能到來了。
李:您認為這次事件是否有可能導致以后科技記者的增多?
錢:一定會的。可能不光是地震,也許有科學、救災、防范、醫療方面有經驗的記者都會增多。
李:就採訪本身的體驗,您覺得在唐山地震的時候,心理的調節有問題麼,面對著那些現場的沖擊?
錢:現在想起來比較含糊,但是當時一定是有的,特別是看到解放軍戴著防毒面具在運尸體,我自己拿著噴藥罐噴著,但記憶有點模糊了。我特別感覺到,這一次因為媒體報道特別快,讓好多人巨細無遺的感情表達第一時間都公諸於眾了。當年因為沒有這些東西,事后採訪慢慢講述出來是很不同的。所以在大家印象中,當年唐山大地震的人民好像比現在的人堅強,或者說麻木,這也可能是媒體傳播放大效應的一部分原因,這次會放大很多東西的。
李:您做了那麼多后期跟蹤的採訪、訪談、挖掘,這對今天四川地震之后的三年、五年、十年都是很寶貴的經驗,您覺得有什麼可以傳遞下來的嗎?
錢:我就是特別希望他們去做,比較純粹地去做。我比較擔心的就是兩種驅動力的作用,分別是政治的驅動力和資本的驅動力。如果驅動力沒有了可能就不會有報道了。政治的驅動力很簡單,他有時候希望你去報道某一個事件,你就拼命去報道,但是政治驅動力是會轉移的,過些天他又有可能希望染你去報道另外的一些事件,那就不是媒體所賦予你的任務了。另外一種就是資本的驅動力。現在這樣做可以增加媒體的影響力、發行量、點擊率和收視率,但是過一段時間就可能沒有了。那還會不會去做呢?這兩點如果都除開,個人必須要有一種極大對人道主義關懷、對災區的關懷,才可能推動你三年五年地不斷做下去。
李:比如說更細的採訪技巧,受難者心理傷口在愈合的時候,您會怎樣打開他們的心扉,不使他們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更加痛苦?
錢:這裡面有兩類不同的人。一類人是比較堅強的,跟這些人打交道相對來講是比較容易的,對這些人我對他們的採訪跟新聞記者通常的快速的採訪是不同的。比如我採訪的那個十三天被挖出來的老媽媽,當年我見到她的時候一句話都沒說過,只是看著她在挂鹽水。過了8年后再去找她,我從公安局卡片中大海撈針,從六個同姓名的人中找出這個老媽媽。然后我再見到她的時候一見如故,像成了她兒子一樣,我甚至在她家包餃子、吃飯。當然這裡面也有一個美麗的誤解,她認為我就是當時救她的那個解放軍戰士。這個裡面有很多拉近距離的方法。我跟很多唐山人都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他們對我都非常好。因為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不是像現在的記者,不是拿著錄音機、採訪本去採訪和記錄。我后來的時候都是追記的,到后來都不需要記錄。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八年以后採訪、十年以后寫出來的東西,到了地震30年之后的時候,2006年全國有很多媒體進行了追訪,他們把我裡面提供的線索又都搜尋了一遍,你會發現,他們很多說了和我一樣的話。所以真的不要以為技巧是太重要的東西,要把自己當做普通的人。而他們更多把我當作救災隊員。你是來救過災的人,所以他們心理上有親近感。唐山人對解放軍是特別有感情的,當年解放軍特別好,因為我也是一名解放軍,所以他們也就對我像對待親人一樣。比如我和礦工聊天的時候,就是坐在炕上和他們一宿一宿地聊。他們叫“嘮嗑”。慢慢地就嘮出了很多細節、很多故事。
李:如果您今天還是一個媒體的領導,派記者出去,您是否會面臨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您希望記者很快地出稿填充版面,一方面又希望他們能做得深入?
錢:我想這個問題是媒體第一需要和第二需要的問題。第一需要是媒體需要把事情、救災抗災的第一現場的情況最快的時間之中報道出來,用媒體參與救災。這個時候你不能提出縱深的要求。如果要把一位大娘的心理描寫出來,那是是過分的要求,而且沒有必要,不合時宜。所以第一時間能做的就是現在媒體在做的事情。然后需要的就是第二需要、縱深方面的問題,是日后一個持續的關懷,需要更加從容、有耐心的採訪。我現在如果是媒體領導的話,我就會讓記者去抓災區真相,像《南方周末》一樣,報告和再報告。我不會讓他們像我十年前一樣,那個可能還是錯誤的。現在讓記者坐在炕上和災民嘮嗑,不一定是正確的。
李:為什麼會是錯誤的呢?
錢:因為時機和心境不一定是最佳的時候。你如果有能力在旁邊觀察,靜靜記錄是好的。隨著傷口的愈合,災民慢慢有自己的感受,那時候你再慢慢地進入,關心他們的問題,那個採訪時機是好的。什麼事情都是抓住最佳時機最關鍵了。
李:您當時在唐山採訪的時候有什麼裝備或者其他物品准備嗎?
錢:大蒜、黃連素,僅有的一瓶糖,椰子糖比較有營養,到了災區的第一天就被發放完了。簡單的筆和本是有的,那個時候我是文學青年。但是也沒有錄音的設備。但是我是解放軍,有一些戰備意識。
李:那個時候進入那個地方需要什麼証件嗎?
錢:有介紹信,我的介紹信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介紹信,一定要有介紹信。后來我的蔣叔叔因為是民政局長,他給我開了很多綠燈。
李:您是否同意有些記者的想法,認為救人比寫報道更重要?特別是第一批進入的記者,慘狀還在面前,呼救聲還在耳邊的記者。
錢:我同意,但是記者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沒有專業救援知識的話,得考慮怎樣合理地和專業人員結合在一起來做這個事情。如果有人需要搭你的車的話,肯定應該讓災民上車。
李:您對這次報道的主題、傳達出來的東西有什麼評價嗎?
錢:就大方面來說,這次也生命為核心是對的。我統計了唐山地震和這次地震的頭十天《人民日報》的報道。唐山地震中,頭十天,《人民日報》中出現“生命”這個字眼的文章隻有七篇﹔但是這次就有149篇。所以你也能理解,充斥在耳邊全是“生命,生命”,這是好的。但是這次也不是沒有值得反思、檢討的報道。我最擔心的是媒體把”奇跡“報道得太多,干擾了救人。所以我在《最后一搏!為生命不為奇跡》的文章中就是表達了這樣一種態度。
李:這次您文章中提出的觀點也有人反駁。您當時說面對這樣的大災難,質疑在那時是不合時宜的,應該全力以赴地去救人,但是針對這個也有人,如張曉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面對真相的質疑永遠不會不合時宜,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待?
錢:我說的現在不是時候,文章的標題是《現在是解民於倒懸的關鍵三天》,事實上不用我回答,大家做的都是救人。你看七十二小時裡面,所有媒體,不要說想不想質疑和反思,到了前線都是想的去救人。我說的質疑不合適是說那個時候談大的面上的東西搞深沉不合時宜。
李:但像《亞洲周刊》邱立本主編也談到他們質疑了建筑質量,他覺得挺驕傲於這一點,因為他在地震第二三天很早就寫出了這個文章。您是否覺得這種觀點也是救災的一種雜音呢?
錢:我不認為這個是雜音,我不支持的“反思”有特指。當時地震發生的當天下午就有人邀請我在廣州參加一個反思會,我說我不參加。我說現在不是反思的時候,我現在全部想的就是想任何辦法,包括噴水、送風,把廢墟中的人挖出來,而且我認為這是現在最應該做的。看過我寫的全文的人不至於產生誤會。我說你們要做的這些都是應該的,然后只是現在不是時候,現在是解民於倒懸的關鍵時刻。
李:另外一個比較現實的事情,當時如果做反思的話還可能可以做成,因為當時沒有禁令。
錢: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說真話的時候不會考慮是否我的話跟別人說得一樣。政府是從控制的角度不讓你反思,我是從救人的角度不支持反思,如果兩者有重合,那沒有問題。有人是偏要和政府反著干,政府不讓你反思的時候偏要反思,這樣我認為沒有必要,這是我個人的觀點。頭三天讓我去參加反思會,我絕不會去參加。至於說別人要反思,別人有反思的自由,我只是說這個不是時候,要玩深沉更不合適。所謂玩深沉還有一個含義,我拒絕了很多人第一時間要把我帶到現場的建議,這是作秀,他想搶一個別的媒體沒有的角度。讓我現在就去談歷史上怎樣怎樣,我不會去做這個秀。
李:這次意見這麼多,另一個驅動力也是網民比較敏感,反應也比較激烈,您怎麼看待網民的意見?
錢:網民的意見我們擇善而從。網民的意見如果跟你的見解不同,你讓它們和你的意見獨立存在,可以是一個並存的關系,這個沒有問題。一個知識分子不應該去利用,更不應該讓自己受網民意見的左右,或者為了迎合網民而說一些話。如果我的話有些觸怒了網民,冒犯就冒犯了,那別無選擇。因為你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你也可以不說。
李:您有沒有想接下來為四川、為地震報道做點什麼?
錢:因為我現在還是在香港做研究,我是為一線記者服務的,我自己是不可能做汶川的報道的,我願意為真正的反思提供建議。比如大家想反思地震預報,我首先講地震的資料應該善保勿失,我可以告訴大家資料在哪裡,而且我列出了幾條必要的資料。第一條就是歷年全國地震趨勢會商會。它對於龍門山斷裂、龍門山構造的判斷是怎樣的。從1976年鬆潘平武地震以后的歷年四川地震資料在哪裡,那麼多觀測點的觀測數據在哪裡,因為我是在地震局工作過的,我可以提供給媒體人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你不會是從零開始,我希望看到的是切實的反思,不是情緒化的責罵。罵人不是反思。(i 汶川地震后不久,從六月開始,錢鋼即閉門查閱史料,思考地震預警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在八月號在“地震反思”專欄刊登了錢鋼的長篇論文《地震預警問題初探》 )
也包括對於豆腐渣工程,如果你已經看到了跟墳墓一樣的學校,你說它是豆腐渣工程就不是什麼新鮮的了。如果你要說周圍十萬公裡全部的學校建造都是豆腐渣,需要証據,你要讓我們看到証據。
我說的意思是,不要讓豆腐渣工程的罪魁禍首——黑心的建筑商,有逃脫的可能性。四川全省地震的地震裂度是七度,設防就隻設定到七度。隻要在四川境內倒塌的校內,沒有被你看到鉛絲一樣的鋼筋,如果真的是黑心建筑商,就有逃脫的可能性。記者的責任就是要不冤枉好人,也不放過壞人。我們這次都知道劉漢中學做得很好,但是我就沒有看到報道中說劉漢中學地震是幾度,是極震區嗎?如果劉漢中學所處的地區是11級的極震區而它還沒有倒,那麼它就是奇跡。它為什麼沒有倒,那它就是做得和防原子彈一樣牢固了。但在中國的設防是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筑做成軍用建筑的。首先現在是市場社會,我可以做出能防原子彈的房子,但是你買不買呢?老百姓要買他們買得起的房子,它一定隻能是某種程度的平衡。
所以這次,我覺得信息不明確,什麼叫十萬平方公裡呢?什麼叫破壞最嚴重的地方達到十萬平方公裡?沒有人告訴我們這個概念。我能夠猜測的,十萬平方公裡是7度區的概念,就是地震七度裂度區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大地震才是大過唐山地震的。在這個區域裡,我希望出現一流的記者,去調查哪些校舍應該是牢固的,同樣在八度區,當然承包商是按照七度裂度去設防的。學校也是按照這個標准設防的,但是為什麼周圍的房子沒有倒呢?
還有一個維修的責任。有些房子是因為多年失修而倒的,還有的學生不是因為豆腐渣工程而受災的,豆腐渣只是其中的一個符號。青川木魚鎮的學校怕學生中午去打游戲,把學生鎖在裡面,逃不出來的。這是人為的一些不合理的規定。我希望記者現在去補充這種知識。
比如地震設防的標准是大震不倒,中震不壞,小震可修。大震不倒就是房子壞了,不可修了,但是不至於死這麼多人。所以現在讓我來表達一下的話,當然應該開始反思,但我希望這個反思建立在優良的新聞專業主義水准之上。我們應該把最近十年以來,中國調查報道記者已經積累的最好的品質,最重要的經驗進行充分地發揮。我們不要簡單地抱怨說政府讓不讓我們反思,但是我們如果做得好的話一定有機會的,政府會改變的。
李:您有沒有想過做一些培訓?
錢:我在香港這邊做了一些,在香港房屋署講了一些。當然現在確實需要對地震方面有一定知識的人去進行宣傳。這需要有一些積累,有積累的人還應該去考慮救災預警機制的問題。
李:您有沒有想過利用你所有的平台幫中國記者提高水平,甚至說讓有些人專門做一些項目,達到您剛剛提到的獨立、細致和深入地觀察?
錢:我現在覺得不止是豆腐渣工廠、救災反映、地震預報這三個問題,應該還有別的問題。有時候不止是政府做得不好,還有是政府努力做了,比如堰塞湖問題。還有一種中性的調查,著眼於未來的對策、應對,這方面也特別有意義。
李:您覺得這次事件對於中國新聞史的突破和意義在哪裡?
錢:突破是一個証明,包括我們之前說的以人為本。它已達到這一步,讓人們看到了知情權的進步,它提供更多信息讓你來獲取的﹔第二是表達權,它讓你有可能去表達了。這兩點都要進步,而不要退步。我希望能夠鞏固。
李:您看好媒體環境的繼續良性發展嗎?
錢:審慎樂觀,我並不興奮,而且有進兩步、退一步的思想准備。我特別想說,媒體人我們是共同體,我們都希望公開開放,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挫折放大,生活會充滿了抱怨。我們要做的應該是相互打氣、舔舐傷口。“你也太CCTV了吧”這樣的話很不利於媒體作為一個共同體。這種非黑即白,媒體裡面把自己人為地劃線是一種舊時代的思維,不利於今天的進步。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媒體之間不要競爭,要團結,我在汕頭大學2005年舉行的海嘯研討會上也說過這樣的話,一篇好的報道,傳得越廣越好,為什麼不可以讓其他媒體來用呢?這個時候生命比任何職業榮譽都更重要。
李:您覺得這次地震之后,大家對於中國媒體的發展會有一些樂觀的想法嗎?會不會精神煥發,不至於死氣沉沉?
錢: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主流媒體中突破了過去的禁區和樊籬,會有一些記者比較昂揚﹔但是稿子被斃、節目被撤的記者可能會比較灰暗。但是我想說的是,希望兩種人都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比較昂揚的人要看到同伴的種種委屈﹔這次心情比較灰暗的同仁們也要看到畢竟還是有進步的一面。我還是持有一種比較中性的看法。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