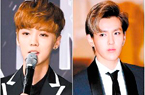紙媒進軍新媒體,是為了獲得競爭優勢。但對手不會甘居劣勢,哪怕模仿也要跟進,那是為了獲得競爭均勢。均勢極不穩定,總有媒體落入競爭劣勢。把媒體競爭視為歷時變化的狀態,結果就有競爭優勢、競爭均勢、競爭劣勢之別,優勢還分短暫優勢與持續優勢。本文討論這幾種情況,上篇分析短暫競爭優勢,下篇討論其他三種。
一、短暫優勢及耗損
把紙媒進軍新媒體畫一道弧線,兩端分別是:小投入、低風險和大投入、高風險。兩者各有優勢,也會因不同原因耗損,因而大都是短暫優勢。
先動優勢因模仿者耗損。小投入、低風險是進軍新媒體的普遍情況,常稱的新媒體“四大件”:微博、微信、App、網站,還有紙媒常用的二維碼、手機報等,大都屬於小投入、低風險類。你比競爭對手搶先,至少獲得吸引眼球的先動優勢。但這優勢也非常容易耗損,因為這類新媒體門檻低,進入難度小,你投資少、見效快,人家也投資少、見效快。低門檻技術是標准化、簡潔化、傻瓜化的,看到先動者得甜頭,追隨者會迅速跟上。或者直接模仿,你微博我微博、你微信我微信。或者間接模仿,形態不同功能類似,你微博我微信,你手機報我App。或者模仿包圍,直接模仿的、間接模仿的起哄架秧子,先行者淹入“大家差不多”的一片汪洋都不見。
財力優勢因不確定耗損。再看進軍新媒體的另一端:大投入、高風險。大投入必有財力優勢,不管這財力來自政府項目、風險資本、借貸還是發行股票。財力就抬高了門檻,一般對手無法進入。它不怕模仿沖擊,但要面臨另一種風險:不確定耗損。主要是兩種不確定:技術和市場。美國學者杰伊•巴尼等認為:技術不確定指一項IT投資可能在預定時間不能達到預期績效,具體風險有:
——由於實施困難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比預期實施成本高﹔
——比預期實施時間長﹔
——技術績效比投資時預期的低﹔
——研發的IT系統與選用的軟件和硬件不相容。
這5個風險提出在2004年,想想“即刻搜索”2013年的命運,每一個都像10年前的預言。杰伊•巴尼繼續分析市場不確定,指用戶接受新IT產品的風險。盡管產品達到了技術目標,但用戶就是不接受,可能他不喜歡,也可能替代品太多,反正你用戶不夠,收不抵支。①我的天!這不就是對默多克iPad電子報《The Daily》的分析嗎?回想《The Daily》研發時遇上不少唱衰,信乎塔列朗之言:“比中傷更可怕的武器,就是事實”。
以上分析進軍新媒體的兩極,連接兩極的光譜是風險由低到高,你想低風險,就搞小投入,那就缺乏門檻,眾多模仿者跟風,要耗損你的先動優勢﹔你要抬高門檻,就搞大投入,模仿者少些,但風險也大,技術不確定和市場不確定又要耗損你的財力優勢。兩極之間還有很多復雜情況,比如,大投入的先動有優勢嗎?沒有!反而有先動劣勢,因為先行者要付出“探路”成本,你解決技術和市場不確定的成本很高,等你基本解決,模仿者反而降低風險,反而有“后發優勢”。這兒不分析各種復雜情況,隻從兩極簡要說明,進軍新媒體可以獲得競爭優勢,但也容易耗損,因而大多是短暫優勢。常見人重復一句話: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一時間不少人開始羨慕豬,似乎沒想過,風口上的豬就是獲得的短暫優勢。
二、從短暫中多收獲
別嘲笑會飛的豬,短暫優勢也是優勢,明確其短暫,就爭取多收獲。這有以下5條途徑。
彌補紙媒弱項。任何媒介都有特定潛力和局限,新媒體以下長處,確實能為紙媒補拙。一是速度,首發紙媒內容的預告和推介。二是選擇性,在紙媒大眾傳播外,選擇一些內容通過微信、App、豆瓣、博客等推送,有針對性地分眾傳播。三是到達率,新媒體有跨時空的潛在廣泛到達率,把過期(強調“過期”,詳后撤掉電子版)的報刊再上網,在新媒體上延伸影響。四是多媒體,圖片、圖表、音頻、視頻,讓紙媒的部分內容可視聽,尤其用在廣告,如房地產廣告的戶型實景圖。
五是互動,這是個復雜問題。從新聞角度看作用不大,微信、QQ等的互動偶爾能發現報道線索或獲得反饋,但非常牽扯精力。因為新聞來源不可靠,核實過程比常規新聞來源復雜好多倍。還因為反饋的千奇百怪,用戶要了解宇航員的太空生活,你滿足他,下次他要地心游記、要見拿破侖……互動是新媒體的突出優勢,但不是別人優勢“都”能為我所用,全球報網互動搞了10多年,也沒搞出個可復制的成功模式。關鍵是,互動,走向深層即互相控制,其與紙媒的“輿論導向”“授予地位”等功能是矛盾的。他要你轉發“老軍醫治性病”,你滿足不了,那互動就走不遠,你去解釋還被罵一頓。但是,從營銷角度看互動有潛力,像現在常見的報刊的汽車、旅游、美食等微信號,就是用分眾傳播來固定一部分有特殊需求的群體,讓他們成為紙媒手中對廣告商有吸引力的資源。
滿足特定受眾。報刊受眾由多個群體組成,近段時間,紙媒喜歡講“全媒體”,盡管遇到不少難題,但陳國權分析它受到兩類受眾的歡迎。一是當地黨委政府,其工作動態、宣傳主題,用多種媒介形態傳播,效果更好。二是廣告客戶,希望最大產出比,隻付平媒廣告的錢,而新聞網站、手機報、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廣告作為附帶贈送品,客戶會認為物超所值。②
這分析厘清了全媒體的目標受眾,有利於進一步探討。首先,全媒體不是自身媒介“品種”的全,而是滿足目標受眾“需求”的全。那麼,建設全媒體實際是產品組合決策,以“一組”產品滿足用戶。決策者必須了解兩個重要信息:每個產品的投資回報率,產品組合與競爭對手的比較,從而把資源投向對手薄弱而回報高的新媒體品種。其次,全媒體不僅做加法,還要做減法。那些受眾不感興趣的品種,或缺乏競爭力的疲軟品種,管它新不新,都要及時砍掉或大刪功能。想想索尼的“隨身聽”吧,它只是把當時爛大街的錄放機,砍掉錄音功能,節省成本還成重大創新。砍掉或刪除一些,對外未能免俗且稱“全媒體”,心知肚明它是“缺媒體”,或者更雅致些,它是“疆界不斷移動的媒體”。再次,既然“全”是為滿足受眾,有必要每家報紙獨辦嗎?能否報刊集團辦一個、或幾家報紙合辦、或干脆借用別人的新媒體,反正受眾隻要報紙有字、電視有影、廣播有聲,他才不管影像來自何方。
付費請我參加。以上兩點多是自辦新媒體,其實,何必都自己辦?分工合作嘛,把你擅長的內容賣給新媒體。但當前賣價極低,因紙媒先上了免費電子版。我已一、二、三論“撤掉電子版”,並引博弈論証明,隻要約5%的成員結盟,就足以造成影響。③沒想到這首先來自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所有期刊,一共80多本,與“中國知網”談判不成,從2013年開始,全部從知網撤掉電子版。往往見論文以知網為依據計算論題、關鍵詞,從2013年起,那裡少了一大塊羅。
撤出知網去哪兒了?有些轉移到中國社科院承建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其中有些屬“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按資助要求,要為此數據庫提供電子期刊。得此消息我第一反應——這是“付費請我參加”呀!有國家基金資助,當然可以給你電子期刊!資助的那筆辣價錢,是賣給知網的近百倍!
古羅馬執政官西塞羅被邀赴宴,先問:誰將受益?偉人就是偉人,他知道,他參加一個游戲,也就改變了它,宴會因他在場,不同於沒他的宴會了。參與,就是改變游戲的杠杆。紙媒手握版權,隻要組織起來,即約5%的成員結盟,先撤掉電子版,然后學西塞羅問一句:誰將得到“聯盟”的電子內容而受益?受益者會願意付出報酬,於是,你借助別人的新媒體傳播,還是紅包鼓鼓的同台吃飯。
付費讓我退出。與某期刊老總聊起社科院期刊退出知網事,他脫口而出:我又不是基金資助期刊,目前在知網,總還有報酬,讓我退出,這損失怎算?我恍然大悟,退出也要付費呀!
讓對方付費,關鍵在激化競爭。“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與“中國知網”是競爭對手,你的進退,就是給競爭一方加砝碼。舉一反三,新媒體的競爭多如繁星,像當前的四大新聞客戶端:搜狐、騰訊、網易和鳳凰,競爭開機廣告就打得你死我活,紙媒自辦客戶端,費力不討好,你在“四大”中穿梭提供嘛!紙媒喜歡講內容為王,你關起門來做皇帝自辦新媒體卡拉OK好大個王,你走出去,尋找競爭雙方,扶東則西弱,助西則東弱,你是內容生產商,最有價值的是以內容激化競爭,靠智慧賺錢。
再觀察,移動互聯網與桌面互聯網在激烈競爭,社交網絡與搜索引擎、微信與微博、微信群與微信公號、百度百家與騰訊大家……都在激烈競爭,我曾論述撤掉電子版的紙媒“聯盟”別把所有內容一次性“批發”,要“零售”——把專版、專欄、專題、評論、頭條等,重組為聯盟的“分類數據庫”,賣給“不同”網媒——把面包賣給雙方,它們就可以繼續打下去。
任何一方打敗了,對紙媒都沒有好處。有報人對微博遇冷幸災樂禍,未免心胸不廣如周瑜,微博衰退,對紙媒有什麼好?報刊在微博上投入不少,微博無足輕重,這些投入都成為“沉沒成本”。如微博再衰退,紙媒最好有集體行動,別讓微博成為博客第二。報刊對博客投入也不少,當時坐視其衰退,老人倒了不扶也害自己,那些博客成本再也打撈不出來了。你總不能一次次投入新媒體,又一次次隨它衰退而讓自己的投入打水漂吧。春且住!多留春一陣也好,報刊集體行動“賒”面粉都該救微博。
你不需要滅別人的燈光使自己明亮,微博之后,紙媒還會遇上其他新媒體挑戰。一種新媒體來去匆匆,但后續形態不斷出現,一系列挑戰構成紙媒“永恆的危機”。最值得做的,是運用現在時髦的互聯網思維,要“分享”,與新媒體“分享危機”、分享壓力和連累……湊熱鬧不嫌事大。紙媒要全心全意為新媒體服務——賣面包激化競爭,吃了面包要發熱,要讓新媒體們盡可能打下去,而且一方不能很快戰勝另一方。它們斗得越厲害,對紙媒就越好,這要靠紙媒聯盟以不同配方的面包(重組的不同數據庫),精心選擇賣誰與不賣誰(參加與退出)。
進退“付費”是簡潔說法,傳媒人都白領粉領的,哪能非要點鈔票搞得自己像個圓領,既冒昧也不明智。博弈論專家內勒巴夫,提出“付費”的七種方式:④
——要求對先期投入,如改造生產線的成本進行資助﹔
——要求得到擔保的銷售合同﹔
——如有其他競爭者,要求簽訂最終考慮條款﹔
——要求得到生意的更多信息,從局外人變為局內人﹔
——利用出價機會接觸對方高層﹔
——除當前合同外,要求對其他生意出價﹔
——現金當然也可以,人民的幣人民愛嘛!
留一手不結盟。把以上七種付費方式分合運用,新老媒體的競爭與合作犬牙交錯。但要明確,這都是短暫優勢,進退付費會因模仿者、因市場與技術的不確定而不可長持,長久還得靠自力更生。我分析過《新聞記者》的法人微博:“《新聞記者》雜志紙質版是第一時間獲取本刊完整內容的唯一渠道!”說它提出了紙媒長青的12字箴言——紙質版是:第一時間、完整內容、唯一渠道。⑤
沒想到期刊已有不少實踐,前面說“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要求把電子版與紙質版同步上網,即放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但是,不少期刊都拖延了。仍看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屬的資助期刊,我2014年10月20日搜索此數據庫,最新的《新聞與傳播研究》,是2014年6期,再看文史哲經的最新:《文學評論》2014年3期,《中國史研究》2013年3期,《哲學研究》2014年6期,《經濟研究》2014年3期。該數據庫2014年5月26日新浪法人微博,回答網友上線期刊的更新——“每本期刊的更新速度根據不同編輯部的要求是不同的,一般是滯后一期到兩期,最長的也有滯后半年上線的。”——《中國史研究》業已打破這記錄了!這些電子期刊是將曾在知網的“收費”策略,轉成現在的“拖延”策略。網上讀者收不到幾個錢,拖延——報紙或更適合殘缺——才促使讀者回到紙媒,這就是留一手!
紙媒老想棄紙上網,我反復論述,紙媒的優勢在線下,不在線上。你到別人的陣地作戰,對手太強、變數太多,你是以劣勢對人家的優勢。紙媒從1979年進軍互聯網——該年加拿大《環球郵報》辦出自稱是“世界首例”的電子版,搞了35年,上升停止了,下降卻停不下來,魯莽沖向別人陣地是根本原因。然而,如果紙媒不承認“先前”失敗是“最后”的失敗呢?那要重新選擇陣地、選擇時間地點、以自己的方式參戰,隻要作點小改動:留一手!其正面表述:確保紙質版是——第一時間、完整內容、唯一渠道。有此紙上壟斷,網媒才不能“完全”替代紙媒,你才保有生產面包的百年老店。甚至,參加聯盟的“各家”紙媒都要留一手,要考慮聯盟天生的脆弱,盟友總伴隨爭吵、博弈和背叛,每家紙媒留一手,是自力更生建設根據地、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
各家紙媒留一手最多保護自己,而當報刊“聯盟”組織起來留一手——硬幣的另一面就是賣面包,再與不結盟合用,紙媒又獲得一種競爭優勢。且回顧“不結盟”的源起,那由南斯拉夫的鐵托元帥首創,基本思想是不承諾冷戰中的任何一方,但保留作出承諾的可能性。如果一個超級大國的壓力過大,弱小國家就威脅同另一個超級大國結盟來保衛自己。斯大林與鐵托決裂,鐵托從美國得到經濟援助﹔他也意識到不能太指望美國,留下與蘇聯和解的余地。
紙媒賣面包給新媒體,如果對方出價太低或商業欺詐,就威脅——或實施去賣給它的對手,讓新媒體制約新媒體。紙媒討伐“今日頭條”,指責與起訴似乎是智慧的極限。其實,起訴“今日頭條”的還有搜狐,索賠1100萬元﹔“今日頭條”反訴搜狐商業詆毀,索賠100萬元……新媒體打起來了,紙媒正好選邊站——如果以紙媒“聯盟”選邊站,力量就更大,進退都能抬高身價。唉!紙媒以不介入為禮貌,以自我孤立為幸福,時機過去了……且把病歷升華為藥方,療人也自療吧。
國際關系中的不結盟表明超級大國並不能為所欲為,大國命令小國團團轉的能力非常有限,美蘇雙方都盡力把小國納入其勢力范圍,這種強勢反而給了小國擺脫控制的手段,因為小國可以隨時倒向另一方,或至少威脅要這樣做,尾大不掉、尾巴開始搖狗了。⑥回到媒體世界,紙媒對新媒體就是弱勢,如果“留一手”又“不結盟”呢?留一手保証面包生產能力,不結盟賣面包給新媒體又保持中立,同時保留不中立,倒向它對手的可能性。國際關系中的不結盟后來成為世界運動,多次召開首腦會議,為運動注入新活力。我們的報刊協會,晚報、都市報或學術期刊協會等是否研究一下,如何把紙媒組織起來,以“聯盟”的方式在自己的陣地作戰,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作戰。邁克爾•波特說:真正的戰略,就是選一條自己的跑道。
原載《中國記者》2014年12期,標題《進軍新媒體 贏得紙媒優勢》。
注釋:
①杰伊·B.巴尼、德文·N.克拉克:《資源基礎理論——創建並保持競爭優勢》,159、160頁,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陳國權:《報業轉型新戰略》,32頁,新華出版社2014年版
③張立偉:《撤掉電子版 拯救紙媒》,《紙媒防御戰的第一塊盾牌——二論撤掉電子版拯救紙媒》,《App是報刊戰略失誤——三論撤掉電子版拯救紙媒》﹔《中國記者》2011年10期,2012年2期,2013年10期
④拜瑞·J.內勒巴夫、亞當·M.布蘭登勃格:《合作競爭:博弈論戰略正在改變商業游戲》,95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張立偉:《認識媒介能力 開發報紙生機》,《新聞記者》2014年10期
⑥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冷戰——交易·諜影·謊言·真相》,145、15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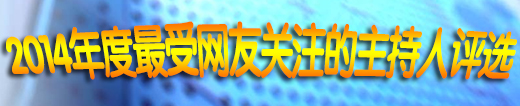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