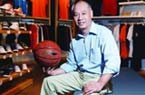|
|
|
夜未央,天欲曉。
12月12日凌晨5點半,西安市救助站流浪未成年人保護中心,一層女生宿舍靜寂無聲。當記者輕輕踏進房門時,在枕邊兩隻毛絨熊的陪伴下,心月和同屋的女孩們猶在夢鄉。這是她在這裡度過的第1027個夜晚,也是她在古城的最后一天。
穿衣、疊被、洗臉、刷牙……被生活老師輕輕喚醒的心月,重復著往常的生活節奏,但內心的情感波動似乎按捺不住,笑著接過新書包和文具,又笑著登上返鄉的面包車。
時針指向6時30分,寒意未消,跟隨高速路牌四川達州方向的指示箭頭,記者陪同西安市救助站護送人員驅車一路南行。
沒有與小伙伴們告別,心月隻翻出一本大學生志願者送給她的合影相冊帶在身上。幾張照片,將承載這位11歲女孩對這裡的全部記憶。
從西安救助站到四川達縣南外鎮千坵村
■沒有哭泣,她用陌生而拘謹的擁抱迎見久未謀面的親人
穿秦嶺,越漢江。坐在車尾的心月,似乎有意回避著記者的鏡頭,扭過臉安靜地凝視著窗外。
“愛笑,不愛說話。”這是她兩年多來留給西安市救助站工作人員的印象。
“被公安部門送到救助站之初,和很多孩子一樣,什麼都不願意講。時間長了,才慢慢吐露出籍貫、家庭情況等信息”,西安市救助站副站長仵國典在車上低聲對記者說。
直至不久前,通過勸導,小姑娘才說出在老家就讀小學的線索,由人民日報法人微博發起,在記者和熱心網友協助下,西安、達州兩地民政、公安部門僅用一天時間就找到了她的家人。
一天急速“愛心接力”,改變了心月的人生路徑,卻無法挽回其遠離家庭關愛、滯留救助站的逾兩載光陰。
孩子的內心世界,大人們通常讀不太懂。曾經流落街頭的“迷路雛燕”,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方式,更值得成人俯身用心揣摩。
這一點,在心月見到父親、外公和妹妹時,格外觸動人的思索。趕到達州市時,已過晌午,沒有哭泣,沒有“希望捕捉到的鏡頭”,心月僅僅用陌生而拘謹的擁抱迎接著久未謀面的親人,面對當地民政、教育、婦聯等部門工作人員的關切,她隻輕輕地說著一句話:“謝謝叔叔、阿姨。”
誰都猜不透,面對眼前這一切,那平靜如水的雙眸下究竟蘊藏著怎樣的情緒湍流,抑或是茫然無措?隻有被救助站人員送回達縣南外鎮千坵村,背朝眾人坐在老家舊屋熟悉的門前時,臉上的愜意放鬆,才偶爾流露出卸下心防的真情。
“截至11月底,救助管理站共對224名救助的流浪未成年人進行過調查”,達州市救助站站長何立安細數著流浪兒童的成因,“除了走失和孤殘遺棄,父母離異,家庭暴力,因父母外出打工老人無力管教而輟學的情況越來越多。”
家庭社會教育缺失和監管不力,令“迷路雛燕”們失去的不僅是“家”。
“少無所依”,更是心靈無所依靠。
在縣城與人合租的“家”
■女兒入睡后,單親爸爸出門,“做保安,值通宵,一個月能拿一千五六吧”
家人團聚的兩天裡,心月的父親張國兵在記者面前已三度落淚。
36歲的達縣人張國兵,當過泥瓦匠、塑膠廠工人、工地雜工、保安……他從20多歲外出打工,和孩子母親的足跡輾轉福州、西安、廣東,“農村人沒什麼文化,又沒技術,碰見什麼干什麼,哪裡能掙錢就去哪裡”,張國兵勾勒出單調的人生軌跡。
2010年初,一直待在老家由外公照料的心月,被母親接去西安與父親、妹妹一起過年,農歷正月還沒過完,外公李學仁得知,“大外孫女不見了。”“小孩有時候調皮,打罵是有的”,張國兵沒有想到,心月會就此離家不歸,“我和孩子母親報過案,一直找不到,晚上回到出租房就抱在一起哭,靠我們倆能怎麼辦?”陌生的城市,來自外鄉的農民工夫婦,一對弱小的身影就這樣無力地穿行在車水馬龍間,尋覓著親生骨肉……
“以為孩子被帶到外地上學了”,過完年新學期開學,心月在老家就讀的三裡坪小學一年級課堂上,一副座椅空了出來。面對記者的疑問,三裡坪小學校長李志勇坦言,大量農民工子女隨遷現象,使欠發達地區農村中小學的生源流動司空見慣,“有的家長流出証明都不開就把孩子帶走了”。一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離開校園、在外地“搞丟”的消息,僅僅在千坵村村民間以口耳相傳的方式被關注著。
另一方面,西安市救助站曾將心月和其他孩子的照片登報尋親,西安市救助站站長張海林向記者拿出隨行攜帶的舊報紙,“被家人發現的概率很低,成功的案例隻有一個。”
家庭、學校、政府、社會,面對流浪未成年人救助這一復合性極高的工作,龐大的資源有時卻遲遲未能同步整合為有效救助網絡。
12日晚,心月靜靜地收拾著自己的書包,而剛上小學的妹妹則時不時沖著父親撒嬌。“前妻每月給小女兒寄500元生活費,心月還得再想辦法”。在達縣縣城張國兵與人合租的三室一廳的“家”裡,避開孩子坐到裡屋的床上,張國兵對記者講述著家庭新波折。
就在5個月前,張國兵剛剛與孩子母親協議離婚,安頓閨女倆入睡后,張國兵還要出門上班,“做保安,值通宵,一個月能拿一千五六吧。”
客廳沙發上,留著一部手機,平時他用來和小女兒晚上聯絡。
父愛如山,這一晚的張國兵,才重新擔起這份重擔。
重返曾經熟悉的課堂
■比周圍人高出一頭的她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從一年級重新念起
13日上午,風中飄著細雨,記者一行走進了位於山坡上的三裡坪小學,隨同孩子父親和校長,目送心月重新回到熟悉的課堂。她的妹妹,正坐在隔壁的教室裡。
“拼音a、o、e都忘了”,成長經歷中曾經的“斷點”,讓小姑娘隻能從一年級重新念起。面對比自己小了三四歲的“同學們”,比周圍人高出一頭的心月默默地坐在教室最后排,有些無所適從。
一宿未眠的張國兵,隻好強打精神蹲在一旁,耐心勸導著大女兒,久久才轉身離去。
教室外的操場上,達縣民政局2000元的“臨時生活困難救助金”交到張國兵手中。同時,由西安市救助站、達州民政、教育等部門和當地鎮政府捐助的數千元善款也已到手。
“縣低保辦也在核實家庭情況,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達縣民政局楊曉燕主任向記者許諾。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而更多“心月們”的故事還在繼續。
“救助鏈條涵蓋事后、事前救助兩個層面,現在更多的是事后救助,重心放在如何妥善安置流浪兒童及安排其返鄉,”陝西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尹小俊認為,有必要重新設計救助資源配置方式,開展以被救助者需求為導向的事前救助工作。
“應該建立預防機制,救助機構可聯合學校、社區、村委會提前針對處於‘高危’狀態的兒童重點走訪,”尹小俊建議,“應當依托民政系統,建立跨區域尤其是周邊和相鄰區域的響應和行動網絡﹔救助機構不是應急性、過渡性單位,而是調配龐大社會救助資源的重要中轉平台。”
上課鈴響過,班主任頻頻關照心月回答問題,“孩子大了接受能力強,將根據其學習情況盡快幫她完成學業。”
走出教室,記者從門口再次回望可愛的小姑娘:冬日的早晨,書聲琅琅間,心月人生中新的一課開始了……
(文中心月系化名)
蹲點感言
心月是不幸的,當她重返課堂,那彷徨無助的眼神,更令人平添一分沉重﹔心月又是幸運的,她能夠進入公眾視野,各方最大限度調動資源為其尋親、返鄉、就學、經濟扶助提供便利。
更多的“心月”們則沒有這份“福氣”。
在心月回家的路上,本報法人微博發起尋找家人並圖文直播了返鄉安置過程,更讓我們體驗到龐大的社會救助資源一旦充分運轉起來,力量何其巨大!
毫無疑問,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是項繁雜的工程。當“社會細胞”的家庭因各種因素而面臨“失控”時,如果學校、街辦村委會等基層社會管理組織、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組織能夠及時介入﹔如果各地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門資源能夠充分協調聯動﹔如果政策的陽光雨露能夠及早滋潤這些家庭,情況會大有不同。如果每一個環節,多走一步,效果就大為可觀……
圖片說明:
圖①:臨行前,西安救助站工作人員為心月梳頭。
圖②:重踏鄉間小路,心月的腳步格外輕快。
圖③:曾經殘缺,一朝團聚。兩個女兒圍坐在父親張國兵身邊。
圖④:早上,值了一晚夜班的父親,強打精神耐心勸導大女兒。
圖⑤:老師將心月介紹給班級的同學們。
圖⑥:見到久違的父親和外公,心月雙眸平靜如水,沒有哭泣。
照片均為本報記者姜峰攝
制圖:張芳曼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