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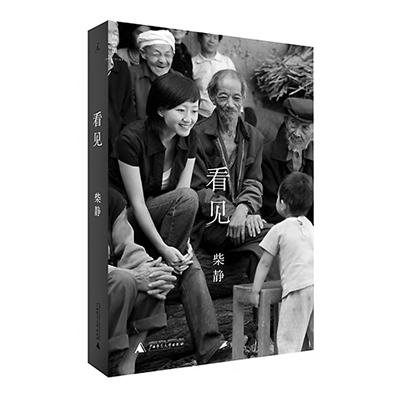
《看見》 版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定價:39.00元

柴靜和妹妹。

2006年,作為央視記者採訪兩會。

2008年汶川地震,採訪楊柳坪村民。



“我渴望呆在最寂靜的角落裡,被最熱烈的聲音包圍。”這句話出自柴靜的日記,后來又多次出現在柴靜或關於柴靜的文章裡。它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被用來解讀在柴靜新書《看見》首發式上的一張照片:
11位文化名人人手一冊《看見》站成一隊,柴靜坐在他們前方。解讀者認為,柴靜一如以往地安靜。
《看見》一書,首印50萬,是柴靜講述十年央視歷程的自傳性作品,其中有這十年中
最為重大的公共事件,如非典、兩會、汶川地震、北京奧運、華南虎照片事件、藥家鑫事件等的親歷記錄,她在書中敞開自己的思考與內省的過程,可見柴靜自身精神成長的過程。
封面故事
2000年,我還是湖南衛視“新青年”主持人,進了央視后,這個頭發很快被剪短了,穿上了套裝,坐在主播台上,想著自己臉上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麼都得想,不知道怎麼才能忘掉自己。陳虻說:“回家問你媽、你妹,她們對新聞的欲望是什麼,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王軼庶 攝 柴靜 供圖)
柴靜是山西臨汾人,出生於1976年,父親從醫,母親師教。她自小貪戀文字,很早開始自己的閱讀生活,父親訂閱的《中醫雜志》,母親的函授書籍,都成為她閱讀的對象。因為識字早,四歲就上小學,與同學的年齡差距,讓她格格不入,她寫幼時的自己,一個孤獨的孩子,靠牆背手看著人家玩沙包、皮筋。
1991年,15歲的柴靜進入長沙鐵道學院會計系。關於大學生活,我們在柴靜的文字裡可以看到兩種表述,一種是張揚的,“在那裡學會談戀愛,跳搖擺舞,靠寫文章出盡風頭和賺到生活費”,一種是孤寂的,“不習慣集體生活,與同寢室的女生都疏遠,天天插著耳機聽收音機”。
19歲時,柴靜開始主持湖南文藝廣播電台夜間情感類節目《夜色溫柔》。人們把滿腹心事付諸筆端,經由柴靜的聲音傳遞給陌生的人們,大家在陌生人的故事裡悲哭歡歌。她說,當初做廣播,是因為不想做小會計,願意在深夜裡聆聽各種孤獨的聲音。為此,她掙脫了彼時定向分配的體制安排,為了自己喜歡的工作,交了一大筆出路費。
她曾經的聽眾如此形容她:“她曾經用19歲的聲音,溫暖了長沙漫長靜謐的黑夜”“如水流過的聲音,略帶憂傷的句子,鄭智化沙啞的歌聲《讓我擁抱你入夢》,讓小女生們淚流滿面”。多年以后人們在央視節目看到的柴靜,身體前傾,目光注視受訪者,不斷點頭。一種傾聽的姿態。她希望給予每一位受訪者以尊嚴,以及,被理解。
《夜色溫柔》十分紅火,柴靜也成為當時湖南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她卻不甘心就此停靠自己的生活,1998年選擇辭職北上,到北京廣播電視學院學習電視編輯,為自己充電。后來,她反思二十歲時的自己:“抄在本子上的,是政治經濟學課上的一二三四點的筆記,邊角上還抄著流行歌曲、亦舒言情小說裡的字句”。沒有被教授足夠的知識去關系公共事務、參與社會,她為自己感到遺憾。被她拿來做對比的是20歲的胡適,他背誦抄寫著《新民說》《天演論》《群己權界論》。老師們出的作文題目是“論日本之所以強”和“言論自由”。
打開心靈,觸碰真相
在北廣不到半年,柴靜成功入職《三聯生活周刊》的兼職記者,不久后受湖南衛視邀請,成為《新青年》的電視主持人。從電台到電視,她的知名度再次提升。2001年,她進入央視,在“東方時空”因收視率下降被迫改版后新增欄目《時空連線》任節目主持人,是央視編制外職工。她在《看見》一書中寫當時自己採訪完了夜裡編輯片子到凌晨三四點時的情景:“我是臨時工,沒有進台証,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逢裡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扑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著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2003,柴靜從《東方時空》到《新聞調查》,從主持人成為出鏡記者。那一年春天,“非典”肆行,她參加了《北京“非典”阻擊戰》的拍攝,成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線的採訪記者之一,三天六次進入病區。她身穿白色防護服的瘦弱身影和蒼白面容,讓人們記住了她一位勇敢堅定的央視女記者。關於“非典”的採訪,柴靜說:“作為普通人的時候,我可能很軟弱,但是作為記者的時候,我卻非常堅強。”因為記者有很多武器,比如,攝像機鏡頭,紙和筆,發問的權利。對普通人和記者此二者的區分,經常可以在柴靜的文章中看到。
由於2003年的“非典”採訪,柴靜被媒體多次報道,有人贊美她的勇敢,也有人敬重她在信息不夠開放的社會執著於真相的探尋。之后,柴靜從主持人成為一名調查記者。她在接受採訪時說:“記者需要的是欲望,去知道生活究竟是怎麼回事。記者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就是因為它賦予我打開別人心靈的權利,這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打開別人心靈的瞬間,你會觸碰到一些真相。”
2006年,柴靜被選中報道央視的兩會節目,優雅知性的女性形象與嚴肅政治結合,使得關於兩會的報道多了些許人性的色彩,而柴靜對提真問題的堅持,又為節目增添了冷峻睿智的氣質。那一年,柴靜開設了個人博客,在博客上與網友互動。網友稱她為央視最“親民”的主持人。
主流媒體內的新聞專業主義
2011年8月,柴靜主持的《看見》正式開播,人們可以在她的博客上看到每一期節目的預告、節目視頻、文字簡介以及幕后故事,她的博客成為新聞報道背后的報道,一種更加感性的敘事。博客也為柴靜提供了一個更加自由的表達平台,她寫下諸如關於顧准的思想隨筆等,贏得了知識群體的認可與尊重。
越來越多的人,將柴靜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在她的文章裡,胡適與顧准的話,被引用的頻率增加了,尤其是胡適,她不僅引用胡適關於自由、民主與獨立之間的關系,甚至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會出現胡適:“日子就像胡適說的,‘平淡而近自然。’”
作為國家最大的主流媒體,央視內部形成了一種強勢文化氛圍,有其自身的價值衡量體系與思維體系,容易將置身其中的人塑造成相類似的氣質,但這樣的氛圍,也使得那些有能力又有力量持守自我個性的人,變得耀眼,白岩鬆、崔永元等,都是這樣的著名主持人。而柴靜的耀眼,在這之上。
就媒體業而言,電視較報紙雜志更保守,也更晚走出宣傳角色進入專業主義。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媒體走向市場化,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媒體緩慢扎根,真相可以埋葬虛偽與謊言,真話能刺穿戾氣與悖謬,事實本位的新聞則可干預社會,媒體人一路尋找新聞夢想得以實踐的現實空間。
從深入“非典”第一線,到調查山西污染事件,再到採訪藥家鑫案雙方父母等,這些人們更習慣在市場化雜志上看到的深度報道,出現在央視,令人驚喜。
而對柴靜而言,從電台主播到央視調查記者,是走出自我走向公共社會的過程,她在這個過程中完成的自身的嬗變:從文藝女青年至新聞專業主義者,從哼唱《讓我擁抱你入迷》,到論析胡適名言:“你們要爭自由,不要爭民主,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她仍在變得越來越顯眼,大有“天下誰人不識君”之勢,在文字裡她是謙卑的:“我的起點太低,用不著發愁別的,接下來幾十年要做的,只是讓自己從蒙昧中一點點解敷出來,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這點就踏實了。”
“我確實對人很感興趣”
新京報:你擁有很多誠摯地喜歡著你的讀者,他們的存在,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柴靜:我這十年,也沒見過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有多少,在哪兒。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售的時候,我聽到工作人員說,很少見素養那麼好的讀者,在大冷天安靜地排著隊等待簽名。而對於我而言,這些讀者拿著書到我面前的時候,已經排隊很長時間,還跟我說,你辛苦了。說得我都快哭了。我與他們相處,其實隻有幾秒鐘的時間,我希望在這一段的時間裡,能和我的讀者有一個眼神的交會,我微笑著,說謝謝,這也許是他們應該得到的溫暖。事實上,在簽售的過程中,最放鬆的時候,就是看著讀者並對人家說謝謝的時候,他們臉上久久未褪的笑,是對我的一種饋贈。他們都是很普通很善良的人。
新京報:你從事新聞行業之前,做的是電台的工作,而且是那種通過聲音交付內心,或者說,不斷進入他人內心的狀態,這樣的開端,對你后面的新聞職業道路有怎樣的影響?
柴靜:我覺得不能說是開頭影響了后來。那是一個初衷吧,做傳播的初衷,本來就不應該失去。我是誤打誤撞。我是第一代湖南廣播電台的所謂的長聘員工,在我之前,必須是專業對口院校畢業的分配員工,我當時懵懵懂懂,都不知道這些背景,恰恰在1995年留下來,是這個社會剛解凍的時候,我是鐵道學院畢業的,工作單位已經安排好了的,是中鐵十七局。不服從定向分配,需要交數額不小的出路費。當時社會就是如此,人被僵凍在一個地方,要挪動一下,代價很大。但我當時就想做電台的工作,不假思索,非干不可。自己的滿足感,就全部來自工作,來自工作中與人之間的交往,我確實對人很感興趣。我在簽售會上見到讀者的感覺,非常像我當年與我的聽眾之間的關系。有聽眾給我寄明信片,上面寫著:“大眾是最好的雇主。”我記住了這句話。后來做新聞,也是這樣的。
這也是我說的,寫這本書最困難的地方是,能不能誠實。心靈流動的軌跡,你若是想隱匿,是可以隱匿的。但是,你若是選擇隱匿,你就失去了讀者與你之間的共鳴。但袒露又很困難,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會在別人面前一覽無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寫出來。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實實寫。
“記者是要將事情袒露出來”
新京報:在你新書的首發式上,老六再次引用一句話來贊美你,說你既是男人中的異性,也是男人中的同性,你在這些好友之間是沒有性別的,“她本來也沒有”。你聽到這樣的評價有何感受?在自我承納層面,你會珍視自己的女性身份,還是會有意識地抵消這個身份的某些特征?
柴靜:其實,跟男性與女性沒有關系,我覺得,朋友是人和人的關系,隻不過恰巧他是男人,恰巧我是女人,僅此而已。
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太在乎女性身份,都是太拿外界當做自我的參照了,在我看來,珍視或者抵消女性身份,肯定是因為有一個參照系統在那裡。新聞界有個傳統是說,女性不要有女性身份,我也會面臨這樣的聲音,但總體來講,它沒有怎麼困擾我,我覺得女性或者男性,應該像呼吸那樣自然,如果你想著你該怎樣呼吸,那你就難受了,自然而然就是了。
新京報:很多人評價你的作品,會用一個詞,流暢,再加一個詞,有哲理,然后再加上,悲憫。你在寫作的過程中會去揣摩讀者的期待嗎?會有意識地迎合讀者嗎?
柴靜:沒有揣摩和迎合吧。
有時候,人遇到某件具體的事情時,通常會有相似的反應。作為記者,我也許要做的是,誠實地意識到它,並且將其袒露出來。
這也是我說的,寫這本書最困難的地方是,能不能誠實。心靈流動的軌跡,你若是想隱匿,是可以隱匿的。但是,你若是選擇隱匿,你就失去了讀者與你之間的共鳴。但袒露又很困難,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會在別人面前一覽無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寫出來。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實實寫。
新京報:“作為一個記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艱難,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又必須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為這個職業,我願意傾盡所有,但是,作為一個人,我是如此不安。”就你的體驗與理解,記者這個身份,其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有何特殊之處?在《看見》這本書裡,你會有意去謹守“記者”這個身份嗎?還是,把自己從記者這個身份中釋放出來?做出這樣的選擇,你所持的理由是什麼?
柴靜:記者比非記者多一個“問”的職責,這個職責你知道,對方也知道。但像那個踩貓的女性,她喝酒的時候,聽你唱歌的時候,她忘了,所以她向你有一個交付。但是她坐在你對面,你不可能因為她交付了你就不“問”了,這個問要觸及到她最難堪最受拷問的人性部分。但沒有辦法,像同事說的“你讓她難堪了,但你不能不問”。我能做的只是我也很難受,我跟她共同承擔這種難受。
寫書時,我覺得事實准確是記者身份的要求。其他部分讓它自己流淌吧,新聞的原則不是干燥的鐵律,是你在描寫生活時,它從生活中自己浮現出來的。
“我只是想還原他們的生命”
新京報:你把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寫得非常有個性,每個動作、每一句話,都意味深長,這容易讓人把目光從書頁上收回來,而重新轉向人身上,以及作者身上。你在寫人的時候,會有所虛構嗎?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賦予他們個性嗎?
柴靜:沒有吧,我只是想還原他們的生命。已經經過的事情,很容易變得很平面,關於某個人的印象會變得很模糊,死去的人,會變成一個名字,如果能寫出他生命的實質的話,哪怕就只是片斷,他好像就會重新活一遍。但我真不確定我能不能做得到。所以我一開始,不用資料,而是靠自己的印象去寫,因為我想喚醒這個實質,究竟是什麼。寫作的過程,其實是尋覓的過程。你記得的是這個事情,而不是那個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
新京報:你的很多文章裡,讀者們能感受到一種寬和清健的力量,一種積極理性地看待世界的努力,對你自己而言,是否也包含著一種積極向上的自我暗示?
柴靜:其實寫的時候是不覺得,你想,採訪完踩貓的女性,你在半夜裡12點,同伴們已睡下,你不能開燈,你拿著圓珠筆在自己的筆記本裡開始寫,周遭的世界已經沉入黑夜,你什麼都看不見,你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想寫下來,心裡難受,折騰得睡不著,你隻能寫下來,寫下自己的不安,這是唯一的宣泄方式,承認自己有讓自己為難之處。你所說的力量,善或者好,其實不是我寫的時候的目標,是我自己在不得不寫的過程中拱出來的。隻有這樣,你才能得到安寧。
新京報:做新聞調查,追逐真相,是一個艱難的旅程,你是否有過內心坍塌的時候?你似乎很少把內心的無力與崩潰,幽怨與憤懣訴諸筆端,是什麼支撐你一路走下來?
柴靜:我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堅強吧。你看我寫“山西”那一章的時候,我是在書稿截止之前加了最后一段,就是關於石榴那一段。(《看見》P132)那應該就是一次崩潰。我寫那棵石榴樹被砍倒之后,我在電話裡沖著我爸又哭又喊,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向我的家人宣泄自己的壓抑,那就是一次崩潰。有些東西是無可安慰的,你隻能選擇寫還是不寫。
我隻對我自己負責。我的書想說的也是,人應該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內部,眼睛向內觀看。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老天給你的時間,就那麼多。
“寫作者是被人解讀的”
新京報:榮格說,一個人不是憑想象光明來覺悟的,而是意識到黑暗,或使黑暗化作意識。就是說,面對黑暗與陰影,面對自身的“惡”,尤其重要。我們可能在你的文字裡讀到的更多的是關於光明的覺悟,比如你對人性的寬容、對平等正義的理解、對獨立自由的辨析,關於你自己人性的剖析可能不是那麼多,你是否有意選擇在文字層面呈現一個不斷完善的自我,而不是一個不斷與自身黑暗斗爭的自我?
柴靜:這是一個最終的結果,就是說,這可能是讀者對這本書的解讀,我寫的時候,有過一次跟六哥(老六)的交談,當時很意外。因為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是想寫人的,寫他人,寫我的報道,並沒有自覺,是要寫自己,除了寫“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那一章。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身份是記者,盡量不要寫自己。但他看完初稿后,跟我說,好的寫作者,比如何偉寫《尋路中國》,何偉從來沒有想過寫他自己,可是通過他寫他人,卻看到了他賦予每一個人以尊嚴。其實,寫作者是不自覺的,或者不自知的。是被解讀的。
新京報:公共理性,比如平等、公正、正義,可以放在公開的言論平台去討論與詮釋,私人理念,比如愛、善意、自由等,其表達的方式與途徑,都是私人的選擇。你在寫《看見》的時候,是否有一些表達上的傾向?願意讓更多屬於公共理性的東西,浮現在字裡行間?或者說,對邀請別人進入自己的世界,有一定的顧忌?
柴靜:可能正相反吧。我跟牟森有過一次信件往來,大概是我寫了三四章的時候給他看了,他不太滿意,給我回了一封信說,說你這不像新聞記者的寫作,我認為一個記者應該有寫史詩的雄心。你問的這個問題,若是要回答的話,我會再次提到我寫作的初衷,本來就不是為了公眾寫的,但在寫的過程中,會意識到你是寫給一個個具體的人看的,這些人未必是學新聞的人,是最普通的人,所以,我的書,其實很個人,沒有借鑒,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寫作方式,我看過國外同行的寫作,但最后寫出來的,是按自己的方式寫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我的書,不同的章節,是在不同的狀態下寫的,寫“非典”或“地震”,“眷戀”或“陳虻”,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心態。唯一相同的是,真實地寫,孤注一擲,投入其中。
寫作對我而言,是一種交付,很不容易,會觸及你內心深處的東西,我沒有從概念出發來談論。如果在寫作之始,去想我要說什麼,我是不知道的。書的序言,也是我書稿全部交稿后,在去國外的飛機上寫的,因為大家都說不寫序言,太違反常規,所以,我是在飛機上寫,那我到底寫的是什麼呀。有朋友曾經跟我說,寫一本書,你必須用一句話來說明,而且,隻用一句話就說明。其實在此之前,我是泥沙俱下地寫的,寫序的時候,才理解自己寫了什麼。
“我沒有以完整自我為出發點”
新京報:你曾向錢剛老師反思自己,說自己隻讀過言情小說,離專業新聞所要求的知識素養有一定距離。那麼,你是否會有意去為自己補充營養?有意識地去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與視野?
柴靜:我沒有以完整自我為出發點,去閱讀,那樣的話,也太功利了,也做不到。我是帶著我的困惑閱讀的,就是碰到什麼事情,困而求知。我這幾年的閱讀,也都體現在我的博客裡面,我寫顧准的時候,寫了八九千字吧,不是為了發表,而是要把不得不說的東西,表達出來。閱讀本身沒有什麼目的,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困惑,為了解除困惑,就會去閱讀。在這個過程中更新自己。
新京報:在一個社會文化秩序不夠完善的社會裡,你若是擇善固執,想有所堅守有所為,就會與你所在的環境的秩序與規則發生沖突。有沒有人給你示范,此種情境下該如何行事?
柴靜:我隻對我自己負責。我的書想說的也是,人應該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內部,眼睛向內觀看。就像同樣的歷史時期內,蘇聯會有阿赫瑪托娃,而我們為什麼隻有《艷陽天》。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老天給你的時間,就那麼多。
我敬佩的是錢剛,認識他那麼多年,沒有聽到他一句抱怨與牢騷,他永遠保持關切,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對我而言,是一個示范。我覺得,人對自己的社會共同體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創造。
新京報:你描寫陳虻的狀態:他活著,就像一片緊緊卷著的葉子要使盡全部力氣掙開一樣,不是為了得到什麼,也不是要取悅誰,他要完成。那麼,如果讓你描述自己的生存狀態,你會如何描述?
柴靜:我們在這一點上有一些相似。
【記者手記】
“柴靜”縱橫
我早到了一個半小時,柴靜遲到了半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又修改了一遍採訪提綱,翻了一遍她的新書《看見》。
柴靜的文字,有一種力量,一種有溫度又有黏度的力量,情境感極強,讀者可疾速進入感同身受的狀態,抒情與說理,皆是內斂而輕柔的,大多指向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夾雜著探索人性的熱情,關照著那些為憐憫所涵納的不安、恐懼與絕望。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在不斷地向自己發問,不斷質疑,故而字裡行間帶有脆弱迷人的氣質,與此同時,又因這種發問與質疑的持續性,這些文字擁有一種韌勁,糅合著作者的執拗與激情。
但我猜,受過嚴格的邏輯訓練的人,會對這樣的文字產生些許不適,因為其中經常使用的,恰恰是“我的答案就是沒有答案”這種的悖論式表達,而其思考的探究,也常止於最易達成共識的界面上,諸如:過程是有價值的;人性是復雜的;認識自我是艱難的;內心要獨立等。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思考者那裡,你都能找到相類似的句子,以及更精致的論証過程。
不可否認的是,生活中充滿悖論,而人性中有些東西,確是亙古未變,悖論式的表達附以輕靈的詩意,足以長驅直入至人的內心,擊中人們內心的真實,讓很多人無力還擊。而所有這一切為一個記者造成的麻煩在於,你若要尊重理解對方,你便無可置疑,就像你無法問一個詩人,為何“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除非你能成功地獲得進入對方內心的門票,細觀其思考運思的過程。
柴靜說,我的理想是不斷完善自我。這話對我而言,是一個誘惑,它有那麼一點意思,招呼著我去探看她的內心,煽動我去描繪她精神成長的軌跡。如果她願意交付自我,這個過程就是一次深度對話,而任何一個人,無論他的世界多麼小,總還是超出了單純的他自身,而滲透了他所在的時代、環境和當前可見世界的精神的。如果她拒絕,這將是一場不可原諒的冒犯,人不可度量他人的內心。
在我對這次採訪疑慮重重時,柴靜出現了。她在我對面坐下,掐掉手中的電話,對對方說,“我要開始工作了”。柴靜比我想象得要瘦得多,眼神交錯時,她給我一個標志性的溫婉沉靜的微笑,眼睛明亮,有血絲。採訪前一天,她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售新書《看見》,幾千名讀者排隊幾個小時,隻為自己所擁有的《看見》一書扉頁上有柴靜手書的“柴靜”二字。她對每一位上前簽名的讀者微笑著說謝謝。
《看見》一書首印50萬冊,上市幾天即大量加印,這些都被各大媒體作為新聞點加以報道。很難估量這個瘦弱文靜的女子所擁有的話語影響力。她的話,現在經常會出現在一些營銷微博賬號上,用做“晚安”貼,她在文章裡引用的他人的話,也常被當做是柴靜之言加以引用,可見一斑。
然而,當我問到如此龐大的印數是否含有對自身寫作的價值判斷時,她的回答是,書寫完了,就與作者沒有關系了。這是一個標准的文藝理論范疇的解答,一個作品,自其誕生起便擁有自己的生命,與作者無關。
若是放在文化觀察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一部作品的流行,必是契合了特定的社會文化需求,與當前人們的日常生存需要與經驗相關。探尋柴靜何以流行,對我而言是另一個誘惑,但她要尊重作品自身的生命,便關閉了為我提供相關答案的門徑。這是我在採訪之外需要完成的事。
因為擔心自己判斷有所偏頗,我在此前請身邊幾位長者評價柴靜,其中一位要我仔細想想價值坐標,判斷一個人一本書的價值,需區分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關於前者,千百年來,經典就那麼幾本,關於后者,得先衡量一下當下社會的文明底線。他也提醒我,你沒有權利要求他人符合你的價值理念。
如你所見,縱向,柴靜的成長,橫向,柴靜的流行,是這次採訪的內在紋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