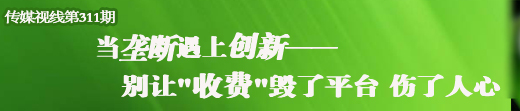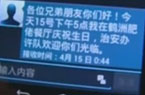形式需創新,內容取舍難
由於文學和電影分屬不同藝術類型,要把文學名著拍成電影,又要不喪失原著精華,難度極大。但好萊塢自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成功率卻很高,即便是已經改編過十余個版本的《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最新版電影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即使你對原著故事很熟悉,看電影還是會有新鮮感覺。兩部小說我是耳熟能詳,看電影之前並不抱很大期望,但電影真的拍出了新意,讓我很感動。”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研究員金燕說,“這兩部電影,一部借鑒了舞台劇的形式,另一部採用音樂劇的形式,在表現形式上都有創新。”
在金燕看來,文學名著改編不僅要形式創新,內容也要取舍得當。“尤其是大部頭名著,往往有大量心理分析,編劇要學會取舍。”她舉例說,小說《悲慘世界》,芳汀從工廠裡被趕出來,本來有很長一段故事,電影隻用了三五分鐘的戲就表現出來了,還非常感人。影片也沒有把法國革命僅僅當作歷史背景,而是正面呈現革命者群像,其效果更加震撼人心。
相比之下,《白鹿原》就很讓人不滿足,影片對小說亦步亦趨,抱著忠實於原著的想法,形式結構卻散了架,丟掉了故事的內在靈魂。蘇健認為,電影《白鹿原》與小說的差距就在於導演貪大求全,“電影畢竟隻有兩個多小時,充其量是個中篇小說的量級。如果把長篇小說拍成電影,必須有所取舍,不可能把整個小說表現出來,可以一個人物為中心,講這個人和其他人的故事。”
至於電影改編是否要忠實於原著,蘇健認為可視不同情況而定。對於經典文學名著,由於不同時期已有很多改編的版本,拍成電影可以做較多嘗試,增加當代感。“經典文學名著可以大膽改編,編劇要考慮當下觀眾的審美趣味,在情感上與觀眾產生溝通,關注當下觀眾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狀態。”他認為,《西游降魔篇》是對“西游文化”的顛覆,周星馳借用《西游記》的文學素材,表達自己心中的東西,這種做法還是可取的。
但是,對於很少被改編成電影的當代文學名著,電影改編最好盡量忠實於原著。“我也參與過改編獲茅盾文學獎的小說,片方甚至要求把原著裡的人名、地名都改掉,這完全沒有意義,對原著作者也不尊重。”蘇健認為,要想改編好當代文學名著,導演一定要從原著中找到跟自己共鳴的東西,彼此產生化學反應,對小說內涵進行視覺轉化。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