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字典》近日被互聯網公司注冊成片名將被拍成電影,引發爭議。

《同桌的你》去年上映后成為票房黑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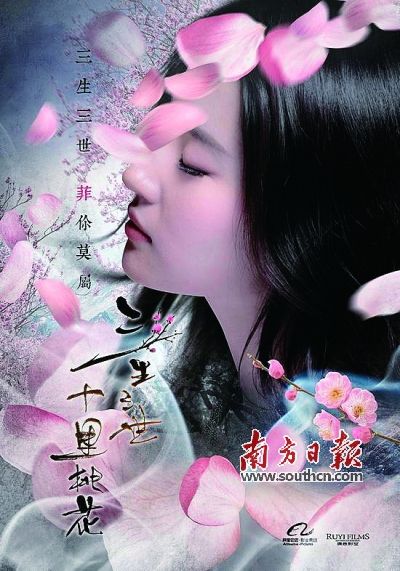
電影《三生三世之十裡桃花》從項目啟動時,就向網友征集主角人選。
核心提示
誰能想到,在沒有劇本、演員甚至導演都沒確定的情況下,隻有一首歌就能讓眾多投資人忙得熱火朝天?
目前正在熱映的《梔子花開》,証明了這並非天方夜譚。這部由歌曲衍生而來、由原唱者何炅導演的電影,上映5天票房達3.2億元。用現在流行的概念來說,《梔子花開》挖掘了“音樂IP”的大金礦,也是典型的“IP電影”。
什麼是“IP”?簡單說來,IP就是知識產權,可以是一首歌、一部網絡小說,也可以是一個名字、一段流行語。隻要當它們具有可供影視改編的屬性,就可以被稱作IP。
IP在中國影視圈中的火爆程度已經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今年五一檔、國慶檔、賀歲檔等重要檔期,都被IP電影以燎原之勢所攻佔。有人說,IP是娛樂圈中遭到爆炒的“概念股”,是當下涉足國內影視行業最快捷的途徑。
可也有人對IP說“不”。《我是路人甲》的導演爾冬升就說:“不要問我IP,也不要問我電商!那是老板跟發行商的事,那不是我的行當。”
1
【焦點】
“世界那麼大”
也要拍電影?
最近不停的有人對編劇陳彤提到“IP”這個詞。她覺得:“這不就是之前一直存在的文學改編電影嘛。”曾操刀過電視劇《離婚律師》、《一仆二主》劇本的陳彤,第一時間聯想到的例子是電影《暮光之城》和《哈利波特》系列,兩部作品的原著都是風行全球的暢銷書。
“現在總是要把一個舊的概念包裝得跟以前不一樣。”導演張一白在宣傳電影《匆匆那年》時,也忍不住向南方日報記者“吐槽”。
從2014年開始,仿佛一夜之間,“IP”忽然成為影視界人士挂在嘴邊的時髦詞匯。這個詞最初指的是為廣大受眾所熟知、具有開發潛力的原創文藝作品。不過,時至今日IP改編的范圍早已不再局限於文學作品和網絡小說,一首歌、一個人物形象、一句流行詞、一個社會現象,隻要深入人心,都是有可能被搬上大銀幕。
歌手盧庚戌去年1月推出了講述搖滾夢的導演處女作《怒放之青春再見》,可惜票房失利。同為音樂人的高曉鬆則幸運得多,他將自己創作的經典民謠《同桌的你》改編成電影,以4.6億元的票房一舉成為影壇黑馬。
《同桌的你》火了,這也讓成功操盤過《失戀33天》、《匆匆那年》等賣座青春愛情片的電影營銷高手張文伯開始思考流行歌曲轉化為大銀幕產品的可能性。張文伯找到盧庚戌,提出希望改編水木年華的另一首作品《一生有你》。張文伯向南方日報記者表示,之所以看好《一生有你》,“首先是因為歌名本身,其次是它的愛情指向和蘊含的主題,另外它有非常好的熱門暢銷的基礎。” 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都從經典歌曲上窺探到改編的商機,其中包括已上映的《梔子花開》和定檔今年8月的《愛之初體驗》,以及已宣布啟動的、由老狼原唱的《睡在我上鋪的兄弟》。根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近日公布的立項公示,張學友金曲《她來聽我的演唱會》、陳奕迅熱門單曲《你的背包》、周杰倫的《三年二班》都將被改成電影。
與此同時,有評論說:“IP就像哆啦A夢的四次元口袋,沒有什麼是它裝不下的。”就連“呵呵”,也成了一部電影的片名,影片講述的是一位懷揣導演夢的年輕人堅持理想的故事。此外,今年4月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已被注冊為電影片名。黃曉明的戀情也被當成了改編的靈感來源,據說電影的名字叫《小明的baby》。
今年6月,《新華字典》和俄羅斯方塊被互聯網公司注冊,計劃拍成電影的消息,引起熱議。有人認為這是一次新形式的文化傳播,也有人懷疑這僅是一次娛樂炒作的噱頭。更多網友樂此不疲地為劇情出謀劃策:“武俠片各大門派之間華山論劍,隻為爭搶一本《新華字典》”,“講一個俄羅斯方塊與兩人愛恨情仇的故事吧。”
2
【變化】
拍什麼要遵循“民意大數據”?
在當下的影視圈,似乎不聊IP就OUT了。
將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搬上大銀幕的游族影業CEO孔二狗說,拍電影已經不能叫拍電影了,要叫“IP開發”。也有人不太喜歡這個話題,一位資深電影營銷人士向南方日報記者坦言,“已經聊膩了”。
在熱炒概念之余,南方日報記者發現,IP項目正在為影視工業帶來一系列變化。最顯著的一點是,從劇本創作到陣容人選,不再是投資方和創作團隊單方面的決定。
電影《三生三世之十裡桃花》自去年公布項目后,阿裡影業就發表聲明,要讓網友投票來選演員,最終女主角白淺的扮演者花落劉亦菲。理由是“以消費者需求為核心來開發和運營產品是出發點”。為此,阿裡影業CEO張強解釋說:“民意的力量太強大了!大藝術家有時候容易犯低級錯誤,而我們在內容生產上相信大數據。”換句話說,觀眾愛什麼,就拍什麼。
這令華誼兄弟總裁王中磊頗為感嘆。他聲稱:“以前從策劃劇本到准備拍攝,甚至即將發行之前,我們都沒有與受眾有太多的接觸。但是現在的電影都是事先張揚的事件,從開拍之際就變成了大家都在聊的事。”
傳統的導演和編劇們正在為抓不住觀眾的喜好而苦惱。但是回望過去幾年裡大導演的失利和新導演的成功,人們發現是否擁有IP改編背景,成了決定票房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小時代》、《爸爸去哪兒》等電影都離不開出版或綜藝品牌的成功。在電影行業內部,當創作者發現作品有形成品牌的可能時,也會投入大量資源打造IP系列。例如,2015年上映的、票房近10億元的《澳門風雲2》是續集電影,並且會推出第三部﹔將在2016年賀歲檔上映的《西游記之三打白骨精》也屬於這種類型。
阿裡影業研發部總監閆超也表示,目前除了購買已經成熟的熱門IP,未來公司還會扶植有才華、有潛力的作家和編劇,打造全新的原創超級IP。
業內人士向南方日報記者表示,相比IP概念近年來在中國影視圈中的風起雲涌,好萊塢深耕IP已有多年。美國迪士尼公司就是運營IP的高手,依靠米老鼠等形象,不僅拍攝了動畫電影和動畫片,還創造了史上最成功的主題樂園。相關玩具、服飾等衍生產品所創造的利潤遠超電影本身的產值。
要實現更大范圍的IP效應,莫過於產業鏈條的延伸。張文伯以電影《一生有你》制片人的身份介紹說,除了電影,還會同步開發網絡劇、小說、漫畫、手游、舞台劇等,“為受眾提供更加多樣化的選擇。”
7月16日上映的電影《捉妖記》中,動畫角色“胡巴”的形象憨態可掬,被業界認為是一個很有潛力的IP,可以開發一系列衍生品。該片制片人江志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希望能從原創作品中發展IP,“改編熱門IP固然好,但拍原創作品更重要,因為中國電影市場目前還不像美國那樣有完善的產業系統”。
3
【隱憂】
誰中了IP的“毒”?
為什麼大家會將目光瞄准IP?網友“vincent wong”認為:“投資商為了降低風險直接拿熱門IP改成劇本,大大節省了前期成本,而且一定程度上有收視和票房保障。就像大家更願意購買國外電視節目模式而不是自主開發一樣。”
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影視公司搶購版權的大都是已經成名的作品。天下霸唱的《鬼吹燈》、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唐七公子的《三生三世之十裡桃花》、劉慈欣的《三體》都擁有龐大的粉絲群。而《梔子花開》、《一生有你》又都能引發80后的懷舊情緒。而自帶IP基因的電影從立項之初,就擁有了受眾保証和傳播基礎。
“把歌曲拍成電影,傳唱度不是首要因素,但一定是必要因素。”張文伯強調說,有了傳播基礎,就解決了大眾認知的問題,后續宣傳上便會容易很多。另外,IP所具有的好感度也是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華視影視CEO王琛則形容說:“找到一個好的IP,就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因為原著者在創作時已經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心血。制作公司接手時,無論是內容制作還是宣傳上,都會事半功倍。”
還有一種傳言稱,現在有很多影視公司攜帶重金,按照網絡作家的富豪排行榜挨個去敲門。
作為連續三年位居網絡作家富豪榜榜首的網絡作家,唐家三少也是熱門人選之一。王琛從一開始就瞄准了唐家三少網絡點擊量過6000萬次的長篇玄幻小說《斗羅大陸》。將《斗羅大陸》14冊共計三百多萬字讀完后,王琛印象最深的是書中人、神、獸之間的平衡,牽扯到幾個世界間的博弈,“它恢弘的規模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指環王》這樣的作品”。
當下以網絡小說為代表的影視改編版權價格也有翻倍的趨勢。兩年前,一部小說的改編權賣三四十萬元是常態,到了去年,有114部網絡小說被賣出影視版權,平均每部版權改編費達到100萬元,賣到200萬以上的也不在少數。資本的皮鞭在抽打著市場,閱文集團CEO吳文輝說,以前是小說堆在那裡沒人買,現在是賣空了,“甚至開始預購”,他預測未來熱門小說的改編價格還會突飛猛進。
對於這股席卷內地影視圈的熱潮,也有人感到不解。“不管做什麼都講IP,大家像中了IP的毒。”香港制片人施南生說。IP熱背后所呈現出的一些問題也日趨突出。最近播出的IP網絡劇《盜墓筆記》就是一例,與極高的關注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品的內容質量不如人意,慘遭差評。作家張小花直言自己對現已有的IP改編很不滿意。“主要的問題出在制作方心態太過於浮躁,只是一味的想要馬上佔領市場,卻沒有時間去理解原著的精神和提升品質。”
《新華字典》被當做IP搶佔的消息,更是讓一部分業內人士認為,影視行業對IP的瘋搶已陷入了一種不理智的狀態。
知名編劇束煥分享過這樣一段經歷。他曾參與過某影視公司的劇本導師工作,這家公司花了50萬元購買了某位女作家的網絡小說,結果卻根本沒有採用故事原型。“他們告訴我,花了那麼多錢,要的只是作品名字的那五個字而已。”
王琛指出,如何將好的IP轉化成一個優質的影視作品才是關鍵所在。“如果借一時熱度隨便拍一部電影,是對品牌的過度消費,而不是再生和建立。影視行業不應該是IP的終結者,而應該是給IP增值,這樣才能走向正向循環。”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