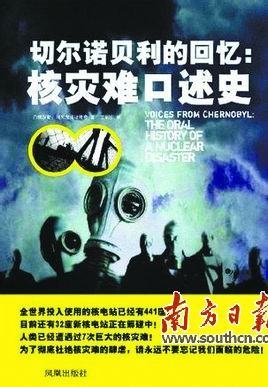
《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中文版2012年由鳳凰出版社出版。
北京時間10月8日19時,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羅斯女作家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授獎詞如此評價阿列克西耶維奇:“她多種聲音的寫作,是一座記錄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的紀念碑。”(黃燦然譯)
新聞記者出身的阿列克西耶維奇,經歷了二戰后白俄羅斯和前蘇聯的許多歷史事件,她用採訪和口述的筆法描寫了經歷二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等重大事件的遭遇和場景,將眾多的個人命運組合成集體記憶,形成了自己紀實性與文學性兼存的“文獻文學”。《鋅皮娃娃兵》《我還是想你,媽媽》《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等作品已在中國出版。其對俄羅斯歷史的記錄,對弱者群體忠實詳細的記錄,表現出了強烈的人道主義和悲憫精神。評論家認為,阿列克西耶維奇的紀實文學繼承了19世紀以來俄羅斯文學的傳統,既是對當代人類歷史境遇的反思、對和平的期望,也是對經典作家的致敬。
獨特視角
關注戰爭中 女性和兒童的遭遇
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1948年生於烏克蘭,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她畢業於明斯克大學新聞學系,曾經是一名記者。在她為數不多的紀實文學作品中,她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寫作紀實文學,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等人類歷史上重大的事件。
戰爭本是男性氣質的事情,女性往往被忽視。在1981年完成的《戰爭的非女性面孔》裡,她描寫了數百名曾被卷入二戰的蘇聯女性的命運。最早翻譯成中文的《鋅皮娃娃兵》主要記錄了阿富汗戰爭中,許多兒童在戰爭后的悲慘命運。
詩人、俄羅斯文學研究者、《我還是想你,媽媽》的譯者晴朗李寒認為:“她的作品扭轉了人們對戰爭的認識。那些參戰的大多是一些十幾歲的小孩,不懂戰爭,但突然被送往前線直面死亡,在懵懂中犧牲。”阿列克西耶維奇對於戰爭的書寫顯示出對戰爭強烈的反感,以及對兒童命運的同情。
為了採訪切爾諾貝利帶來的災難,身為記者的阿列克西耶維奇用3年時間採訪了這場災難中的幸存者:第一批到達災難現場的救援人員的妻子、攝影師、教師、醫生、農夫……從每個人不同的聲音裡透出來的是憤怒、恐懼、堅忍、勇氣、同情和愛。為了收集到這些第一線証人們的珍貴筆錄,阿列克西耶維奇將自身健康安危拋之腦后,將這些弱者的聲音記錄下來,匯成一部紀實文學史上令人震撼和無法忘記的作品。
“她記錄戰爭,是為了反思人類的戰爭所引發的災難。她從女性和兒童的視角去寫,是非常獨特的。她認為,和平是高於一切的。”晴朗李寒如此評價阿列克西耶維奇的和平理想。
文學價值
繼承19世紀以來 俄羅斯文學傳統
曾有人問阿列克西耶維奇:“你撰寫這些著作,自己居然沒有變成瘋子?這種壓力是普通人心理無法承受的。”但她卻回答說:“我是獨自行進的,我完全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人。”
文學評論家、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認為:“在我心目中,她是一個特別勇敢、敏銳的作家,也是一個特別有精神重量的作家。”
“她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她的語言非常簡潔、精准、有力,這可能和她是一個記者有關系,她的敘事,去除了那些多余的枝蔓,直抵問題的核心,又具有很強的文學性。二是她對人類的苦難是有感受,也是有態度的。她不僅記下了許多苦難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讓我們認識了苦難中真實的人。”謝有順說。
而謝有順提到,為了留下這些珍貴的精神記憶,阿列克西耶維奇選擇了艱難的寫作方式——她在寫作之前,要採訪、調查那麼多的當事人,這麼堪稱繁重同時又近乎瑣屑的工作,一般作家是不屑於為之的,但她一直在堅持。
負責阿列克西耶維奇多本著作中文版編輯工作的陳亮說,第一次讀到她的作品,就感覺像在閱讀19世紀的俄羅斯經典作品,而不是出自當代作家之手。她更像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代的偉大作家。“在阿列克西耶維奇的文字裡,我讀到了俄羅斯文學裡最偉大的觸及靈魂的東西。”
晴朗李寒認為,俄羅斯作家一向就有直面歷史、用生命寫作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無論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還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俄羅斯作家對於歷史的記錄和追問是與民族反思意識結合在一起的。
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田洪敏曾探究阿列克西耶維奇在俄羅斯的影響,她發現這種文學風格在俄羅斯並不少見。她認為,阿列克西耶維奇在歷史紀實寫作背后所蘊含的對人性和文明的反思,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等19世紀俄羅斯文學傳統一脈相承的。
獲獎分析
時隔60年再次 頒給“非虛構文學”
在此前的英國和瑞典博彩公司賠率榜單中,阿列克西耶維奇一路領跑,始終處於第一位。但許多評論家認為,阿列克西耶維奇的文學性不高,出名的時間不長,而且作品數量不到10部,體量單薄,不可能獲得諾獎。但瑞典文學院最終還是將文學獎授予了她,是諾獎第二次把獎項頒給“非虛構文學”。上一本非虛構類作品獲得諾獎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了——1953年丘吉爾以《二戰回憶錄》獲此殊榮。
諾貝爾文學獎從設立之初就青睞具有“理想傾向”的文學作品,此次頒發給這樣一種“簡單直白”的文體,讓很多人意外。
阿列克西耶維奇在中文世界裡知名度還不高,簡體中文版已有4部出版:二戰親歷者口述回憶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還是想你,媽媽》即將上市,關於阿富汗戰爭的《鋅皮娃娃兵》和關於切爾諾貝利核災的《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已出版。中文讀者對她還不太熟悉,其實她的作品已在全世界被翻譯成35種文字了,而且在世界文壇已經屢獲大獎,包括瑞典筆會獎(1996年)、德國萊比錫圖書獎(1998年)、法國世界見証人獎(1999年)、美國國家書評人獎(2005年)、德國書業和平獎(2013年)等。
對於一個歷史和戰爭的間接“見証者”,阿列克西耶維奇有著超強的意志,她在書中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情感表達和評價。阿列克西耶維奇的寫作跨度從二戰一直延伸到前蘇聯解體后。田洪敏表示,“人們實際上對這段歷史關注的並不多。有一些俄羅斯作家在寫,但他們的寫作更多的是一種后現代戲仿。她的風格既有寫實性,又有強大的抒情性,充滿著人性關懷。”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上,阿列克西耶維奇也是第14位獲獎的女性作家。田洪敏認為,諾獎授予她,根本上不是因為她寫的那些歷史事件,而是因為她的文學風格。“她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女性寫作,而是體現了俄羅斯文學鞭撻人的靈魂,針砭時弊的力量。”
“我們談不上她是不是冷冰冰的。她的寫作對世間萬物有批判、有同情、充滿愛,不是我們所謂的張純如那樣的絕望寫作。”田洪敏說道。
而謝有順說:“諾獎今年選擇阿列克西耶維奇,我覺得方向是正確的,諾獎獲獎作家系列中,太需要有像阿列克西耶維奇一樣具有現實感的作家了!好的作家不僅要表現現實、創造現實,她還要影響現實——阿列克西耶維奇就是一個可以有力地對現實產生影響的作家。”
我不只是記錄事件和枯燥的歷史,而是在寫一部關於人類情感的歷史。寫人們在事件過程中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記憶的。寫他們相信和不相信的,寫他們經歷的幻覺、希望和恐懼。不管怎樣,在如此眾多的真實細節中,這是不可能憑空想像或發明的。我的著作,是用數千種聲音、命運、碎片構成的。——阿列克西耶維奇官方網頁的一段自白(黃燦然譯)
記者 陳龍 實習生 崔美琳 王海旭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