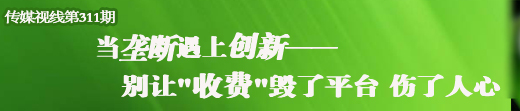二、以“微博打拐”的擴散實踐為例對創新擴散的再思考
1、一項創新——“微博打拐”的興起
據中國相關部分估計,全國流浪乞討兒童的人數約在100萬到150萬之間,這些乞討兒童中能夠被解救成功的卻極少。據悉,2006年一位安徽人沈浩曾發起“扑克尋子”、“DV尋子”等民間打拐行動,截至2011年已有800多個家庭通過這種方法找回了自己丟失的孩子。然而僅靠少數人的力量遠遠不夠,同時這類“打拐”方法具有成本相對較高,實施速度緩慢,實施范圍有限等缺點。
2010年9月,《鳳凰周刊》記者鄧飛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在新浪和騰訊微博上發布了一張被拐兒童彭文樂的照片並附言“彭文樂於2008年3月丟失,家人在撕心裂肺的折磨和苦苦尋找的煎熬中度過了三年”。隨后的每年春節,鄧飛都會把這條微博重發一遍,截至2011年春節,該微博已被轉發6000多次。2011年2月初,一位關注此事的大學生通過尋親網站提供重要線索﹔2月8日,公安機關借此線索,幫助其父彭高峰成功地找到了被拐三年之久的兒子。
第一例“微博打拐”的事件在全國網民的接力中成功之后,2011年1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於建嶸在新浪網開設微博“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呼吁網友將街頭看到的乞討兒童拍下,連同時間、地點等信息一同發上來,希望借此幫助家長尋找丟失的孩子。該微博僅開通10天時間,便吸引了57萬多博友的關注。截至2月初,已有7000多張乞兒照片被上傳,這些信息以幾何裂變的方式增長著。
“微博打拐”這種依靠微博傳播技術新興的民間打拐方式能在短時間內在中國廣大微博用戶中得到擴散並取得良好的效果。從創新擴散理論來看,這種新型的打拐方式的擴散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於傳統創新擴散理論的路徑。它是創新擴散理論在參與式傳播角度下的實踐。
2、“微博打拐”是創新擴散理論在參與式傳播角度下的實踐
上世紀70年代末興起,並於90年代之后居於主導地位的參與式傳播理論認為,現代化范式下單向、自上而下的大眾傳播模式由於漠視民眾的智慧、創造力和地方性知識,導致許多宏大的發展計劃最終失敗。因此必須將傳播實踐從一種與社區分離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傳送模式轉變為草根民眾參與的橫向和自下而上的傳播模式,使傳播更傾向於多元化、小規模、當地化、非體制化。 參與式傳播理論將傳播看作一個參與者之間共享信息的過程,這種理論模式消解了傳者與受者的區別,用“交流”取代了“發送”,從“信息”轉向了“過程”。 學者Jan Servaes認為,在參與式傳播中,專家和項目工作人員是做出回應而不是發號施令,重心是信息交換而不是擴散模式裡面的勸服。 因此參與式傳播被定義為一個在人們、集體和機構之間的動態、互動和變化的對話過程,使得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全部潛力,來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微博打拐”這種新型的民間打拐方法是記者鄧飛在使用微博時創造的,因此這種新事物來源於微博用戶形成的這個社區本身,不是什麼外來力量強行將某一種新觀念、新事物推進到一個社區的。在鄧飛使用微博上傳乞討兒童彭文樂照片到最終該兒童被成功解救之后,許多微博用戶紛紛開始效仿鄧飛的這種“微博打拐”方法,使得參與微博打拐的用戶數量不斷增加。同時由於微博本身的病毒式傳播路徑,這個傳播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關注和參與微博打拐的網友數呈幾何裂變的方式增長,使得“微博打拐”這種新興的民間打拐方法能得到迅速擴散。因此,“微博打拐”是一種參與式傳播角度下的創新擴散,在這個過程中,傳播成為一種在所有利益相關者中開啟對話以產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策略的工具,最終目標是利用傳播作為一種賦權工具,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在決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區別於傳統的創新擴散理論裡“時間”是其關鍵變量,在“微博打拐”這種參與式傳播角度下的創新擴散中,“行動”是其關鍵的變量。微博用戶們通過使用微博上傳乞討兒童的圖片,轉發來自那些尋找乞兒的家長、公益人士的微博,參與到“微博打拐”這種新型的民間打拐活動中,並且能通過評論微博和轉發在微博用戶這個社區中形成互動,同時借助微博本身的病毒式傳播特征,促使“微博打拐”這種新型的打拐方式在微博用戶群體中得到採納,迅速地擴散。
除此,在“微博打拐”的創新擴散過程中,鄧飛、於建嶸等首先使用“微博打拐”方法的創新者不同於傳統創新擴散過程中的創新者,他們放棄了自己居高臨下的專家角色,通過參與“微博打拐”這種新型的民間打拐活動,在社區對話和縱向、橫向傳播中一方面發現“使用者的需要和問題”,另一方面,與廣大微博用戶們一起共同分享和探求微博用於打拐活動的方法。在“微博打拐”的創新擴散過程中,鄧飛、於建嶸等扮演的是協助者的角色,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權威專家。整個“微博打拐“的創新擴散過程中,創新者與早期採納者、早期大多數是處於一種互動、對話、共享的關系。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